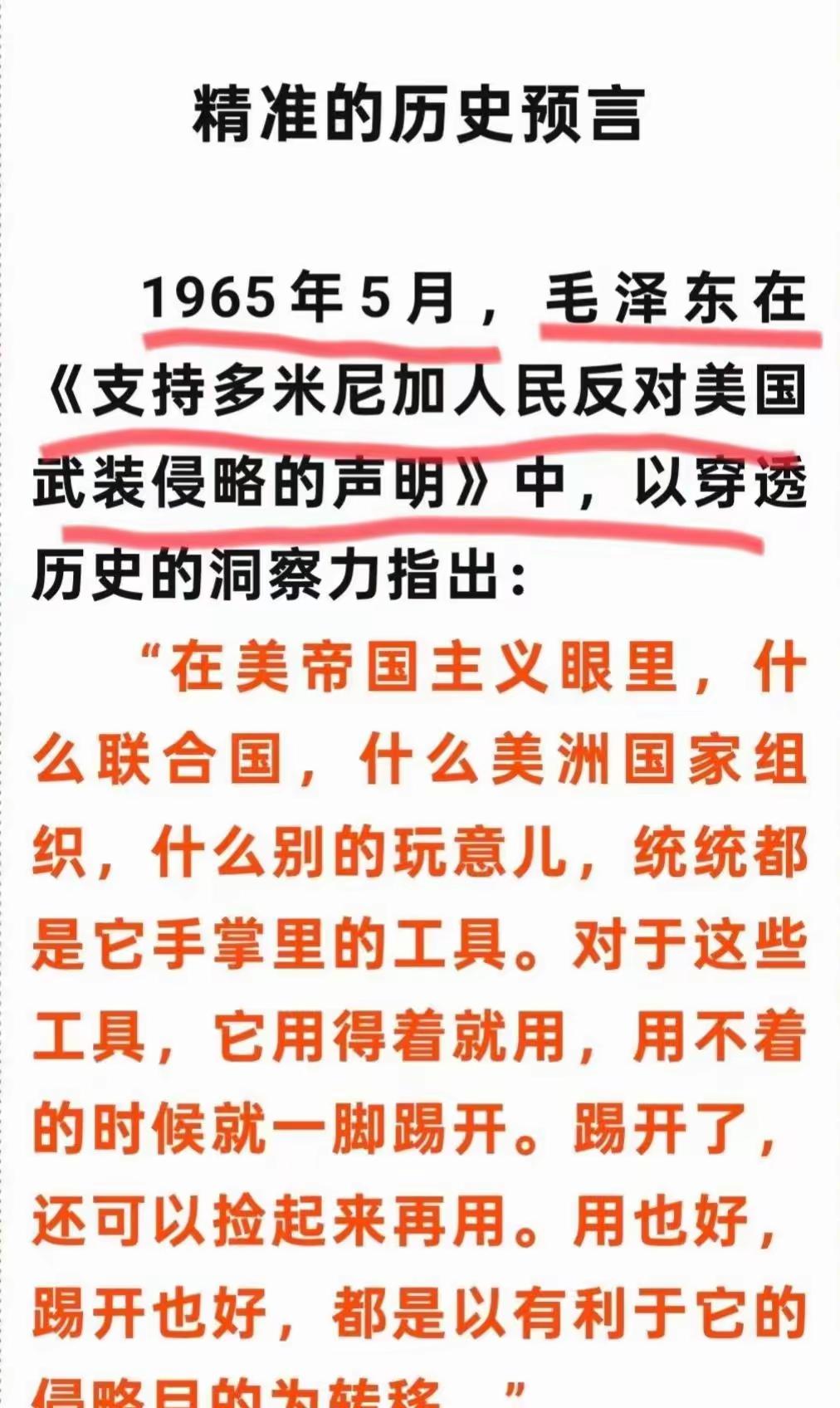1953年,马寅初向毛主席建议实行计划生育。毛主席勃然大怒,当场否决了他的建议,并提出一个令世人敬佩的观点! 马寅初一八八二年,出生在山西,二十四岁时被清政府保送赴美留学,在国外一待十年,先读经济学硕士,再拿经济学博士。回国后进北京大学讲台,当时经济学还是稀罕东西,他成了少见的行家。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全体常务委员合影上,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坐在前排,他站在第二排。 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上帮国家算过不少细账。 人口问题压到眼前,是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结果出来,全国人口已经超过六亿。 马寅初把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一项项写下,当时净增率大约千分之二十,照这个速度往前推,十五年后会到八亿,五十年后有可能到十五亿。再看土地,全国人均不到三亩,大片垦荒短时间展开不了,粮食这口锅有限,多添几亿张嘴,日子会越过越紧。 在他的账本里,人口膨胀不只是吃饭难。 国家百废待兴,要搞“赶超”,要积累资金,要上钢铁、上机器,如果衣食住行都被人口拖住,储蓄挤不出来,工业化就会慢下来,农民对新政权的期待也可能变成失望。 这些担心都被他写进了《新人口论》。 一九五七年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把这些数字和结论当面讲给毛主席听。 他说,一九五三年普查人口已经超过六亿,如果按照千分之二十的净增率往前推,十五年后是八亿,五十年后是十五亿,“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 刘少奇、周恩来当场表示赞同。毛主席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研究,可以试验。 几个月之后,《新人口论》发表,等于把这套推理公开摆在了桌上。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在谈话中又讲“人多好”“现在还是人少”,觉得等人民文化水平提高了,会自己节育。那几年“大跃进”的口号越喊越响,炼钢、修水利、放卫星到处都在要人,人口在不少干部眼里成了现成的资源。同样一串数字,学者看的是几十年的资源和粮食,决策层看重的是眼前的劳力和产量,分歧就在这里埋下了。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批判的风压下来。 周恩来约谈马寅初,希望他写个检讨,把矛盾压一压。他回去翻查自己的推理,自问有没有根本错误,结果还是坚持原来的结论。他给《新建设》杂志写信,逐条回应报纸上的批评文章,还点出“大跃进”在国民经济上的问题,说学术尊严不能不要,自己虽然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也要单枪匹马出来应战。 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他提出辞去北大校长,同年三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决定免去职务,并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讲话、不得接受记者采访,也不要随便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 此后多年,他基本从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消失。 形式上的职务没有全被拿掉,心里那本人口账却再也没机会公开谈。到了七十年代,现实把方向再一次推回控制人口。 毛主席已经提过“人口非控制不可”,节育宣传画从城市贴到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往下走。 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九八年,全国少出生六点三四亿人,其中因为计划生育减少的,大约有三点三八亿。这样一减,对中国自己的资源和环境是一种缓冲,也推迟了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二日那个“世界六十亿人口日。同一时期,医疗条件改善,建国初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二十,人均预期寿命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五岁一路提高,到一九八一年大约六十八岁,已经接近当时不少发达国家水平。 人口越来越多,人活得越来越久,负担也就越来越重。 一九七九年平反的时候,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看完材料,说当年如果多听马寅初一句,中国人口不至于轻易突破十亿,“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 二〇〇〇年前后,年净增人口开始低于一千万,“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岁月告一段落,人口问题却换了模样。 老龄化、劳动力不足、养老难、二孩难成了新的关键词。 城市里的年轻夫妇抬头看房价,低头算开支,还要照顾老人,敢不敢再生一个,很难靠口号来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人口论》又被翻出来。 有人说它不尊重个人生育权,是严厉“一胎制”的思想根子;也有人盯着马寅初本人娶两房太太、生了七个子女,觉得他说一套做一套。这些情绪容易理解,只是如果把几十年的政策和结构性矛盾都压在一个老学者身上,对他不公,对问题本身也不公。 往更长的时间拉开,中国的人口压力远早于新中国。 十九世纪中叶,一些欧洲思想家在文章里就写过,中国缓慢但持续增加的过剩人口,让多数人生活在沉重枷锁之下,“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话有夸张,也有观察。 建国后的计划生育,既为资源和发展赢得过缓冲,也把新的结构性难题留给后来者。 马寅初只是较早把数字算出来、把话挑明的人,他当年看到的是六亿到十五亿的风险,今天的人感到的,是另一种沉甸甸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