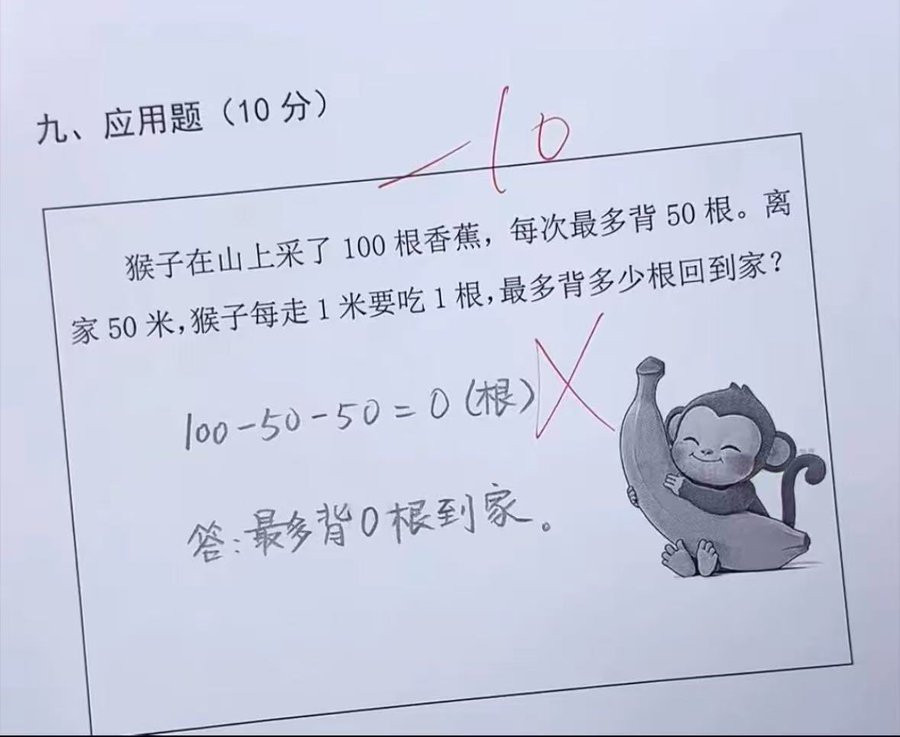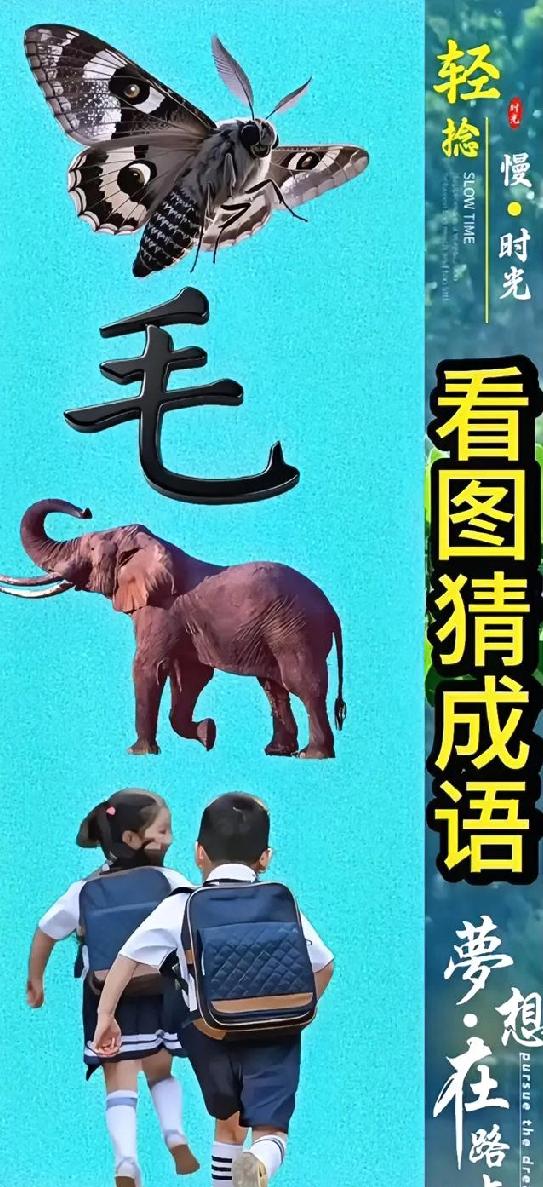1976 年我高中毕业后大队小学恰巧设了初中班,大队领导通知我去做一个民办教师,学校负责人安排我任初中数学课,一天 10 分工,外加每月 7 元 5 角国家补助,在当时比教小学的民办教师多 2 元 5 角。拿着那张盖着红章的任命通知,我攥着衣角的手都在抖 —— 要知道,那年月村里能读完高中的人屈指可数,我不仅能跳出农门捧上 “教书碗”,还能多拿补助,这在全家人眼里,比过年杀头猪还喜庆。 开学没几天,我就发现教室后面墙角的粉笔总对不上数。我每天放学都数好,把长的短的归拢在一个破茶缸里,可第二天早上总会少几截。我问是谁拿了,底下都摇头,只有铁匠家那个高个子小子李卫东,眼神躲躲闪闪。 那天我故意提早到校,猫在教室后窗根下。天刚蒙蒙亮,一个人影溜进来,果然是李卫东。他飞快地从缸里抓了几根粉笔头塞进兜,转身要走,正撞上我。他脸唰地白了,手紧紧捂着口袋。我没骂他,只问:“拿粉笔做啥?”他梗着脖子不吭声。我叹口气:“走吧,去你家看看。” 他娘正在院里生火,见了我忙用围裙擦手。那屋里黑黢黢的,墙上却用粉笔写得密密麻麻,全是算术题,歪歪扭扭的。他娘说:“这娃魔怔了,夜里就着月光在墙上写,说不能比你教得差。”我才知道,卫东下面还有三个弟妹,他爹想让他退学回家拉风箱,他偷粉笔是想夜里多练练,证明自己能读下去。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回校后,我把那破茶缸推到卫东面前:“以后粉笔你管,用多少拿多少。但有个条件,你得教会你弟妹认数字。”他愣愣地看着我,用力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卫东成了最用功的学生。他不仅管着粉笔,还用树枝在地上教弟妹写字。期末他考了第一,我把那支用了半学期的红铅笔奖给他。他接过笔,咧着嘴笑,露出两颗虎牙。 放寒假那天,雪下得很大。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看见卫东还站在教室门口,头上落了一层白。他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塞给我,转身就跑了。我打开一看,是几根长短不一的粉笔,被他用手磨得圆溜溜,像一个个小雪球。 我攥着那些粉笔走出校门,雪地上一串小脚印通向远处。风吹在脸上,冷飕飕的,可心里却觉得挺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