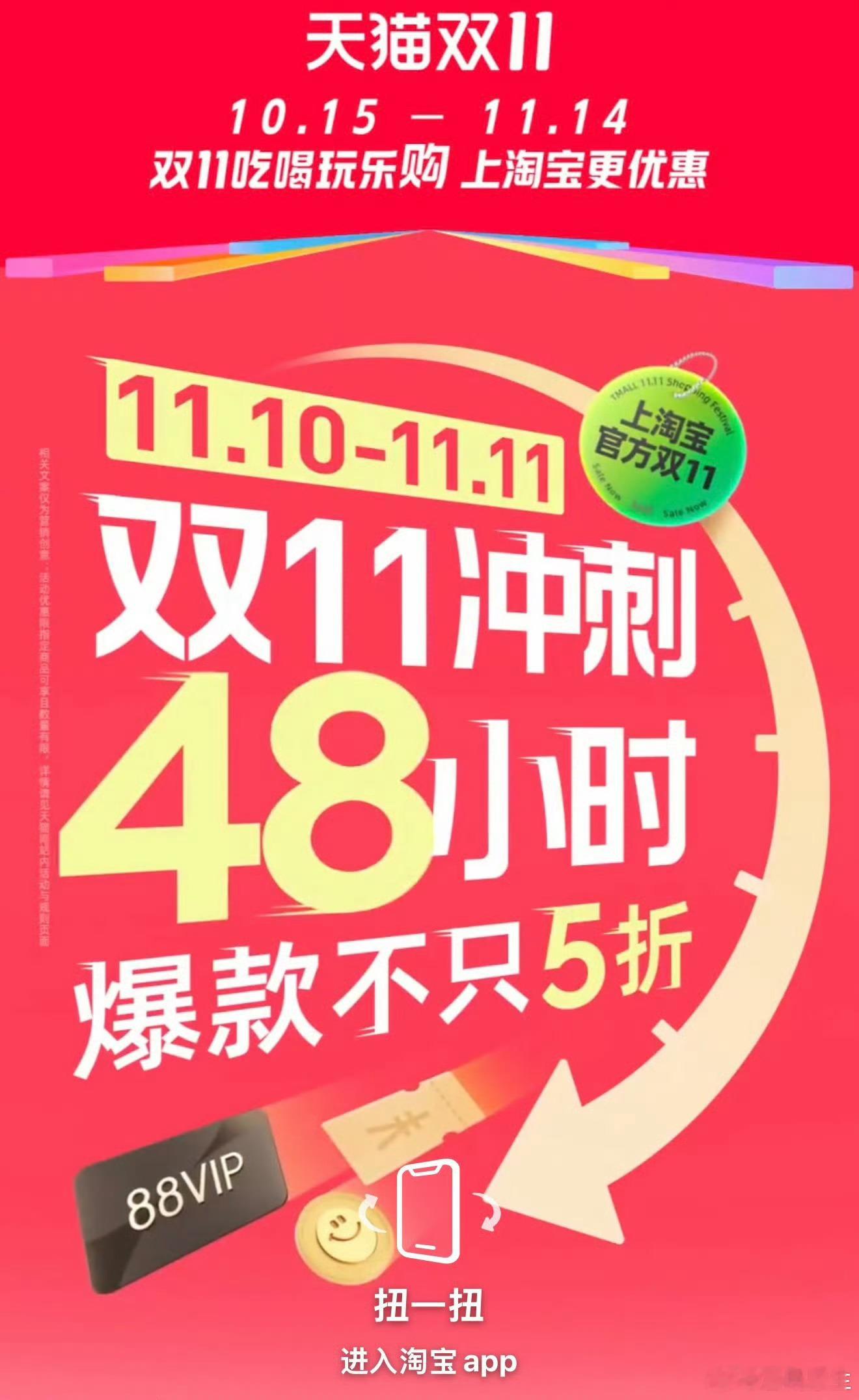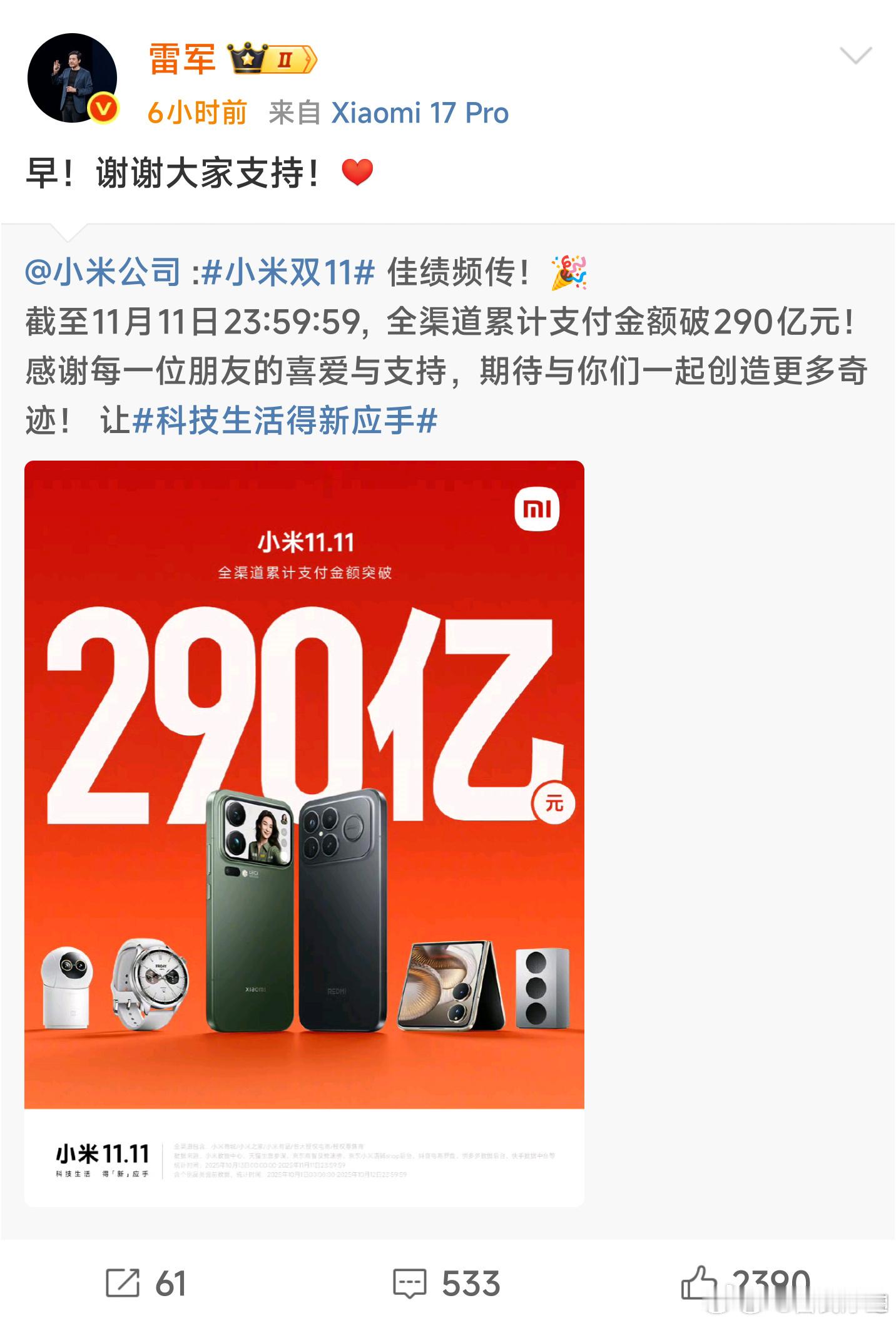双十一狂欢后的冷思考荧幕上的数字疯了。那是在子夜时分,一串猩红的、跳荡的、不断自我叠加的数字,像着了魔的符咒,占据了千家万户的方寸屏幕。它不再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倒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驮着人们的眼神,奔向一个虚妄的极境。这数字的狂欢,这购物的“盛典”,在几声零落的犬吠与秋虫的倦鸣里,膨胀成一片光怪陆离的海。村口的榕树下,老辈人曾摇着蒲扇,谈论谷物的成色、猪崽的行情,那是一种贴着地皮的、带着汗味的计算。而今,这计算似乎被连根拔起,悬在了半空。人们不再关心泥土与收成,却对几百上千公里外,一个被称作“平台”的虚无处,投注了全部的激情。他们抢着那些“满减”、“津贴”、“跨店优惠”,像 decipher 着一部天书,瞳孔里反射着折扣的绿光,仿佛占尽了天下的便宜。只是那便宜,细细想来,不过是纸面上虚划掉一个原价,再踏上一只脚的快意,与货真价实,终究隔了一层。这狂欢的底下,涌动着一种低端的、盲目的焦渴。衣柜早已塞得关不上门,碗橱里堆着从未拆封的赠品杯盏,墙角是上一年囤积的、已然受潮的卷纸。东西是多了,多到成了负担,成了需要额外空间去容纳的“废物”。然而手指还是忍不住要点下去,那一声模拟的“叮咚”脆响,那一个划掉删除线的动画,似乎比物品本身更能带来片刻的满足。这是一种被精心饲养的欲望,它不吃草料,只吞噬注意力与闲暇,然后排泄出更多的空虚。那些廉价的光鲜,脆弱的“新品”,在拆开包裹的瞬间,魔力便已消散大半,如同烟火熄灭后留下的硫磺味,有些呛人。消费,这本是田间地头、市井街坊里一桩朴素的交换,用汗水换盐铁,以盈余补不足。而今却被包装成一种文化,一种标识身份、确认存在的仪式。仿佛不在这数据的洪流里剁一次手,便成了时代的落伍者,生活的局外人。人们消费的,往往不是物品的使用之需,而是那个被广告编织出来的“符号”——是“精致生活”,是“聪明主妇”,是“潮流先锋”的幻影。这实在是对消费的误读,将人拖入一场无休止的、关于形象的疲惫竞赛里。李家的媳妇为了一个logo熬到半夜,张家的后生为了一双潮鞋啃了半月馒头,这其中的得失,怕是算不过来了。市场的风向,也被这人为的飓风吹得七零八落。工厂不再潜心于“匠心”,而是赶着周期,生产着专为这一日设计的“爆款”——价格低到尘埃里,质量也薄如蝉翼。它们在这一日倾销一空,然后便迅速被遗忘,等待下一轮的改头换面。这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游戏,诚信的商家反倒步履维艰。更不消说那街道两旁的店铺,在狂欢的几日里,冷清得能听见落叶的声音。那曾充满人情味的讨价还价,那可以亲手触摸布料的质感、掂量铁器的沉实的踏实,都在渐渐远去。实体经济,那承载着最多烟火生计的庞大根系,正被这虚拟的繁华一点点地蛀空。人当然需要购物,需要借此安排生活,抚慰身心。但好的消费,应是一种从容的选择,是“量入为出”的智慧,是“物尽其用”的惜福。它不该是被煽动起来的燥热,不该是算法精密算计下的冲动。它应该帮助我们触摸到物品的真实温度,感受到劳作与交换的本真乐趣,建立起人与物、人与人之健康、持久的关系。那或许是在一个平常的午后,于相熟的老店里,不慌不忙地挑一方好墨,选几样时新菜蔬,完成一次沉默而庄重的握手。窗外的凉意渐深,星河低垂,沉默地照耀着这个陷入短暂亢奋的人间。那屏幕上的数字,依旧在不知疲倦地翻滚,像一个巨大的、冰冷的倒计时。它在计算着什么?是财富的累积,是欲望的峰值,还是一个时代在消费迷狂中,那悄然流逝的、朴素的真实?我只听见,更深入静时,自己的心跳,一声一声,平稳而清晰。那才是生命里,最需要去倾听、去守护的,不折扣的丰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