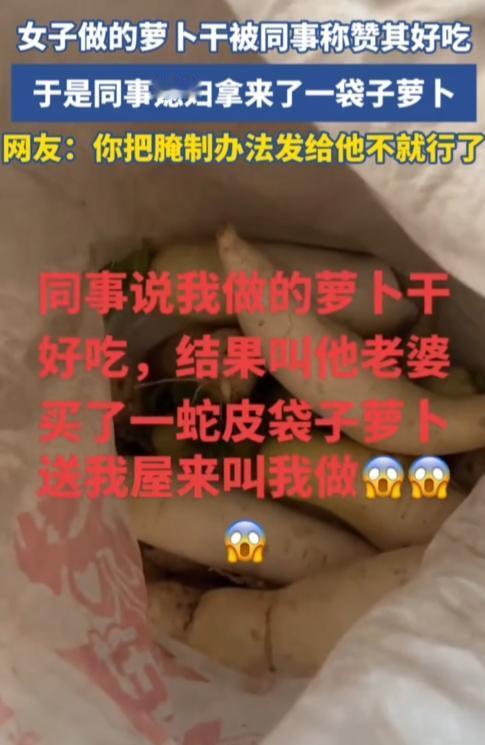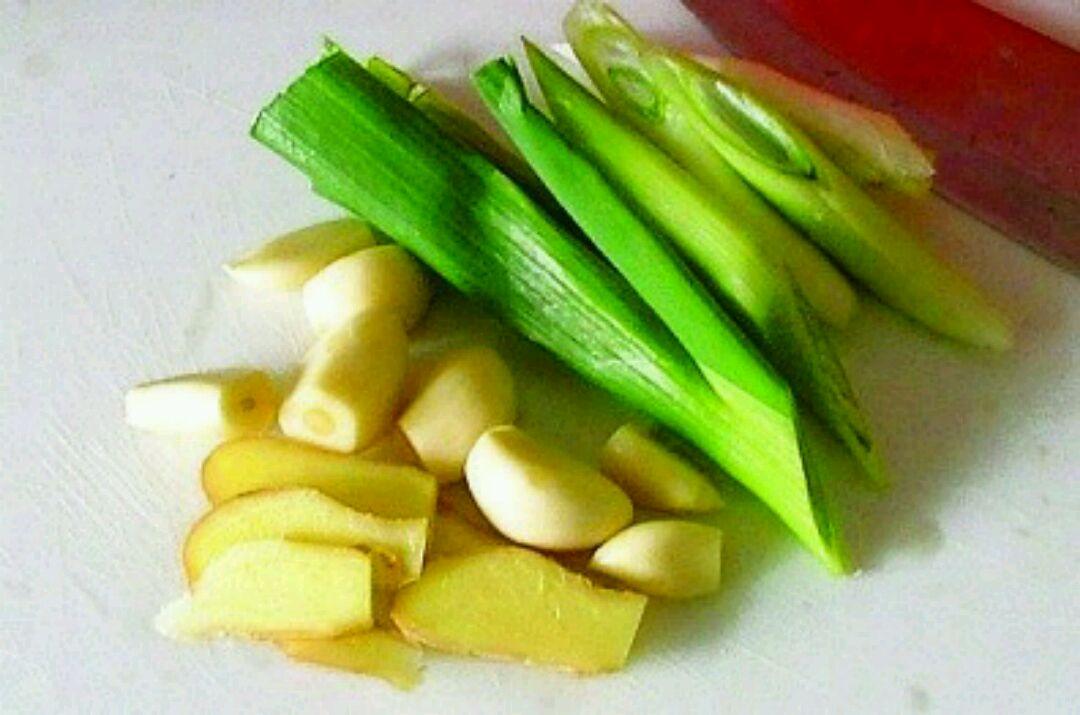初到柳州的人,总被那满城的味道包裹着——不是那种扑鼻而来的浓烈,而是丝丝缕缕、若有若无的缠绕。

要离开许久后,你才会突然想起,原来那些味道从未真正散去,它们只是悄悄躲进了记忆的褶皱里,等着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温柔地漫上来。

脑子里要是想起了螺蛳粉,第一时间出现的并非画面,而是那股气息,酸笋在时光里慢酿出的、带着山野气的清冽,混着螺汤的醇厚,在空气中浮着。粉是滑的,一吸便溜进口中;汤是暖的,顺着喉咙缓缓下去。

吃完后,当那股热闹的酸辣淡去了,舌根处却浮起一丝鲜,若有若无的,像是远山的回响,又像夜半醒来听见的虫鸣,清晰而又朦胧。那余韵不打扰你,只是陪着,陪着走一段路,陪着一个午后的恍惚。

在这龙城的餐饮后厨,大多都有这么一罐柳州特色的双合糟辣酱。红艳艳的,封在陶坛里。它从不张扬,配着小笼包、配着肠粉......它只是轻轻托着食物原本的滋味。吃过后的回味,是温吞吞的暖,从胃里慢慢升起,散到四肢去。

双合糟辣酱的回味不是轰轰烈烈的热,倒像冬日里晒了一下午的棉被,蓬松的,软和的,裹着你。那微甜的酒糟香,在喉头久久不散,让你忽然懂了,原来最深的滋味,都是要交给时间去成全的。

高火上的螺蛳鸭脚煲咕嘟咕嘟地冒着,鸭脚炖得酥烂,一吮,肉便离了骨。芋头吸饱了汤汁,腐竹在红油里浮沉。

热闹是它们的,你只管慢慢地吃。真正叫人惦记的,却是散场后的辰光——唇齿间留着微微的胶着,那是胶原化在汤里的印记;还沾着淡淡的香料气,即使过了些许时间,也还隐约闻得见,似柳江的雾,远观浓厚,近了却也只是淡淡地包裹着你,绕着你,直到下一道美味的到来。

天蒙蒙亮的时候,煮粉的摊子便支起来了。清汤,鲜肉,几片菜叶,简简单单的一碗,却是晨光里最好的慰藉。汤是清的,却能品出骨头的醇;肉是嫩的,还带着生鲜的甜。

吃罢,嘴里干干净净的,没有半点油腻,只有一缕清甜,像晨雾似的,薄薄地罩着。这余韵陪着你走过清晨的街市,陪着你开始一天的忙碌,直到日头高了,才悄然隐去——你甚至不觉得它离开了,因为它已化成了你晨间的一部分,透亮,清爽。

若是往融安去,山间的气息便重了。滤粉是手工滤出来的,粗细不一,反而多了活泼的生气。简单的浇头,纯粹的米香,吃的是山水的本真。

那余味来得慢——不是立刻就能察觉的,要等,等米香在口中渐渐苏醒,等那股谷物朴素的甜悄悄漫上来。它不争先,不张扬,只是像山间的溪水,静静地流,流过石,流过苔,最后流进你的记忆里,留下一片清凉。

街角总有卖酸嘢的小摊。玻璃缸里泡着各色的果子,红的萝卜,青的芒果,黄的木瓜。插一根竹签,边走边吃,酸甜辣在口中炸开,又迅速消散。这

余韵是短的,短得像一个轻快的休止符,在生活的乐章里,添一点俏皮的节奏。它不是正餐,却是不可或缺的点缀——饭前开了胃,饭后解了腻,两餐之间提了神。

这些美味的余韵,淡淡的,却固执地留着。它们不浓烈,却特别——特别到你离开柳州很久了,某个寻常的傍晚,或者某个突然安静的午后,你会停下手中的事,想起那股说不清、道不明,却真真切切存在过的滋味。

那时你才明白,原来一座城,可以这样住进你的味觉里,淡淡的,却总也散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