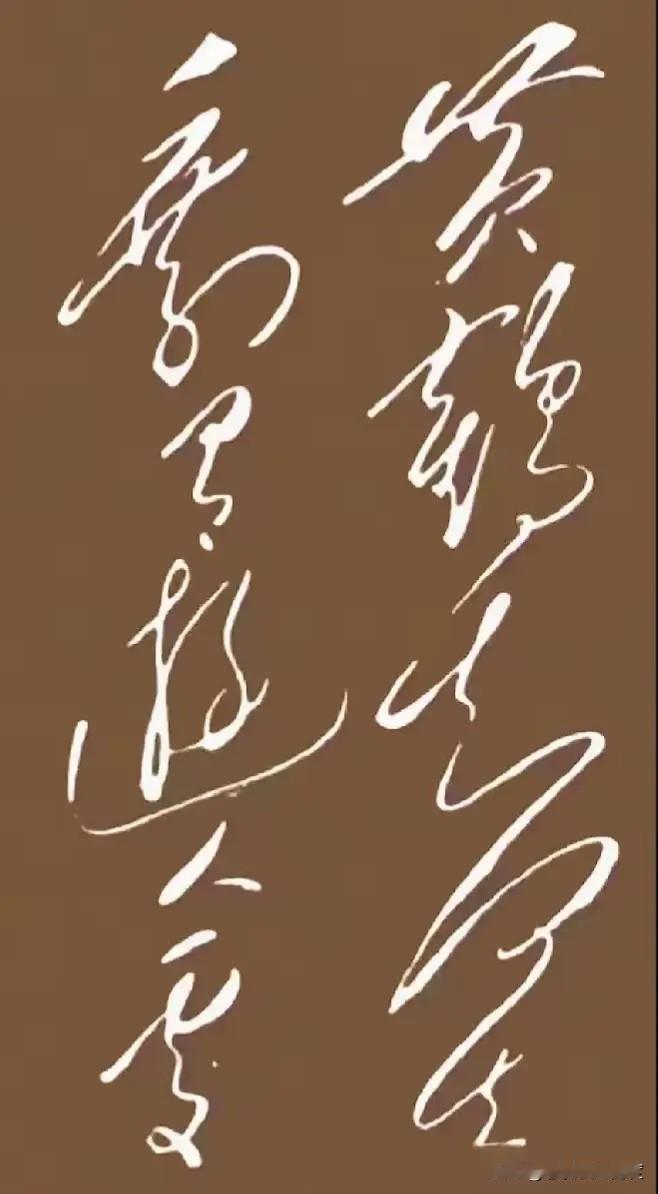那天,去了很久没去的双博馆。小雨夹雪的天气,注定了游客稀少。进入二楼主题展厅,看到一个到令我激动的名字:玉见江汉——武汉博物馆藏玉器精品展。
青铜器和玉器,游玩博物馆时最喜欢的“遇见”。武汉去过几次。为了观看曾侯乙编钟,专程去了湖北省博物院。去了才知道,何止编钟?那些在“国宝档案”和专门介绍青铜器专著里出现过的很多青铜器国宝,原来都是曾侯乙的贡献。对玉器的印象,却想不起来了。

这一次,顺江流而下来到扬州双博馆的玉器,会给我怎样的惊喜?扬州与武汉,两座因为长江被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有共同点吗?
先说一首名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的送别诗,总是写得非常辽阔,丝毫没有别离的忧伤。被长江牵起来的两座城市,像两个分别久远的兄弟,终于找到了彼此。
多少年后,一首名叫《烟花三月》的歌曲,再度将两个城市联系在一起。其实,即便没有李白送孟浩然,没有九九年的这首流行歌曲,武汉与扬州在精神层面的融合,早已经深入骨髓,就像这次玉器展一样。

“和田玉、扬州工”。这些来自江汉之城的玉器里,有没有“扬州工”的产物?可惜,考古专家能考证出文物的大致年代,却无法考据出文物生产的所在地。上古的痕迹通过比对和炭14能让时间的误差减少到最低,遗留的信息里却提取不出产地的气息。
这次展览的玉器分为三个主题:礼器、陈设与配饰。本质上,玉是古人眼中美丽的石头。当美丽的石头经过加工,便拥有了超越石头的能力。到了周朝,《周礼》明确了“六器”礼制体系,规范了“璧、琮、圭、璋、琥、璜”的形制和祭祀等级。即“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壁,男执蒲壁。”
展品中,来自新石器时代的兽面纹玉琮,透着远古的神秘。有趣的是,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人,在玉琮的顶部,加装了一个黄金顶盖。玉琮变身为最高档的香薰。我相信,有此创意不奇怪,敢于将创意变成行动,一定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以后。

巧的是,展品中有两只白玉蝉。一只标明是汉,另一只注明为清。众所周知,汉代白玉蝉,多为葬玉。“汉八刀”的对玉蝉工艺的准确概述。所谓“汉八刀”,指的是琢玉工艺简洁简练,玉蝉神态逼真的特点。有人说,“汉八刀”指的是玉蝉雕刻只用了八刀,附会了。
“汉八刀”用的不是刻刀,而是用水砣砣成。随着葬玉风俗的日渐式微,“汉八刀”工艺终成绝唱。后来虽有众多朝代在模仿“汉八刀”,但是模仿终究是模仿,少了灵魂。清代有很多玉器,都在模仿前朝经典,却没有成功。这里将两只白玉蝉放一起,便能看出高下。
“生者佩玉,以喻其德;逝者葬玉,以护其魄”。这句话凝练地概括了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贯穿生死的双重核心价值。生者佩戴玉器,是儒家“君子比德于玉”的实践。逝者以玉随葬,主要是根植于道家及民间信仰中对玉石神秘力量的崇拜。一块精美的石头,融合了儒家道家两大哲学思想。

《周礼》规定了不同等级的活人用玉。葬玉的使用,也严格遵循着古代礼制,同样是阶级身份的重要标识。同样在《周礼》里有记载,“天子含珠,诸侯含玉”等不同社会等级者,在死后口中所含之物的区别。至于金缕玉衣、金棺玉匣等,仅限皇帝与诸侯王使用,僭越,是要杀头的。
来自江汉之城的玉器展,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朝。其中明代的陈设玉器“白马负经”摆件,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故事,简明扼要到一个精美的摆设上。其小中见大的设计,独具匠心。

用于配饰的“腊子”,正确的叫法“玉勒(上勒下玉)”。这是一种从“红山文化”就发现的玉器饰物。它不同于常见的玉璜、玉璧、玉珩等物,而是更加小巧。既可单独佩挂也可以组合到一起。
清代玉器工艺,尤为繁杂。其中代表“扬州工”的“山子”,是乾隆年间的巨型玉雕“大禹治水图”。在北京不在武汉,更不在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