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从1万变成30万,谁贡献更大?
山穷水尽时想到了他
1937年夏,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迫使国共两党暂时搁置争议,走向合作。在决定南方红军游击队前途命运的庐山谈判中,中共最初提出由经验丰富、战功显赫的彭德怀出任改编后部队的军事主官,但这一提议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遭到了蒋介石的断然拒绝。国民党的底线十分明确: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绝对不能是共产党的高级将领。

主持谈判的周恩来,在排除了众多可能人选后,一个特殊的名字跃入了他的脑海——叶挺。叶挺的经历堪称传奇,他是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的独立团团长,声名远播,也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两次重大武装反抗的核心领导者之一。广州起义的失败以及随后党内复杂的矛盾,让他心灰意冷,最终选择了负气脱离共产党,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当抗日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这位曾经的革命将领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结束流亡,辗转归国。叶挺与共产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此刻他并非中共党员,其“无党派爱国将领”的身份恰好可以规避国民党设置的限制。

经过一番内部的权衡与考量,国民党方面最终同意了这一安排。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命令,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 对于延安方面而言,接受一位脱党十年、经历曲折复杂的将领来领导一支由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部队,并非没有顾虑。
为了消除疑虑,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简陋的窑洞里,亲自与远道而来的叶挺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在这次决定性的谈话中,叶挺表示,过去的革命道路如同登山,自己曾因一时的迷茫和挫折,在半山腰选择了退缩,但现在,他已认清方向,决心重新归队,跟上大部队继续向上攀登。

中共中央最终正式批准了对叶挺的任命,并决定由项英担任副军长,实际负责党内事务和政治工作,同时任命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组成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共同辅佐叶挺指挥这支肩负特殊使命的新生力量。
扎根江南:“三大纪律”唱响茅山
新四军的诞生,源自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整合。初建之时,全军总兵力约1.03万人,下辖四个支队,分别由陈毅、张鼎丞、张云逸(兼)、高敬亭担任司令员或指挥。这支部队面临的起步条件极为艰难:武器装备五花八门,数量严重不足,弹药匮乏,供给困难,与装备相对精良的日军相比,实力悬殊。如何在敌人的心脏地带站稳脚跟,并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成为新四军生存和发展的首要课题。

1938年春,肩负开辟苏南敌后战场重任的陈毅,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主力,跨过长江,挺进到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地区。当部队抵达溧阳的水西村等地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日军正在加紧进行所谓的“清乡”扫荡,妄图巩固其占领区的统治;国民党地方势力和顽固派武装也时常制造摩擦;而当地百姓则对这支陌生的“新四军”持观望甚至怀疑的态度。
陈毅创造性地将红军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群众纪律,作为打开局面的金钥匙。他亲自带领干部战士,将纪律条文用最朴实、最口语化的语言重新演绎,编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例如“进门先扫院,用水先问好,说话要和气,借物当面点,损坏要赔偿,莫拿群众一针线”,并将这些写在竹板或木牌上,悬挂在部队宿营地的门口或村头巷尾,让老百姓看得见、听得懂、信得过。

老百姓从这些点滴小事中,逐渐认识到新四军是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是真心抗日的队伍。在此基础上,陈毅还非常注重宣传工作,他利用一切机会,将苏南的田间地头、村口场院都变成了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讲解共产党政策主张的流动课堂。群众基础的迅速巩固,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四军第一支队不仅在日伪重兵环伺的苏南地区站稳了脚跟,而且迅速发展壮大,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中原逐鹿:红薯窖里的战略家
正当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在富庶的江南水乡艰难开拓、站稳脚跟之际,远在千里之外、连接华北与华中的战略要地——豫鄂边区,另一支新四军部队也开始了其充满艰辛与传奇的征程。1939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敌后武装的指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发展为豫鄂挺进纵队)成立,由李先念担任司令员。

李先念最初南下时,直接掌握的骨干力量仅有160余人。鄂豫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都异常艰苦。这里多是穷山恶水,土地贫瘠,百姓生活困苦。李先念看到老乡们缺少储存粮食的设施,红薯等作物容易腐烂,战士们就主动帮助他们挖掘又深又干燥的红薯窖。
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残酷扫荡下,部队的物质供应极其匮乏。李先念和战士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没有照明用的煤油,他们就把缴获来的日军牛肉罐头、水果罐头等铁皮盒子收集起来,加上灯芯和一点点宝贵的油料,改造成简易的煤油灯。

他领导的部队,以那最初的160人为骨干,广泛发动群众,吸收地方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消耗日伪军。部队如同滚雪球般迅速发展壮大。到了1941年,当豫鄂挺进纵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时,这支从穷山沟里走出来的部队,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5万余名指战员、配备有电台、医院、枪械修理所等机构的强大武装力量,其活动范围遍及鄂豫皖湘赣五省接壤的广大区域,控制或影响着多达53个县,开辟了广阔的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
苏北风云:“推磨盘”拖垮鬼子兵
1940年,为了加强华中地区的抗日力量,统一指挥,八路军的一部分主力部队奉命南下,与新四军在苏北地区会师。其中,由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约两万余人,是一支经历过长征和华北抗战考验的劲旅。

苏北地区人口稠密,河网纵横,是日伪军重点控制和争夺的区域,同时也是国民党顽固派势力较为活跃的地方,斗争形势异常尖锐复杂。黄克诚部队的到来,最初甚至在当地群众中引发了一些小小的“误会”。苏北百姓已经习惯了身着蓝色(或灰色但样式不同)军装、活动在当地的新四军部队,突然看到大批穿着不同颜色军装、说着南方口音(黄克诚是湖南人,部队中北方籍战士也不少)的军队开来,一时间难以分辨,甚至有人以为是“假八路”来了。
面对这种情况,黄克诚让部队在驻扎、操练和行军途中,广泛而响亮地唱起那首早已随着八路军、新四军的足迹传遍大江南北、深入人心的《八路军进行曲》(或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嘹亮的歌声很快就打消了当地百姓的疑虑,也迅速拉近了这支南下八路军与苏北军民的距离。

在军事斗争方面,黄克诚根据苏北平原水网地区敌我态势和作战特点,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游击战争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原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他擅长使用的“推磨战术”。白天集中部分兵力,对敌人的某个据点进行佯攻、袭扰或者有限度的攻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调动其增援部队,使其暴露弱点;到了夜晚,则利用熟悉地形、群众支持的优势,以及部队较强的夜战能力,迅速进行大范围的、敌人难以预料的急行军和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或打击范围,转而选择敌人兵力薄弱、防御松懈的其他据点或小股部队进行突袭。
如此反复,时东时西,忽南忽北,就像推着一个巨大的磨盘一样,将敌人牵着鼻子走,使其疲于奔命,在广阔的苏北平原上不断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和士气。根据地范围不断扩大,武装力量也获得了惊人的发展。第三师在进入苏北后的三年时间里,兵力从最初的两万余人猛增到了七万余人。
皖口传奇:“卖马买种”暖人心
在新四军各个发展区域中,彭雪枫和他领导的豫皖苏边区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历程,无疑充满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和动人心魄的故事。1938年秋,肩负着开辟豫皖苏敌后战场重任的彭雪枫,率领一支仅有373人的精干队伍——新四军游击支队,从河南确山竹沟镇出发,东进至豫皖苏边区。

部队东进途中,恰逢春荒,军粮告罄,战士们面临断炊的困境。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彭雪枫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卖掉自己心爱的一匹枣红战马。在卖掉战马换来钱款后,彭雪枫并没有立刻去购买粮食以解部队之急,而是用这笔钱购买了当时极为宝贵的农作物种子,然后分发给沿途村庄的贫苦农民,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恢复农业生产,并承诺秋后以合理价格收购粮食。
它向当地百姓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队,为了帮助人民群众摆脱困境,建设家园。在彭雪枫的领导下,部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抗日,积极组建地方武装,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豫皖苏边区的抗日烽火迅速燎原。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这支最初仅有373人的队伍,就发展成为一支拥有4万余人、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的正规武装和地方武装力量,创建了横跨豫皖苏三省边界的广阔抗日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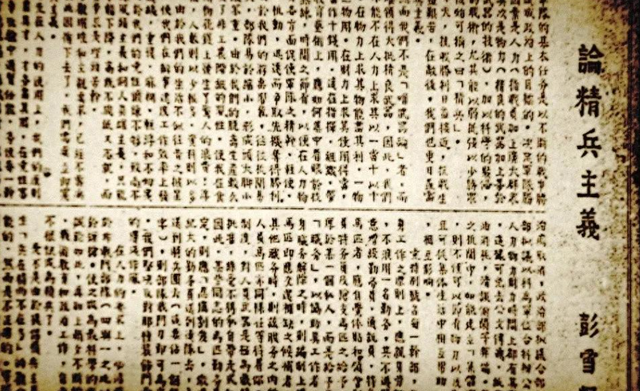
彭雪枫还特别重视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建设,尤其是骑兵部队的建设。1941年除夕夜(农历年三十)进行的一次长途奔袭作战,更是成为了彭雪枫骑兵战术的经典之作。当时,为了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彭雪枫亲率骑兵团主力,冒着严寒风雪,顶着刺骨寒风,在漆黑的夜晚秘密急行军二百余里。
他们突然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冲垮了日伪军精心设置的三道封锁线,歼灭和击溃了大量敌人,缴获了丰富的战利品,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胜利的消息传开后,豫东地区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无数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出现了父子、兄弟同上战场的动人景象,部队中甚至组建了“父子兵连”、“兄弟班排”,豫皖苏根据地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从1937年秋天改编时的1万余人,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的30万(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总计)雄师劲旅,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经历了皖南事变的挫折,更是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实现了凤凰涅槃般的奇迹扩张。
参考资料:[1]耿东旭.新四军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贯彻[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5(1):52-60

 云霞育儿网
云霞育儿网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