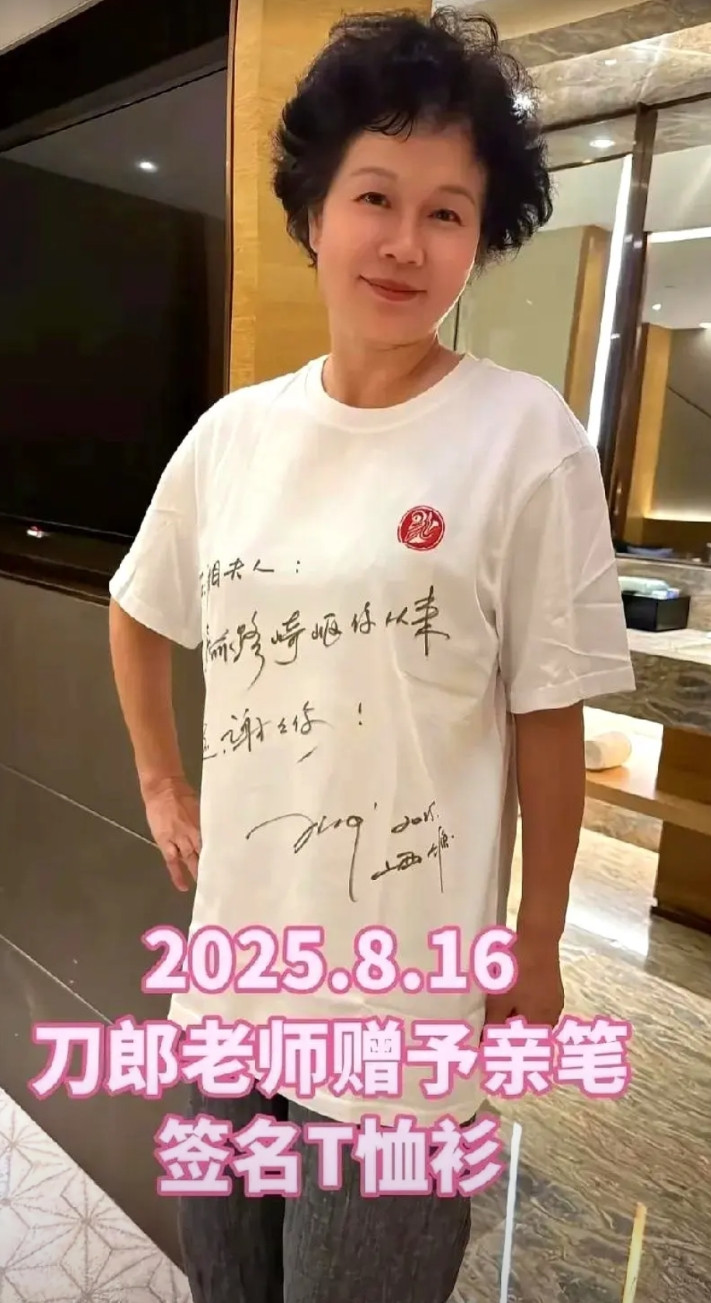1967年,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马思聪叛逃美国,谁料很多年以后,晚年的马思聪对自己的举动做出了辩解,认为他当初并非是叛逃,而是另有隐情。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广东海丰一个种满荔枝树的院子里,1912年出生的马思聪,第一次听见留声机里传来德彪西的音乐时,才几岁,他蹲在地上,把耳朵贴着地面,仿佛连蚂蚁爬行的声音都能分辨出高低起伏,音乐对他来说不是抽象的乐理,而是生活里呼吸一样的存在,十一岁,哥哥带他踏上前往法国的旅程,他被安置在巴黎一间小小的音乐室里,白天练琴,晚上听街头艺人拉手风琴,那时的他或许还不懂什么是命运,但拉琴的手已经知道该如何走向世界。 马思聪初次登台演奏时,巴黎的观众惊讶于这个东方少年的技艺,报纸上出现了对他的赞誉,但他并没有在掌声中迷失,他知道,自己要做的不是复制西方的技巧,而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他开始思考,如何让中国的旋律在世界的音乐厅里响起,多年之后,他回到祖国,带着西方的音乐教育理念,也带着一颗不肯妥协的心。 1930年代,他在珠江边上创办音乐学校,做出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疯狂的决定:请民间艺人走进课堂,他把咸水歌、粤剧片段改编成室内乐,学生们一边学着西洋乐理,一边听着琵琶和唢呐,他常说,西方的小提琴要能奏出岭南的丝竹味道,才算真正扎根,这个理念后来贯穿了他的整个教育生涯,他招收学生不看家庭出身,不问背景,只要有音乐的直觉,哪怕不识五线谱,他也愿意倾尽心力栽培。 中央音乐学院成立时,马思聪是首任院长,他亲自设计课程,带教授们自己钉课桌,甚至扒在琴房墙外听学生练琴,以便不打扰又能听出真功夫,林耀基、盛中国、傅聪、刘诗昆这些后来响彻世界音乐舞台的名字,几乎都曾被他一耳朵听出天赋,然后亲手送上更高台阶,他不仅是老师,更像一个音乐世界的建筑师,用最朴素的材料,筑起一座属于中国的音乐殿堂。 1950年代,《思乡曲》在广播电台播出时,有人说它像风吹过故乡的麦田,也有人说它是游子心头的泪水,这首作品改编自蒙古民歌,却被马思聪赋予了全新的色彩,他用小提琴拉出一种不言而喻的情绪,像是对土地的依恋,也像是对远方家人的思念,每当这首曲子响起,无数身在异乡的人便仿佛看见了家门口的老树。 然而,命运并未因他的贡献而温柔以待,1966年,当全国的空气都变得紧绷,小提琴忽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象征”,马思聪也被推上风口浪尖,原本欣赏他、敬重他的学生,有人开始远离,有人悄悄道别,他的家门前贴满标语,院子里再也听不到琴声,他被送进“社会主义学院”,不是为了研究音乐,而是为了接受批判和改造,那是一段无法用语言完全描述的日子,他每天要写检讨,揭发熟人,还要重复一些自己根本不相信的话,他曾在泥地里,用草秆画出五线谱,悄悄练习指法,只为在心里保留一点音乐的光亮。 最重的一击,是广播台停播了《思乡曲》,那不是一首曲子的消失,而是他心头最后的希望被熄灭,他曾相信,只要这首曲子还在播放,就说明他还没有被彻底否定,但当那熟悉的旋律不再响起时,他知道,留在这里,可能只会等来更深的绝望,1967年初,马思聪筹来五万港币,找人带路,从深圳偷渡到香港,再从香港前往美国,那一刻,他没有告别,也没有回头。 在美国,他没有申请政治庇护资金,也没有借助政府资源,他靠拉琴和作曲维持生活,住在简朴的小公寓里,墙上挂着齐白石和张大千的画,家具用品多是唐人街淘来的中式旧物,他仍旧泡茶、做饭,用扫帚打扫阳台,用中文写信给远方的亲人,他虽然漂泊在外,却从未让自己成为一个“离根”的人,有人称他为“叛徒”,也有人说他是“逃亡者”,但他从不回应,也不争辩,他只是继续谱曲,继续演奏,把思念、痛苦和坚持都化进琴声里。 1970年代后期,他得知国内局势逐渐改变,曾试图联系文化部门请求回国讲学,他写了十四封信,都没有得到回应,最后一封信没寄出去,他写在信纸上:“如果不能回到北京,是否可以先到深圳河边拉一曲《思乡曲》,听完再抓我也心甘,”这句话没有被送达,但却成了他心中最真切的呼唤。 1987年,马思聪因感冒引发肺炎,最终引发心脏病,5月20日,他在费城的病房中离世,享年76岁,病床旁的手稿还未完成,琴盒中的那块红绸布已经褪色,那是他离开北京时妻子塞给他的东西,它陪伴他度过二十年流亡岁月,也见证了一个音乐家怎样在困顿中守住自己的信念。 直到2007年,骨灰被送回广州安葬,他终于回到了祖国的土地上,纪念馆为他而建,奖学金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作品在各种舞台上再次奏响,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他,重新理解那段被遮蔽的历史。 信息来源:马思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