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组织派人找到浦安修,向她移交了补发给彭老总的48000元工资稿费这及一些私人物品。浦安修有些犹豫是否接受,来人告诉浦安修:“您和彭总的离婚申请组织上没有批准,您还是彭总的夫人。”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1979年,组织将一笔钱送到浦安修手中,总额四万八千元,那天她正在单位上班,工作中途被叫出办公室,一位从总政来的干部将一只封口严实的布袋放到她面前,说是彭德怀留下来的工资、稿费、抚恤金和一些生活用品。 她第一反应是拒绝,语气坚决地表示这笔钱她不能收,事情立刻起了冲突,来人态度很坚定,说这不是个人恩情,是组织决定,已无退让余地。 浦安修当场起身说她早就与彭德怀不再往来,这些年也没有一点联系,她表示自己已经与他脱离了夫妻关系,不愿以这种方式再和他产生关联。 来人并没有急着收回布袋,而是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复印件,说浦安修曾在1960年代提出过离婚申请,但组织查阅当年档案,发现离婚申请没有获批,手续也未曾办理,因此从组织角度,两人仍然是合法夫妻。 浦安修再次表示拒绝,说自己没有资格,也没有立场替他处置这些东西,来人没有再坚持,只是留下那只布袋,说组织意见已传达完,是否接受由她自行决定。 她没有立刻动那只布袋,而是静置在屋里整整三天,直到第四天,她才打开查看里面的内容,浦安修盯着那一摞纸,看了很久,最终将全部资料和物品登记封存,报备给组织,表示愿意按照原则妥善处理,但不接受私有。 浦安修没有动用一分钱,而是按照名单召集了彭德怀生前的工作人员、亲属和与其有关的几位同事代表,在单位小会议室开会商量如何处理这笔遗产。 会上,她提议将其中一部分捐给湖南家乡的教育单位,一部分发放给生前照顾过彭德怀的人员,并从中划出四千元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后续文稿和历史资料整理。 剩下的资金她主动向军委提出交回国家财政使用,这些决定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她多年来对这段婚姻,对那场分别所做的深层思考。 浦安修与彭德怀的婚姻,开始于延安时期的介绍安排,她当时是北师大的一名学生,刚刚接受组织调派到边区,二十一岁,尚未有过婚恋经历。 而彭德怀已经年近四十,在部队多年,曾有过两段破裂的情感经历,他最早的婚姻是一段家庭包办的婚配,婚前只见过几面。 那段婚姻在他参军后自然中断,女方因为家境所迫,不堪压力而选择自尽,令他多年后都未能释怀。 第二段感情是在战争中偶然相识的一位青年女子,虽有情感,但最终因战乱分离多年,女方已另嫁他人,直到1938年,他与浦安修结婚。 婚后,他们几乎没有真正一起生活过,抗战时期,彭德怀长期在前线作战,浦安修则在后方从事教育和妇女工作,彼此通讯甚少。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各自承担不同任务,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局势骤变,浦安修受到牵连,被多次叫去谈话检查,压力之下,她曾写信劝彭德怀作出姿态,表达立场,却未获回应。 1961年底,在一场极其压抑的氛围中,两人见了一面,那次见面中无争吵无哭泣,只是共同吃了一个梨,她没有说“分离”,但心里明白这一餐是结束。 之后她向单位提交了离婚申请,但组织并未批准,也未做进一步处理,从那之后,两人再未通信,也未见面。 1974年,彭德怀重病,临终前通过医护人员表达希望见她一面,组织向浦安修传达了请求,她本表示愿意,但几天后突然高烧,未能成行,最终由北师大党委以“当前情况不适宜前往”为由否决了行程。 彭德怀去世后,她没有前去吊唁,也未出席追悼,直到几年后,彭德怀平反,组织开始整理他遗留的问题,才重新联系上她。 处理这笔遗产资金只是一个开始,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浦安修开始主动整理彭德怀的历史资料,她从单位申请调阅档案,查找过往通信记录,访问曾与彭德怀共事的老战友,协助文史部门还原彭德怀的重要讲话稿、军事文电和内参意见。 她没有发表个人感言,也未公开亮相,但文稿中的批注、时间线的勘误、资料的重新核对,几乎全部出自她一人之手。 除了资料整理工作,她还参与协调相关部门为部分因彭德怀案受到牵连的干部平反,推动为彭德怀修建纪念设施和校史馆陈列,尽最大可能弥补未曾完成的告别。 她没有再婚,也未接受新的行政职务,终身未将“彭德怀夫人”的称谓写入任何官方简历,1991年,她因病去世,未留遗嘱,也未留下私产。 她的骨灰按照生前请求,未与彭德怀合葬,只由亲属低调安置于北京一处公墓,四万八千元终究没有成为她的生活依托,但却成为她余生所处理的唯一一项关于彭德怀的“个人事务”。 (主要信源:党史博采——浦安修向组织提出和彭老总离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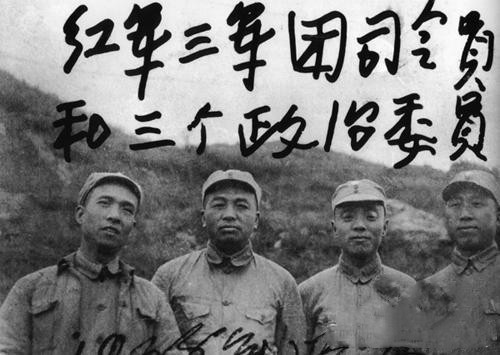

用户15xxx43
患难见真情!我们没有资格去评价那个时代的有些人和事。感觉出来她心里是悔恨的,但已无可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