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回1985年,我那时在省城一家国营厂上班,日子虽然清苦,但也算稳定。大姑的电话让我彻夜难眠,躺在宿舍硬邦邦的床上,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就像一部老电影,在脑海里反复放映。
我还记得十年前,我刚工作那会儿,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兴冲冲地买了一台收音机。那年月,收音机可是个稀罕玩意儿,我特意托人把它带回乡下,送给了大姑。见到收音机的那一刻,大姑笑得像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抱着它,就像抱着一个珍贵的宝贝。那笑容,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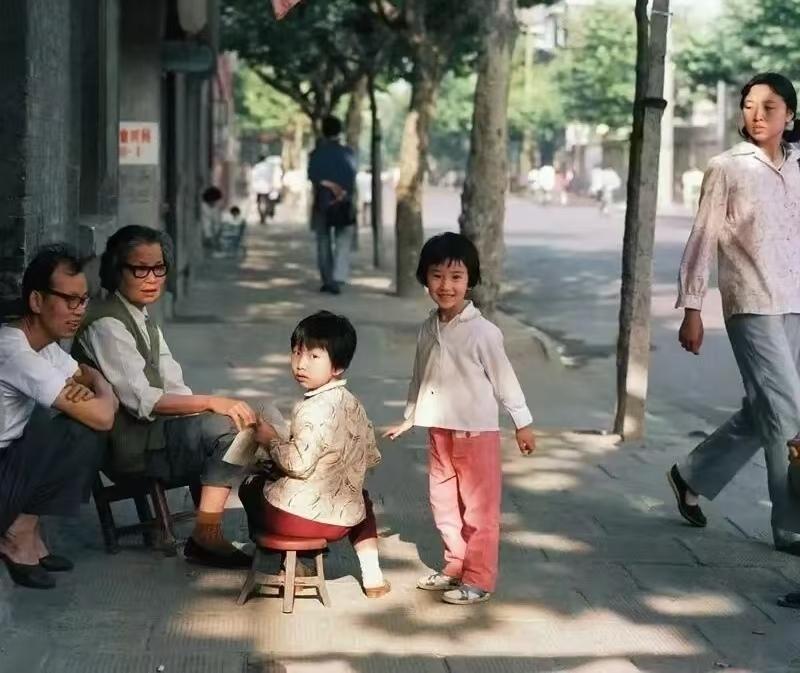
更早一些,1975年的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病魔,夺走了大姑夫的生命。那时候农村医疗条件差,大姑带着大姑夫一路颠簸,四处求医,最后还是没能留住他。为了给大姑夫治病,大姑几乎倾家荡产,甚至连祖传的铜火锅都当掉了。我妈也赶去帮忙,可最终还是无力回天。那年我才十来岁,懵懵懂懂,却清楚地记得大姑跪在病床前,紧紧握着大姑夫的手,泪如雨下,那一幕,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年幼的表哥韩明亮,紧紧抱着大姑的腿,哭得撕心裂肺。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和药水的味道,混合着悲伤的气氛,让人喘不过气来。
35岁的大姑就这样成了寡妇。村里那些嚼舌根的人,闲言碎语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有人说她命苦,有人劝她改嫁,还有人把她和隔壁的李寡妇比较,说她死心眼。可大姑就像一棵坚韧的小草,迎着风霜雨雪,顽强地生存着。她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挣着微薄的工分,晚上还要纺线织布补贴家用,一分一厘地攒钱,就为了供表哥读书。

我记得有一年暑假去大姑家玩,正值盛夏,天气闷热,蚊虫肆虐。我和表哥坐在门槛上乘凉,看见大姑在昏暗的月光下纺线。她手上全是老茧,有的地方甚至裂开了口子,渗着血丝。表哥坐在油灯下写作业,灯光昏黄,他不得不把头埋得很低,才能看清书上的字。他心疼地说:“娘,你手都流血了,歇会儿吧。” 大姑却笑着说:“没事,这点活不算啥。” 就像一位辛勤的园丁,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浇灌着希望的种子。
那时候村里很多孩子都早早辍学,去砖窑干活挣钱。但表哥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后来,他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大姑高兴得像个孩子,可高昂的学费却让她犯了难。那年秋天,庄稼歉收,连口粮都成了问题。开学前,表哥懂事地提出要辍学,帮家里减轻负担。那天晚上,我听到大姑在房间里偷偷地哭,她哽咽着说:“你爹临走时就念叨着要你好好读书,娘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念完书。” 第二天天还没亮,大姑就拿着自己织的布去集市上卖,又四处跟邻居借钱。晚上回来的时候,她脚都肿了,却依然笑容满面地对表哥说:“明亮啊,娘给你凑够学费了,明天咱们去县城报到。” 那一刻,我觉得大姑就像一座山,为表哥遮风挡雨,支撑起一片天。

听到表哥要结婚的消息,我立刻请假买票,踏上了千里迢迢的旅程。当时的火车票非常紧张,多亏了机修车间的老张帮忙,才买到一张硬座。绿皮火车一路哐当哐当,从省城到湘西山区要两天两夜。车厢里拥挤不堪,我几乎站了一宿。邻座是一位戴着草帽的老大爷,听说我去参加表哥的婚礼,特意分了我半个座位。他笑着说:“你这表哥,听你说的真是个有出息的。现在能在县城开店的年轻人可不多啊。”
火车到县城后,还要再坐三个小时的班车才能到村里。山路崎岖,车子颠簸得厉害。车上挤满了人,还有几筐叽叽喳喳的小鸡,旁边一位年轻的母亲,正抱着孩子喂奶。一路的颠簸,让我感到疲惫不堪,但想到即将见到大姑和表哥,心中又充满了期待。

等我到达大姑家时,月亮已经高高地挂在空中了。大姑家还是那间老屋,土墙泥地,堂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散发着昏黄的光芒。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是大姑熬的红糖姜茶。小时候每次去她家,她都会给我煮这个。大姑递给我一碗热气腾腾的姜茶,说:“快来喝口热乎的,去去寒气。” 捧着这碗姜茶,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表哥的媳妇叫张巧云,是邻村的姑娘,长得小巧玲珑,在供销社当售货员。她和表哥在集市上认识,两人一见钟情。巧云性格活泼开朗,嘴也很甜,一进门就亲热地喊“大姑”,把大姑哄得合不拢嘴。看得出来,大姑对这个儿媳妇非常满意。她拉着我的手,眼角泛着泪光,说:“你看看,这孩子多懂事,一进门就知道帮我干活,比我自己闺女还贴心。” 就像久旱逢甘霖,大姑终于迎来了幸福的曙光。

家里地方小,亲戚们都打地铺。晚上躺在稻草铺上,听着屋外的虫鸣,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想起这些年表哥读书的艰辛,大姑省吃俭用给他买书本,冬天自己穿着打满补丁的棉袄,却给表哥买了新棉衣。表哥也非常争气,高中毕业后去县城学了修理工。那时候学费不便宜,大姑毅然决然地卖掉了家里唯一值钱的缝纫机,供他学习。
婚礼前一天,表哥带我去他的修理铺看了看。铺面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墙上挂满了各种工具。他递给我一根烟,感慨地说:“要不是大姑,我早就跟着村里的娃儿去砖窑了。这几年,修理铺的生意还不错,能养活一家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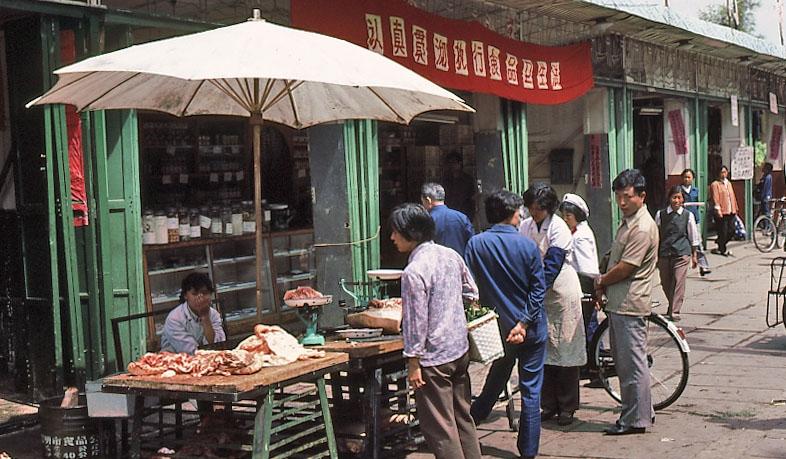
婚礼当天,鞭炮声震耳欲聋,热闹非凡。大姑忙前忙后,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看着表哥和巧云穿着新衣,给大姑敬茶,大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巧云的父母也来了,看到女儿和表哥如此般配,也是笑得合不拢嘴。席间,巧云的父亲端起酒杯,走到大姑面前,动情地说:“大姐,这些年你把明亮培养得这么好,我们家巧云跟了他,我们心里踏实。以后啊,就是一家人了。”
临走那天早上,我收拾铺盖时,发现地上有一块湿痕。后来才知道,原来每天夜里,大姑都悄悄地起来给我们掖被子。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是这样,默默地付出,从不言苦。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和佝偻的背影,我的心里涌起一阵酸楚。
大姑送我到村口,硬塞给我一包她亲手织的毛线手套,那是她熬了几个晚上赶出来的。坐在回程的火车上,我摩挲着手套粗糙的纹理,眼眶湿润了。这哪里是一双手套啊,分明是大姑几十年来的爱与坚韧,像一颗颗珍珠,串联成一条闪耀的光阴项链。
窗外的景色飞逝而过,我想起前几天表哥说的话:“娘这辈子太不容易了,好在老天爷待我们不薄,让我找着了巧云。以后我们小两口一定好好孝顺娘,让她享享清福。” 是啊,人这一辈子,没有什么比亲情更珍贵。大姑用她的一生,编织了一个平凡而温暖的家,而这份温暖,将会永远传递下去,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