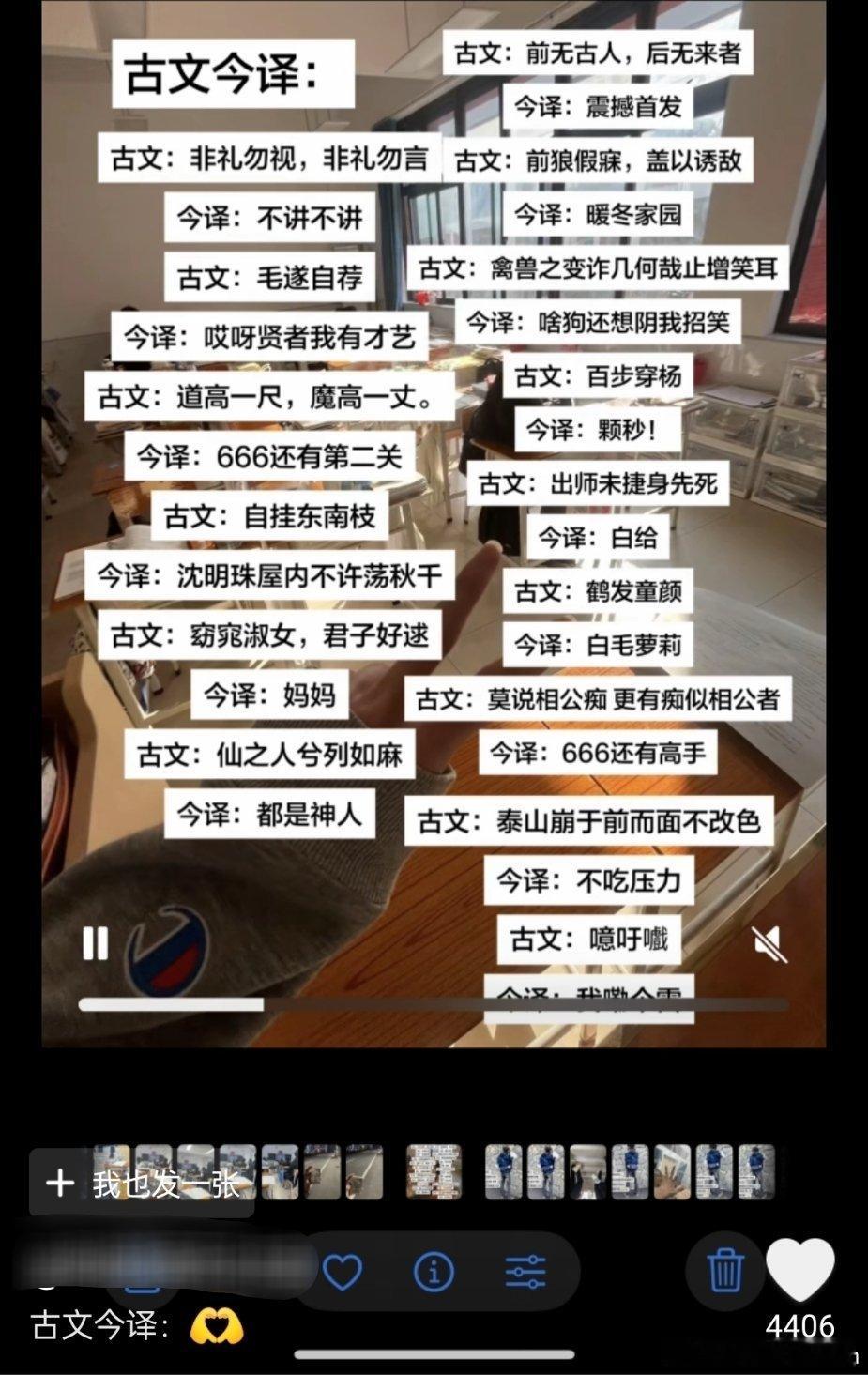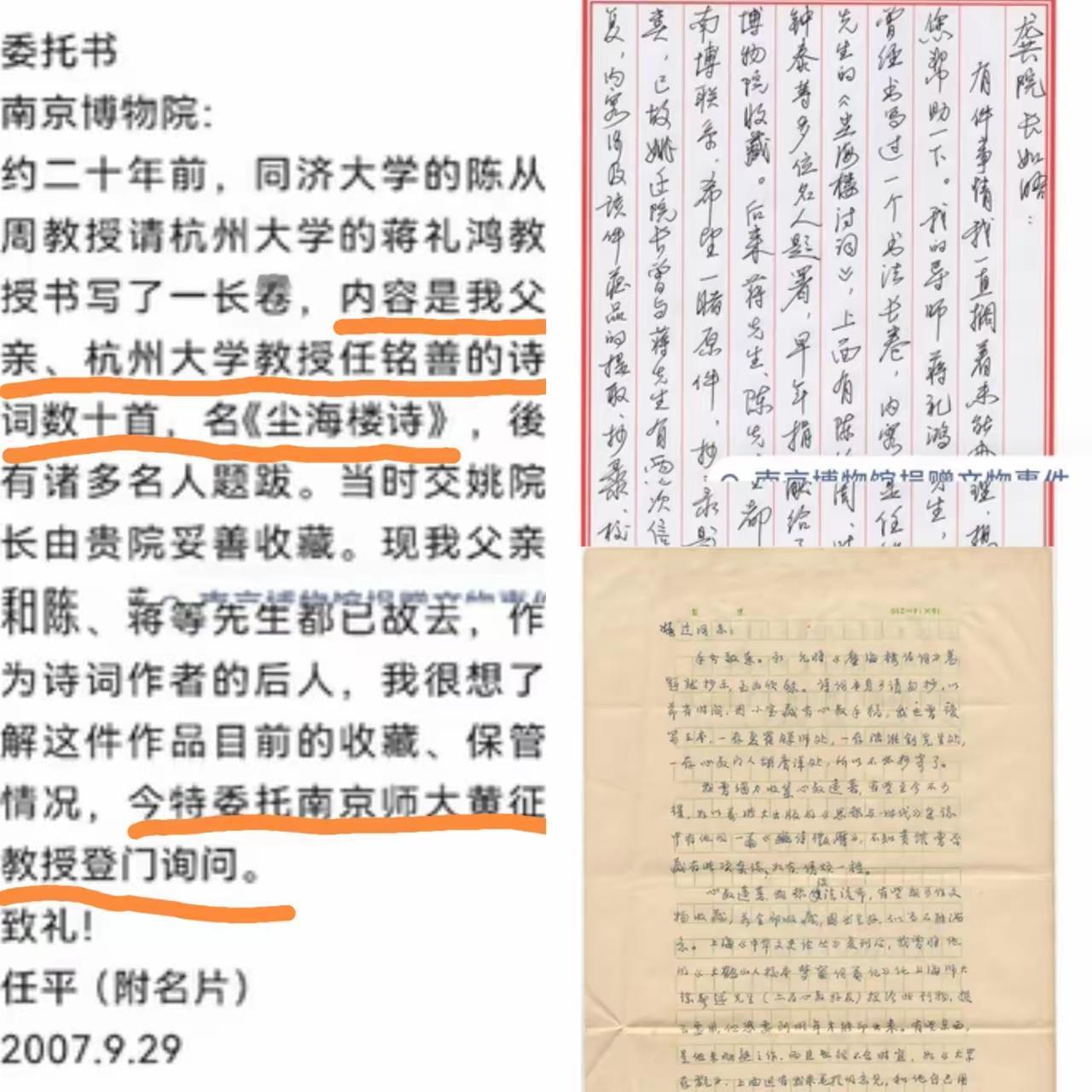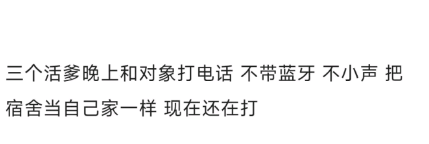1986年10月12日傍晚,福州西湖宾馆灯火初上。应邀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料”审校会的钟国楚刚把稿件放下,就听见一位老同志压低嗓门提到“闽赣省苏主席杨道明如今还在世”,一句话像炸雷般击中他的神经。杨道明?那不是1935年5月紫山突围中被国民党登报“击毙”的烈士吗?会议室瞬间安静,几双目光对视,谁都说不出话来。
当晚回到下榻的房间,钟国楚翻出随行医生给他准备的安眠药,却怎么也咽不下去。他回想起半个世纪前的闽赣山林:硝烟、哨声、黑夜里匍匐前进的影子,还有那个总把“队伍带上山”挂在嘴边的年轻省主席。1934年8月,毛泽东在瑞金临别时的嘱托言犹在耳,而今人居然未死,还成了高僧,这消息实在离奇。

把时间往前拨回1909年,江西兴国河西乡隘前村的冬夜寒得透骨,杨家第三个孩子呱呱坠地。二十多年后,他在圩镇誓师大会上被毛泽东一眼相中:“这伢子能干。”短短四年,乡财政委员到中央政府内务部副部长,履历上每一行都透着血汗。
可1934年底,红军主力长征,闽赣省成了孤岛。省军区仅剩两团,粮弹奇缺,士气低迷。中央最后一封电报传来:“自主坚持游击。”杨道明硬是把三百多人带进戴云山脉,靠老乡送来的一篮番薯支撑。紫山之夜,敌人灯火连成一线,参谋长徐江汉心生去意,叛变导致阵脚大乱。5月8日清晨,枪声、哨声、哭喊声混作一团。等杨道明冲出包围,身边仅剩不足二十人。
后世档案里写着“杨道明被击毙”。事实上,他拖着伤腿在月洲山洞躲了两天,随后改名谢长生,与钟循任分头突围。永泰与尤溪交界的音亭寺香烟缭绕,方丈见他憔悴,还是留了口饭。1935年8月2日,削发仪式举行,法号“磬扬”,从此青灯之下苦修,为的是活下去,找机会重回组织。

抗战爆发,他曾试着同闽中地下党接头,因一场高烧错过。1945年击毙保安分队长的枪声传来,他连夜被捕。福州高院拖了一年多,最终因证据不足释放。那年夏天,他已是清瘦的中年僧人。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电视里高唱《东方红》,寺庙的瓦檐却滴下雨水。磬扬大师抚着木鱼,自问还能替革命做什么。他带僧人开荒种粮,每年向国家售粮五百公斤;乡政府缺文书,他挥笔抄写文件;年迈孤寡,他悄悄送米送油。外界却仍不知“烈士归来”。
1966年,久别的二哥杨真明从兴国来信,才炸开这颗尘封的“秘密”。省民政厅、县革委纷纷派人核实。身世大白之后,有人劝他还俗返政,他摇头笑答:“此身已属空门,但心向红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落地。磬扬被推举为福建省佛协副会长、永泰县政协常委。他不领薪水,却用声望募集二十多万元,修复重光寺、仙佛寺、方广寺;又带人凿山修路,为光荣院老人送粮送衣,成了远近闻名的活菩萨。
听完这一切,1986年10月14日上午,钟国楚带着氧气袋,驱车三个多小时上山。音亭寺的石阶湿滑,八十高龄的他走得气喘,却坚持不用搀扶。寺门前,身披灰袍的老僧已合十相迎。无需介绍,两只满是老茧的手紧紧相握。
“老杨,你还在,真好。”钟国楚哽咽。磬扬大师低声回道:“组织没有忘我,我也没忘组织。”短短十二字,浓缩半个世纪的生死荣辱。

接下来的两天,两位八旬老人席地而坐,翻地图、对地名,把30年代闽赣游击区的战斗经过一笔笔补写,填了党史最缺的空白。临别前,钟国楚留下三句话:“护好佛门,写好史料,好好活着。”磬扬大师合十答应。
1999年5月14日,晨钟未响,磬扬大师在静坐中圆寂,享年九十。音亭寺檐下,老僧们将青灯添油,又敲响木鱼三千声。寺外新修的山路通向远方,正是他生前一斧一凿筹款打下的基石。
回望福州那场审校会,若非偶然的一句闲谈,历史或许仍停留在“1935年牺牲”的记录里。杨道明用半世青灯,守住了对信仰的承诺;当年闽赣游击区那点星火,也因这桩“死而复生”而重新被人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