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起、陈洪:王嘉《拾遗记》与“拾遗”类小说的演进
《拾遗记》又称《拾遗录》或《王子年拾遗记》,最初由后秦道士王嘉编撰,经南朝萧绮整理辑录而成。

明刊本《拾遗记》
该书载录君王轶闻、异能神迹、谶纬灾异,篇末一卷记昆仑、蓬莱等仙家名山。《拾遗记》的体例历来颇受关注。李剑国先生称其为“杂史体志怪”[1],也有论者认为该书是杂传与地理博物结合的产物,具有“一书兼二体”的特征[2]。
陈文新先生《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将《拾遗记》作为文言小说的一类,名之曰“拾遗体”,认为“拾遗体是杂传、博物体、搜神体在辞赋的藻饰之风濡染下结合而成的”[3]。
“拾遗体”是今人对古小说的体类划分。相比“志怪”“博物”“宣教”等早期小说,“拾遗小说”与史传的关联更为紧密。
相关作品,如王嘉《拾遗记》、葛洪《西京杂记》、佚名《汉武帝内传》《汉武帝故事》,体现了遗事轶闻由史料转化为小说的过程。唐代之后,拾遗小说又有发展,出现《开元天宝遗事》《大业拾遗记》等历史小说的雏形。
以往小说研究对此虽有论及,然而,对于拾遗类小说的内涵、外延及其衍变发展的小说史意义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拾遗记》的两次编纂及其所效“纪传”之体
《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载录了两种《拾遗记》:
一为《拾遗录》二卷,题“(后)秦姚苌方士王子年撰”;又有《王子年拾遗记》十卷,题“萧绮撰”[4]。
王嘉,字子年,道家方士,生卒不详,主要活动于后赵至后秦之间(约为四世纪中后期),史载“石季龙(石虎)之末,(王嘉)弃其徒众,至长安,潜隐于终南山”[5]。嘉后为姚苌所害。至于萧绮,史传无载,齐治平点校《拾遗记·前言》推断他是南朝萧梁宗室[6],大体可信。
《拾遗记》的编纂经历两个阶段。该书最初题名应为《拾遗录》,即《隋志》所录“二卷本”,编纂者是王嘉,书中提及“石氏破灭”,成书当晚于后赵亡国(公元351年)。

《王嘉与拾遗记研究》
南朝萧绮整理旧本,在文中增加评述,又作重新编排,故有《隋志》所载十卷本的《王子年拾遗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分别著录两卷本、十卷本的《拾遗记(录)》。南宋之后的官私目录,仅见有萧绮整理的十卷本,两卷旧本应是在宋代之后失传。
今本《拾遗记》卷首载录萧绮的序文,从中可见《拾遗记》体制原貌及萧绮再编要旨,序文节录如下:
《拾遗记》者,晋陇西安阳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为残缺……文起羲、炎已来,事讫西晋之末,五运因循,十有四代。王子年乃搜撰异同,而殊怪必举,纪事存朴,爱广尚奇。宪章稽古之文,绮综编杂之部,《山海经》所不载,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记矣。辞趣过诞,意旨迂阔,推理陈迹,恨为繁冗;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妙万物而为言,盖绝世而弘博矣!世德陵夷,文颇缺略。绮更删其繁紊,纪其实美,搜刊幽秘,捃采残落,言匪浮诡,事弗空诬……随所载而区别,各因方而释之,或变通而会其道,宁可采于一说。今搜检残遗,合为一部,凡一十卷,序而录焉。[7]
据萧绮序言,王嘉《拾遗记》记载了羲皇至西晋的奇闻异事,“十有四代”即三皇(伏羲、炎帝、皇帝)、五帝(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夏、殷、周、汉、魏、晋,“五运因循”附会了“五德终始”之说。对比十卷本《拾遗记》纲目,可知萧绮整理旧本,基本沿用了原书的体制结构。

明万历间汉魏丛书本《王子年拾遗记》
《拾遗记》以历代君王为纲目,采摭各个时期的历史轶闻、奇人异事。书中所载君王,皆烜赫一时,颇富有传奇色彩。如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穆王、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在正史中的记载虚实相间,坊间传闻也累世不绝。
王嘉采摭旧说,以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帝王为中心,勾连同时代的奇人异事。如卷三“周灵王”一章,旁及孔子神异降生、韩房献玉以及师旷、老聃、师涓、子韦等人奇遇,篇末又附录范蠡隐退一事。
在以往的研究中,《拾遗记》或被认为是杂糅各体,主要依据是该书在内容上近于“志怪”,材料编排类似编年,再加之书中有专章记述神山,与地理博物相似,故有“一书二体”“一书多体”之说。
事实上,《拾遗记》主要效仿的是纪传体通史,在体制上融合了本纪与列传的特点。具体而言,帝王之事可视为“本纪”,奇人异事可看作“列传”。至于文末所记神山,则是仿照《史记·货殖列传》《汉书·沟渠列传》。
《拾遗记》脱胎于史家纪传,《隋志》将其并入杂史。随着小说观念的演进,宋代之后的目录家因该书近于志怪,转而称其为小说。
《拾遗记》效仿纪传之体,并非偶然。汉魏六朝,有一些和《拾遗记》相似的作品,如《帝王世记》《三五历记》。这些作品虽已散佚,却可据佚文知晓其大概。

《隋书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王齐洲、汤江浩、黑金福编纂,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如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述三皇以来历代帝王的事迹,可以说是历代君王的本纪。三国时,徐整编有《三五历纪》,叙三皇五帝开天辟地之事,也是以纪传为体,史实与传闻相杂。
上述作品连同《拾遗记》,都属于仿效纪传体史书的野史杂传。纪传或传记的优势在于突出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吸纳各种史料,且能够根据人物身份之不同,因事、因言而记人,体制严整却不失灵活。《拾遗记》所记人物,有君王,也有方士,上下相悬甚大,史料性质也不尽相同,以纪传为体是最合理的选择。
《拾遗记》依托纪传之体,既可提升野史传闻的史学品质;也可以整齐神异叙事,为作品的传世创造条件。萧琦称王嘉有“搜撰异同”之功。所谓“异同”,主要针对前代典籍已载或未载之事。神异之事,本不成篇什,王嘉却能将零散的奇闻轶事结撰成篇,足见作者镕裁之心。
譬如,书中“秦始皇”条记始皇遇骞霄国画工“含丹青漱地,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象”[8],又云“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9]。上述记载皆不见于前代文献。苏秦、张仪遇鬼谷子,《史记》《论衡》虽有涉及,却与《拾遗记》互有异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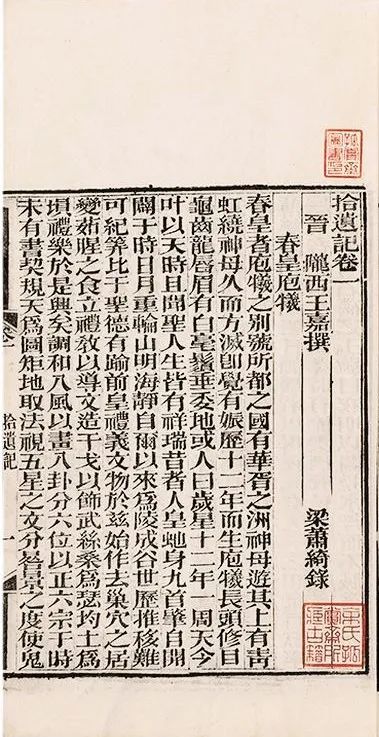
清光绪崇文书局刊本《拾遗记》
再如卷三记“穆天子”乘八骏巡游,《史记》《博物志》以及西晋出土的《穆天子传》皆有提及,《拾遗记》所载更为丰赡华丽。
王嘉长于卜筮,史载其能“言未然之事,辞如谶记,当时尟能晓之,事过皆验”,“苻坚累征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参诣,好尚之士无不师宗之”[10]。正如许多陷入政治纷争的方士,王嘉因为得罪姚苌而死于非命。
汉魏之际,游走朝野的方士将占卜之术、谶纬神学及天师道术法相结合,言说灾异,变幻莫测,祥瑞奇迹,一时竞起。《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了费长房、左慈等奇人异士。三国、魏晋之间,又有管辂、于吉、葛洪神通灵验,事迹广见于史传杂记。
王嘉“好为譬喻,状如戏调”[11]。所谓“譬喻”,即借彼喻此。桓谭《新论》论小说曰“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12]。
寻其名义,乃是以故事陈说道理。而“戏调”,即谐谑。《史记•滑稽列传》载优孟、淳于髡、东方朔等机巧善辩之士,多能剧谈。葛洪《抱朴子·行品》云“士有机变清锐,巧言绮粲,揽引譬喻,渊涌风厉”[13]。
王嘉生前善于言说故事,结合其方士身份,《拾遗记》是要借纪传之体为方士张目。王嘉以历史上神异故事宣扬神秘主义,暗示冥冥中神异的存在,变幻莫测的道术则是沟通现实世界与神秘力量的途径,史家的纪传之体为其所用也在情理之中。
《拾遗记》经萧绮再次编纂,内容、体制均有变化。萧绮对《拾遗记》文辞多有润色。正如萧《序》所云,旧本《拾遗记》“辞诞迂阔”,有“繁冗”之弊。萧绮征实其迹,删繁就简,提升了作品的可读性。今本《拾遗记》辞气顺畅,似经过镕裁藻饰,其中多有萧绮之力。

中华书局整理本《拾遗记》
萧绮重整《拾遗记》,体制上最明显的改变莫过于增加了“录”。“录”原本是纪事之体,《隋志》载有《南燕录》、汉末赵歧《三辅决录》。萧绮的“录”或在文末,或在文中,形式类似纪传体史书的论赞。萧绮的“录”用以诠释《拾遗记》所载之事,主要作用有三:
一、补充史料,征实其事。如“三皇”条,引录《周易》补叙伏羲之事,以经典所载补王嘉所记。
二、以史为鉴,议论得失。如西晋亡国,萧“录”总结道“四夷侵掠,骄奢僭暴,擅位偷安,富有之业,莫此比也”[14],算得上是颇有见解的史评。
三、考辨神异,阐幽发微。萧绮将历史征实与神道诡异相调和,如在大禹事迹评述中,萧绮之“录”既承认“神迹难求,幽暗罔辨”,又辩称“远古旷代,事异神同”[15],试图弥合历史叙事中尚实与神异的矛盾。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
萧绮通过完善文体,将《拾遗记》纳入史学范畴。然而,“萧录案语”又体现了南朝史学的时代特色。
一方面,圣王之道、春秋之法仍然主导史家话语;另一方面,自汉代以来的谶纬之学融入历史,神异之事有了更为合理的阐释。
萧绮的史学思想在南朝颇具有代表。史载南朝萧梁整理谶纬典籍,《文心雕龙》也有《辨纬》一章,讨论谶纬之学的文学意义,是“文之枢纽”的一部分。
谶纬史观给予神话传说、奇闻轶事乃至鬼神之说极大的生存空间,《拾遗记》也因此形成两种话语:一种是王嘉的神秘主义世界观,宣扬神道信实不虚;另一种便是以天人感应统摄神道与人道,将神异之事纳入史家正体。两种话语共存于同一作品之中,相互激荡而呈现出斑驳陆离之象。

二、拾遗类小说的形成
汉魏六朝时期,有几部与《拾遗记》类似的作品,如托名刘歆的《西京杂记》、殷芸《小说》以及撰人不详的《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
上述作品依据旧有史料辑录整理而成,兼有杂传、杂记之特点,是史传向小说的过渡。在此不妨以王嘉的《拾遗记》为代表,名之曰拾遗类小说。
之所以名之曰“拾遗”,而不是“西京”或其它题名,主要是“拾遗”二字最能体现此类作品的特点。常言“路不拾遗”,《战国策》《史记》早有此成语[16]。在汉代,又有类似谏官职能的“拾遗之臣”[17],司职查漏补缺,建言献策。

《说苑校证》
“拾遗”一词用于著述,便以野史杂记补史之阙,采摭史、子之文集腋成裘,与早期遗闻轶事类小说的内涵颇为贴切。
拾遗类小说的出现与文献整理有关。西汉刘向编撰的《说苑》《新序》便是史料拾遗的成果。史载刘向任校书郎,据中书典藏,辑得《说苑》《新序》《列女传》。
《说苑》主要收录周汉间的轶闻轶事,内容多载士人言谈,颇似《国语》。为了方便使用,《说苑》分“君道”“臣术”“建本”“立节”等二十专题,人物故事各以类从。
《说苑》之外,刘向另有《新序》传世,内容与《说苑》互有重复,经编者删繁去冗,独立成书。
今本《新序》十卷,除去“刺奢”“节士”“义勇”“善谋”等专章,另有五卷署名“杂事”。所谓“杂事”,大多见于周汉文献。如“晋文公逐麋”见于《左传》,“曾子杀人”见于《战国策》。

《刘向评传》
刘向编撰《说苑》《新序》,将其作为基础史料,供日后之需,取材范围不限于高文大册。曾巩《说苑序》云“向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以为此书”[18]。高似孙《子略》称“先秦古书,甫脱烬劫,一入向笔,采撷不遗”[19]。《说苑》《新序》是刘向校书的副产品,两者是轶闻、传说的文献集成,对后世著述编撰多有启发,其中包括《拾遗记》与《西京杂记》。
《西京杂记》的成书与《拾遗记》有相似之处。
《隋志》史部“旧事”著录《西京杂记》二卷,不题撰人。西晋葛洪为此书撰写序跋,自云“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原书一百卷,“洪家具有此书,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20]。
根据序文,《西京杂记》的第一作者应是刘歆,此说受到后人质疑。余嘉锡称《西京杂记》“盖即抄自百家短书,(葛)洪又以己意附会增益之,托言家藏刘歆汉史”[21]。鲁迅也认为“既托名于歆,则摹拟歆语,固亦理势所必至矣”[22]。作者刘歆说因无旁证,学界仍倾向于将《西京杂记》的编者定为葛洪。
《西京杂记》辑录旧闻,书中的文献来源较为博杂。譬如,“大驾骑乘数”载西汉祭祀典礼的车驾规格,具体而详细,不似好事者捏造。“上林名果异木”,列举上林苑名贵果木百余种,如数家珍,篇末云“余就上林令虞渊得朝臣上草木名二千余种。邻人石琼就余求借,一皆遗弃。今以所记忆,列于篇右”[23]。据此可知,果木清单应源于皇家文献,“余”是记述人,也是转录者。
又如“曹敞收葬”,记平陵吴章为王莽所害,门客曹敞毅然为之收葬,作者自称少时听闻此事。“昆明池中船”言昆明池楼船之盛,篇末云“余少时犹忆见之”[24],又似耆旧追忆往昔见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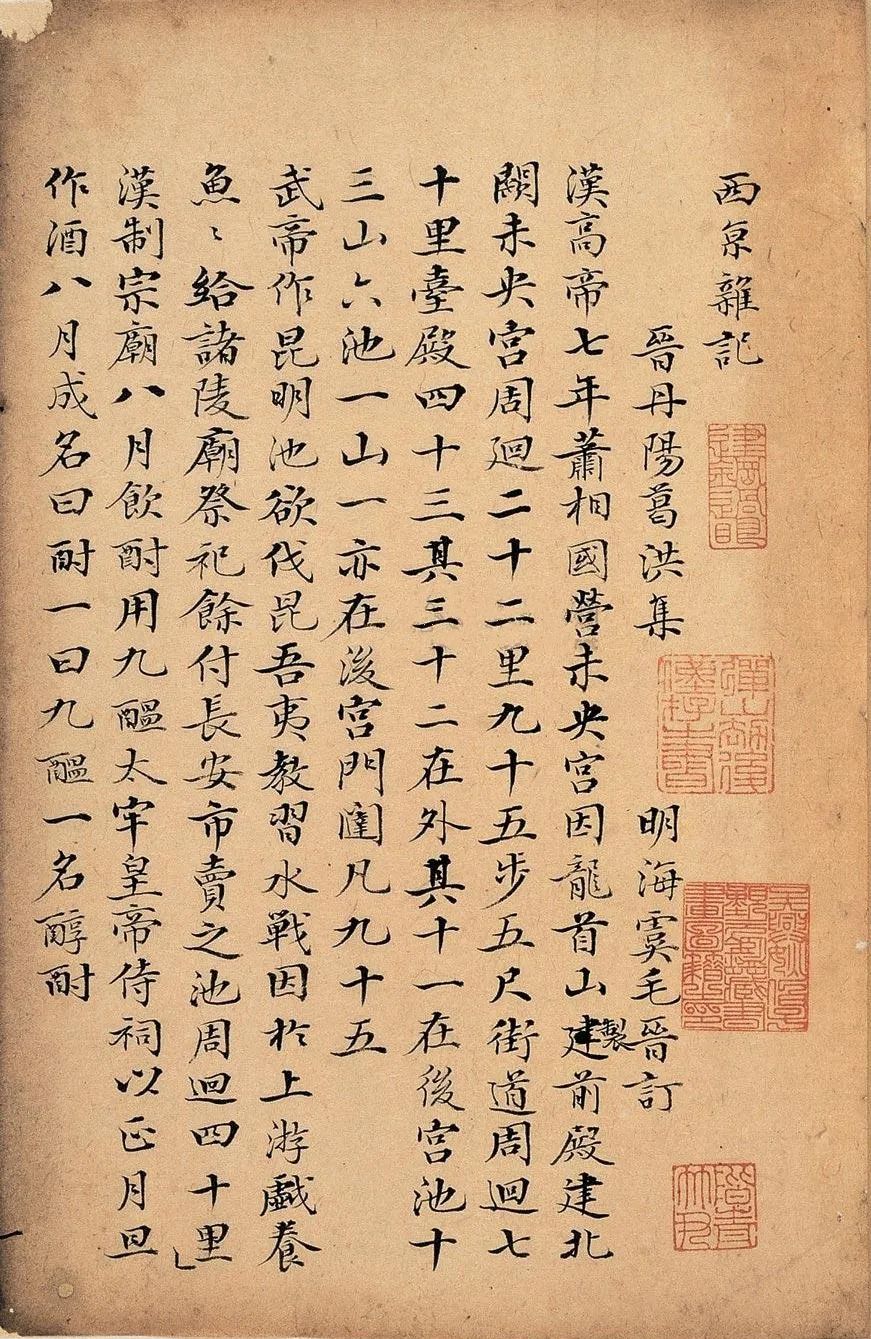
旧抄本《西京杂记》
此外,“匡衡凿壁借光”“忘忧馆时豪赋”“霍妻双生”“画工弃市”,皆西京名人轶事。这些轶事或见于经史杂记,或流布于市井坊间,编者一并收录,又将其中与《汉书》重复的删去。
《西京杂记》在文献转抄中逐渐形成定本,《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也有相似的编撰过程。《故事》《内传》旧题班固所作,通常认为是魏晋后的人伪托[25]。汉武帝刘彻,《史》《汉》皆有本纪。
相对而言,《汉书》主要记述武帝的政治事迹,《史记》偏好武帝求仙之事。东汉以降,有关汉武帝的坊间传闻很多,这些传闻为好事者所喜,成为汉武帝故事系列。
其中,以武帝命名的,除《内传》《故事》,还有《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此外,《十洲记》《西京杂记》《拾遗记》也载有不少汉武帝轶闻。

明刻本《汉武帝内传》
《内传》《故事》是汉武帝奇闻轶事的文献集成,《内传》以汉武求仙为主,拔奇取异,详于武帝与西王母相会;《故事》以武帝一生为线索,虚实相间,俨然是一篇武帝传记。两部作品采摭传闻,辑录成书,体例对史传多有借鉴。
“内传”之体本源于经史之学。《左传》又被称为《春秋内传》,“内传”之外,又有“外传”,如《韩诗外传》。“内传”“外传”体现了“传”与“经”的疏密程度,不少诸子著述也分内、外篇。《汉武帝内传》的编撰者对仙家传说更感兴趣,与西王母相会一事最为离奇。“内传”之称有隐秘之意,足以引起好事者的关注。
《汉武故事》也采用了史家著述之体。“故事”本源于史官。战国典籍,如《吕氏春秋》《韩非子》,称“故事”,意为成法惯例。汉代“故事”由专员司职,供朝廷行政议事。随着史学的发展,“故事”内涵逐渐丰富。
《史记》中的“故事”便倾向于奇闻轶事,如《滑稽列传》褚少孙“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以郭舍人、东方朔、东郭先生、淳于髡、王先生、西门豹补充太史公之书。
魏晋以降,又出现以“故事”为名的著作,如《三辅故事》《汉武故事》《晋建武故事》。这些作品类属野史杂记,所载轶闻,与纪传正史互补。《汉武故事》则以武帝生平为线索,依次辑入轶闻,体制模仿本纪,内容更近小说。
以上所述拾遗类小说大多属于史著范畴,是今人文学视野中的古小说。
《隋志》“小说家”载录《小说》十卷,题云“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26]。殷芸,《梁书》有传,生于齐,仕于梁,卒于大通三年(529年)。殷芸《小说》作于梁武帝时期,成书时间与萧绮整理《拾遗记》相去不远。

《殷芸小说补证》
殷芸《小说》主要记载人物言行,体制与《拾遗记》极为相似:《拾遗记》以时为序,各以人物采掇故事;《小说》模仿纪传体,如卷一“秦汉魏晋诸帝”,犹如本纪;以下九卷:“周六国、前汉人”“后汉人”“魏世人”“蜀吴人”“晋江左人”“宋齐人”,分属列传。殷芸曾任昭明太子侍读,史载其“性倜傥,不拘细行”,“励精勤学,博洽群书”[27]。
《小说》以奇闻轶事为主,史源广泛。如曹操、袁绍抢亲,出自《世说新语》;秦始皇遇海神出自《三齐要略》。齐梁时期的典籍收藏十分兴盛,再加之“好异尚奇”的文化心理,为此类书籍的编撰创造了条件。
拾遗类小说本质上是遗闻轶事的文献集成,作者无创作之实,却有编纂之功。此类作品虚实程度不同,却有以下特征:
一、从史官视角追索故事。
史官视角,主要体现在编撰者的历史意识,如《拾遗记》《西京杂记》《小说》以历史为线索,勾连异事;《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则以史家姿态“反顾”古人。编撰者有意从历史的角度构建史料的系统性,以不同方式暗示史料的稀缺性,强调所载之事征实可信。

《中国笔记小说史》
这种心态在拾遗类小说的生成过程中时有体现。如葛洪在《西京杂记》序跋中坚称家藏一百卷本《杂记》,从中摘取二卷,皆史书未载之事。萧绮批评王嘉“迂阔”,也为《拾遗记》辩说,试图将谶纬神话纳入信史。“拾遗”是一种历史文献意识,行之于作品,便以补史之阙的名义“拯救”轶闻,满足好异尚奇的文化心理。
二、以传奇人物凝聚异辞。
异辞是不见于正史之事,或难为正史接纳的史料。《公羊传》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词”之说。拾遗类小说主要载录异辞,内容与帝王行迹有关,如炎帝、黄帝、夏禹、商汤、周幽王、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等,这些历史上的帝王,有着共同特点,即传奇性。
如周幽王好远游,因而衍生出八骏出行(《拾遗记》),武帝爱求仙,演绎出与西王母相会(《汉武帝内传》)。以传奇人物凝聚轶闻,体现了历史传说的生成规律,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为好事者关注,衍生出愈来愈离奇的故事。
拾遗类小说中的人物事迹更加完整,零散的杂记开始围绕某一人物发生聚合,塑造出与史传记载有所不同的人物形象(如《汉武故事》)。
三、取经史传记内塑体例。
今人所说的拾遗类作品通常指小说,这是根据小说发展事实所作的划分。唐代之前的小说概念较为狭窄,拾遗类小说在目录著作中大多被归入史部。以《隋志》为例,《拾遗记》属“旧事”,《西京杂记》属“传记”。
拾遗类作品近于史,易于从经史传记中获得启发。譬如,王嘉《拾遗记》借鉴了《帝王世纪》的编撰体例,萧绮又以“传录”强化了作品的史著性质。殷芸的《小说》同样采取本纪与列传结合的方式。编撰者根据内容不同调整结构,如《汉武帝内传》偏重于仙家传说,采用的是旧事杂记的体例,《汉武故事》在形式上则更近于传记。

《汉魏六朝文学研究著作提要》,杨晓斌、马燕鑫、杨沐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3月版。
拾遗类小说在唐前各体古小说中较为独特。相比《搜神记》《列异传》等志怪小说,拾遗类小说偏向于纪实;相比《十洲记》《博物志》等博物之书,拾遗类小说主要载录历史轶闻;与《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世说”类小说相比,拾遗类小说又以人物事迹为主。由于拾遗类小说的内容及体制特点,使其成为唐前小说中独特的一类。

三、唐宋时期拾遗类小说的演进
拾遗类小说在唐代亦有发展,代表作品有刘餗《隋唐嘉话》、李肇《唐国史补》、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以及撰人未详的《大业拾遗记》《大宋宣和遗事》。几部作品的延续了补史之阙的特点。
《隋唐嘉话》又名《国朝传记》,载录南朝陈至唐开元年间轶闻故事,作者刘餗,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

《隋唐嘉话 朝野佥载》
《隋唐嘉话》的编撰目的是补正史之不足。刘餗书中自述“(余)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28]。由于出身史学,刘餗编撰《隋唐嘉话》有着近水楼台的优势。书中以隋唐间的历史轶闻为主,所涉人物较为广泛,并不局限于帝王将相、名臣显贵。
中唐时期,翰林学士李肇撰有《唐国史补》,作者自序“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29]。
《国史补》续接《隋唐嘉话》,作者秉承补史的观念,内容上“言报应,叙鬼神”[30],不避鬼神之事,又“采风俗,助谈笑”[31],类似“剧谈”“杂俎”。
五代之时,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体例与《西京杂记》颇为相似。该书记玄宗开元、天宝间的遗闻轶事,如张九龄讽刺朝臣趋炎附势,华清宫七夕乞巧,而“县妖破胆”“传书莺”稍具规模,较能体现小说的文学意味。
上述作品大多属于野史杂记,后人称之为“史料笔记”。唐宋是“史料笔记”繁荣的时期,中华书局整理的《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多达八十六种,周勋初先生《唐人轶事汇编》《宋人轶事汇编》也是主要根据史料笔记,将遗闻轶事按人物编纂而成。
比较唐宋目录著述,会发现记录遗闻轶事的杂记迅速增多,由此改变世人对小说与杂史关系的认识。唐代目录家通常会将拾遗类作品置于史部杂传,到了宋代,许多目录著述开始将“杂传”易名为“传记”。
以《新唐志》为例,“传记类”载录传名之外的唐代作品近五十种,据其形式,约有三类:一为“杂录”,如《投荒杂录》(房千里)、《祥瑞录》(魏徵)、《英雄录》(李德裕);二为“杂记”,如《宾佐记》(杜佑)、《景龙文馆记》(武平一)、《闻见记》(封演);三为“杂事”,如《国朝旧事》(刘餗)、《朝野佥载》(张鷟)、《文场盛事》(李弈)。以上仅以题名略作区分,三类之外,尚有作品难以归类。

《全唐五代笔记》
宋代的目录家开始有意识地将志怪类作品从传记文类中分离出去,传记内部构成更加单纯。正如周勋初先生所言,宋人轶事“很少见到真真假假驳杂难明的情况”,这说明宋人“已分清不同文字的体类要求”[32]。如此一来,记录遗闻轶事的作品回归史部正统,反倒与小说渐行渐远。
然而,历史上的遗闻轶事终究脱不开文学,以“拾遗”“遗事”为名的小说,在宋代之后开始向历史传奇、讲史说话发展。
譬如,《大业拾遗记》,作者题名初唐颜师古,实为后人伪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其作者是宋人,李剑国先生则认为是晚唐人。

清顺治三年李际期宛委山堂刻本《大业拾遗记》
《大业拾遗记》记隋炀帝巡游江南时的浮靡之事,后人多以艳史视之。书中见载萧妃、陈后主托魂规劝,事涉奇诡,颇有讽谏之义。该书虽有拾遗之名,却与遗闻轶事相去甚远,体现了拾遗类小说向传奇的转变。
时至南宋,市井生活的繁荣和说话艺术的发展,为“讲史”类小说的发达创造条件。今所见《大宋宣和遗事》便是一部以北宋末期梁山起义为素材的讲史小说,作品塑造了宋江、杨志等英雄人物,是《水浒传》的雏形。
《大宋宣和遗事》仍延续了拾遗类小说的不少特征,譬如,“遗事”又称“逸事”或“轶事”,与“拾遗”本质相同;作者依然以“遗事”为信史,将历史作为艺术创作的起点和资源背景。
然而,《宣和遗事》与汉唐以来的拾遗类作品又有所不同,最根本的,莫过于说话艺术的加入。历史叙事有了更为广阔的演绎空间,零散的传说轶事围绕中心人物聚拢起来,形成百川归海之势,虚构也成为历史叙事的自觉追求。所谓“因由一点演绎开来”,便指出讲史小说的基本素材依旧是历史上的遗闻轶事,作者借遗闻轶事演绎发挥,使之脱实向虚,人物故事也从零散走向系统。
综上所述,拾遗类小说在唐宋之后分为两途,相关作品或重归史学,追求信实;或向传奇、讲史演进,成就历史小说的兴旺。拾遗类小说的文学意义可归之于下:
首先,拾遗类小说为史传叙事的多元化提供了载体,为历史故事架起文学的桥梁。
遗闻轶事是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在帝王将相的史实外,弥补了史传记事的不足。史家常为“异辞”而困惑,《史记》叙述史实,便以“或曰”采撷“异文”,或是以闻见之事补充正文所叙。

明徐奉泉大来堂刻本《史记》
《史记》对“异辞”的态度是兼容并蓄的,随着官史制度日益严格,闻见异辞难以侧身正史,只能寄于杂史、杂传、杂记所载。拾遗类作品在魏晋南北朝获得兴盛之机。
一方面,周汉以来的史事轶闻积累丰富,有充足的文献资源供好事者发挥;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的史学思想相对自由,史家对遗闻轶事较为宽容,再加之好意尚奇的时代风气,专门收集遗闻轶事的作品逐渐兴起。
遗闻轶事是传闻之历史,经过传闻者的增饰,易于文学发挥。作者不受“史职”羁绊,故能在传说轶闻中寻得意趣,相关作品也便具有了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品格。
其次,拾遗类小说是历史小说的源头之一,也为后世小说创作提供素材。
史传与小说关联紧密:史家褒贬是非为小说所继承,寓言于事、寄意笔端承载了小说作者的现实关怀;史传为小说提供体例示范,杂传、杂记孕育了早期小说的基本形态;小说叙事吸收史传写人纪事之法,实现“丛残小语”向“有意为小说”的转变。
反顾中国小说发展史,历史小说是古代小说的重要一支,拾遗类小说又是早期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显而易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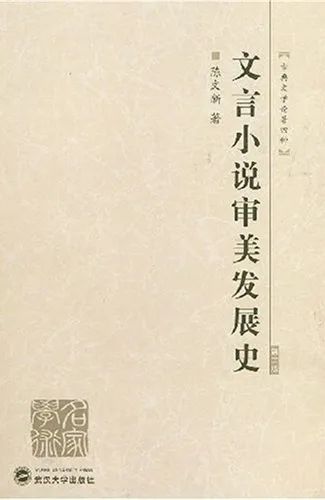
《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
虽然纪传体史书是历史小说的重要源头,但在正统史传之外,野史杂记更能体现历史故事的小说价值。从小说发生的角度,历史故事与神鬼传说又最为小说家所喜。
拾遗类小说采撷遗闻轶事,实现传说异辞的聚合,再经好事者演绎藻饰,逐渐演绎成情节丰富完整、人物形象充实饱满的传奇小说——如《大业拾遗记》、陈鸿《长恨歌传》——由此实现历史叙事向文学叙事的转变。
宋元之后,随着说话艺术的兴起,历史上的遗闻轶事有了更为宽广的施展平台,历史传奇也最终衍为讲史话本,汇入通俗小说的潮流之中。
注释:
[1]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
[2]王兴芬《杂史杂传为体地理为用:论拾遗记的文体特征》,《西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3期。
[3]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4](唐)魏徵《隋书》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1页。
[5](唐)房玄龄《晋书》卷九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96页。
[6](晋)王嘉撰,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页。
[7]《拾遗记》卷首,第1页。
[8]《拾遗记》卷四,第99页。
[9]《拾遗记》卷四,第101页。
[10]《晋书》卷九十五,第2496页。
[11]《晋书》卷九十五,第2496页。
[12](汉)桓谭著,朱谦之校注《新论》卷一,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页。
[13](晋)葛洪著,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校笺》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50页。
[14]《拾遗记》卷九,第219页。
[15]《拾遗记》卷首,第1页。
[16]《战国策•秦策一》云:“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汉)刘向辑录:《战国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
[17]《汉书•谷永传》云:“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为太中大夫,备拾遗之臣。”《汉书》卷八十五,第3465页。
[18](宋)曾巩撰,陈杏珍校点《曾巩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191页。
[19](宋)高似孙《子略》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页。
[20](汉)刘歆撰,(晋)葛洪辑,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附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页。
[21]余嘉錫《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13页。
[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23]《西京杂记》卷一,第51页。
[24]《西京杂记》卷六,第254页。
[25]胡应麟认为《汉武故事》乃六朝人所作,详见(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7页。《汉武帝内传》晚于《汉武故事》,详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9页。
[26]《隋书》卷三十四,第1011页。
[27](唐)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一,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96页。
[28](唐)刘餗《隋唐嘉话》卷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29](唐)李肇《唐国史补》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30]《唐国史补》卷首,第3页。
[31]《唐国史补》卷首,第3页。
[32]周勋初《宋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云霞育儿网
云霞育儿网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