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匪被捕后提出要见高岗:二十年前在陕北,刘志丹曾我的副团长
经过多年的猖獗活动,长期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土匪头目张廷芝终于迎来了他的末日。他的恶行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最终,他的嚣张气焰被彻底扑灭。随着他的落网,这片饱受其害的土地终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张廷芝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为西北地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安宁。
在面对绝境时,任何人都渴望生存,张廷芝同样如此。

途中,张廷芝与孙有光持续交谈,表达了希望与高岗会面的意愿。高岗当时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及政委等职。
二十年前在陕北地区,我担任团长职务,刘志丹是我的副手,高岗则负责教导队的具体工作。当时,他们两人都加入了共产党,而我则主要负责民团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张廷芝察觉到孙有光神色如常,心里顿时一紧。
事实上,张廷芝曾多次面临改变命运的关键时刻,但每次在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他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这些土匪头子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因此对付他们必须讲究策略。他们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长期社会矛盾的产物。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对症下药,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简单粗暴的手段不仅无法根除问题,反而可能激化矛盾。所以,在处理这些棘手问题时,必须谨慎行事,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
毛主席在对待一些重要匪首时,往往会采取宽大处理的态度。这主要是考虑到他们曾经为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同时也顾及到他们的少数民族背景。以陈渠珍为例,这位湘西地区的头面人物就得到了特别关照。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对历史功绩的尊重,也照顾到了民族团结的需要。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都是基于这些重要因素而做出的特殊安排。
在历史记载中,还有一些极为罕见的匪首,毛泽东主席曾亲自下令严惩。比如井冈山地区的萧家壁,主席明确指示必须活捉归案。还有那位著名的“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尽管周恩来总理为她求情,毛泽东依然坚持依法处理,没有网开一面。这些案例体现了当时对匪患的严厉打击态度。
张廷芝属于那种极为罕见的大土匪。

据张廷芝自述,他在二十年前曾加入陕北的红军队伍,这一说法并非虚构。然而,恰恰因为他曾是红军的一员,他的所作所为才显得更加令人不齿。
1908年,张廷芝出生在陕西靖边县的金佛坪村,他的家族在当地势力很大。据史料记载,张廷芝的祖辈中有八位文武举人,虽然家族里没人考中进士,但在当地,他们家族的地位非常高,是公认的显赫家族。
到民国初期,张家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周边400多个村庄,拥有土地约1500亩,当地大部分农民都成了张家的佃农。由于当时军阀混战,张家为了自我保护,在其控制区域内修筑了土墙防御工事,并组建了一支私人武装队伍。
这支队伍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是防范匪患,二是震慑地方。
张廷芝继承了家族的庞大产业后,非但没有利用这些资源为当地百姓谋福利,反而滥用权势,成为地方上的祸害。他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秩序,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张廷芝的所作所为,使得他声名狼藉,成为人们口中的恶霸。

1930年春天,冯玉祥从甘肃和宁夏调集西北军投入战斗,同时指派苏雨生担任宁夏骑兵第四师的指挥官,负责驻守平罗。苏雨生抓住这个机会扩充军队,将张廷芝的土匪队伍收编进来,并任命他为第16团的团长。
在1928年渭华起义失利后,刘志丹和谢子长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开始进行军事渗透活动。他们巧妙地进入苏雨生的部队,利用其名义组建军队。在此期间,刘志丹不仅与苏雨生部15团团长王子元建立了联系,还被任命为16团副团长。同时,高岗也被安排进入16团,担任教导队副队长。尽管刘志丹曾试图在张廷芝的土匪部队中开展工作,但最终未能取得成效。
宋哲元担任西北军将领时,委任谭世麟为甘肃暂编第六旅的指挥官。谭世麟上任后,迅速展开行动,吸纳了当地的土匪势力和地方武装力量。与此同时,张廷芝在离开苏雨生的部队后,也选择加入谭世麟的阵营。
刘志丹抓住谭世麟扩编地方武装的时机,率领部分部队加入其中,暗中策划兵运工作。这支队伍在三道川与张廷芝等多股土匪合并,组成陇东民团军清乡司令部直属第三团,由谢子长担任团长。
可惜的是,张廷芝搅黄了这次联合建军的计划。当时刘志丹应谭世麟之邀,前往庆阳协助组建部队。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廷芝突然出手,强行收编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军周维奇营,导致这支队伍四分五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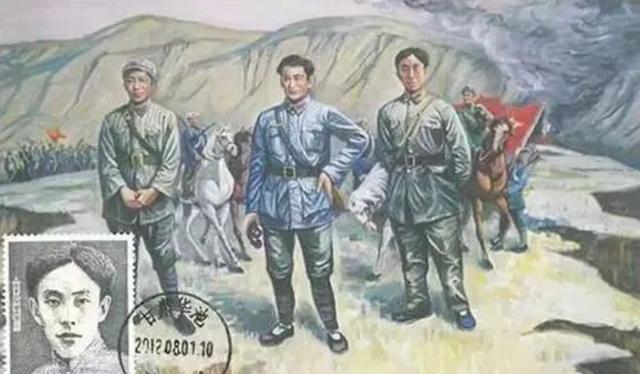
在三道川事件之后,张廷芝表面上是谭世麟的部下,但实际上他已经自立门户,成为地方上的军事强人。
谭世麟完全被蒙在鼓里,直到事情发生后才知晓。他愤怒地指责张廷芝,称其为"背信弃义的卑鄙之徒"。谭世麟对张廷芝的行为感到极度不满,认为其出尔反尔,毫无诚信可言。这种背叛让他深感被愚弄,因而大发雷霆,毫不留情地痛斥张廷芝的为人。谭世麟的愤怒源于对张廷芝人品和行径的彻底失望,他无法接受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派,故而用激烈的言辞表达了自己的愤慨。
张廷芝的人生轨迹充满了反复和不确定性。他的行为和决策常常变化无常,这种不稳定性贯穿了他的一生。张廷芝的个性和处事方式让人难以捉摸,他的生活充满了起伏和转折。这种反复无常不仅影响了他的个人发展,也对他周围的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廷芝的一生,可以说是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中度过的,这种特点成为了他人生的重要标志。
在刘志丹和谢子长成功建立陕北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张廷芝一直是该地区的主要威胁。
【二】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多次与附近的张廷芝匪帮发生冲突。
从军事实力来看,张廷芝的部队根本不是我军的对手。不过,当时我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付国民党军队上,这才让张廷芝有机可乘,多次发动偷袭。
左权指挥军委警卫连和工兵连攻打张廷芝的土围子,战斗很快取得胜利。但由于张廷芝当时不在据点内,因此侥幸逃脱了抓捕。

1935年末,中共为了更有效地管理东靖边、定边和西靖边地区,决定成立三边特委,并任命谢唯俊为该特委的书记。同时,为了应对当地的匪患,还特别设立了剿匪指挥部。这一系列措施旨在强化对这些区域的领导和控制,确保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出乎意料的是,张廷芝成功策反了我军游击队连长宗文耀,导致他在关键时刻倒戈。
谢唯俊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赣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之一,也是红军中的杰出指挥员。他深谙毛泽东的军事策略,能够准确把握并执行其战略意图。他的意外牺牲让毛泽东感到震惊和惋惜。
叛乱最终被镇压,然而张廷芝却再度成功脱身。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廷芝毫无廉耻地投奔了驻扎在包头的日本军队。到了1943年,他还被怀疑参与杀害了五名从苏联回国的我党干部。战争结束后,张廷芝的武装力量被国民党政府正式收编。
张廷芝清楚自己犯下了许多罪行,但他毫无悔意,根本没有想过要改过自新。
在陇东战役中,张廷芝家族世代居住的土堡被解放军攻陷,随后他投奔了驻扎在榆林的国民党第22军。

1949年6月1日,国民党军第22军军长左世允带领部队起义。与此同时,张廷芝再次逃离,他的部队被驻扎在绥远的国民党军第111军收编。得知绥远部队也有起义的打算后,张廷芝又一次逃跑,后来悄悄返回并混入了绥远第36军。
1949年9月19日,绥远地区发生起义后,张廷芝的部队被整编为一个骑兵连。然而,当他得知自己可能被派往北平接受训练时,因害怕被追究责任,他再次选择了叛变。
1949年11月,张廷芝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我军的严密包围下,最终选择缴械投降。
张廷芝的投降不过是故技重施,毫无真心可言。回顾历史,他的这种行为早有先例。在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之前,他曾带兵攻打我陇东苏区,结果被我军围困。那时他就假装投降,趁我军不备,趁机突围逃脱。这种反复无常的行径,充分暴露了他不可信任的本质。
1949年12月,西北军区提交了一份关于剿匪工作的阶段性报告。毛主席在审阅这份报告时,注意到了张廷芝的名字,随即作出了批示。
此人过去罪行累累,行事反复多变,必须立即处理,绝不能姑息!
毛主席的批示来得有点晚。
在解放军军官训练班学习时,张廷芝并未安分守己。他暗中拉拢其他投降的土匪,利用他们过去犯下的罪行制造恐慌,使不少人因害怕而支持他的主张。

1949年12月11日,张廷芝带领一伙土匪从训练营逃脱,逃往乌审旗王府,再次发动叛乱。
当时,西北地区匪患猖獗,给了张廷芝发展的机会,张廷芝收编匪众声势浩大,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不久之后任命下来,张廷芝出任“反共救国军1016部队司令”。
【三】
1949年到1950年初,靠近陕甘宁边区的伊克昭盟地区土匪活动十分频繁,尤其在南边的乌审旗更为严重。当地的头目是蒙古族土匪奇正山,他曾经是乌审旗的王爷。
奇正山不仅掌握了当地的蒙古族军事力量和普通百姓,还整合了以张廷芝为代表的汉族匪帮,构建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武装势力。
当时,绥远军政委员会决定派遣部队进行剿匪行动,但由于当地社会情况复杂,决策过程颇为纠结。最终,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提出了解决方案:调动内蒙古军区下属的骑5师进入叛乱区域执行任务,同时任命伊盟盟委书记高增培兼任骑5师政委。
1950年2月13日,骑5师进驻伊盟达拉特旗,同时安排第15团驻守黄河一带,防止匪徒向北逃窜。
战前虽然制定了细致的作战方案,但实际的清剿行动却遇到了诸多阻碍。敌方的骑兵部队机动性强,不与我军正面交锋,而是采取游击战术,利用对地形的熟悉优势,不断进行骚扰和突袭。这种战术让我军在推进过程中举步维艰,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伊盟地区长期由蒙古贵族统治,当叛乱分子溃逃后,他们散布谣言,诬陷我军前来是为了消灭当地居民,这种不实言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的民众恐慌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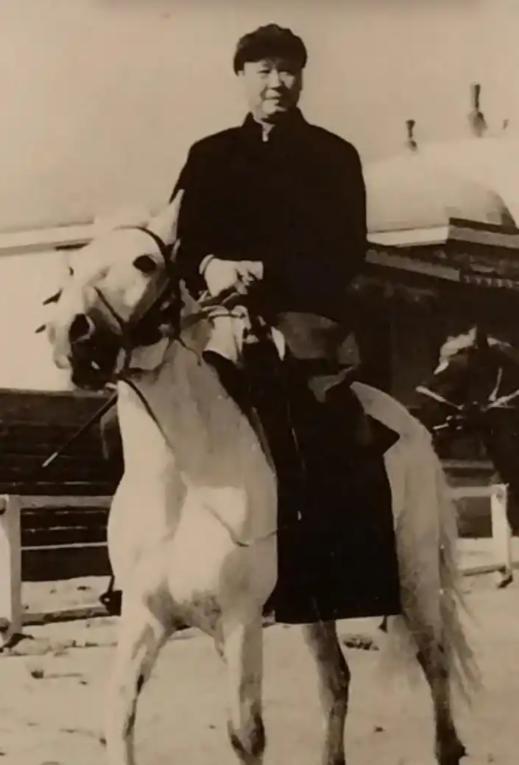
张廷芝这类奸诈的匪徒采取了更为阴险的手段,他们伪装成解放军士兵,专门袭击当地牧民,严重损害了解放军的声誉。这些土匪通过乔装打扮,冒充正规部队进行抢劫,不仅给当地居民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在群众中制造了恐慌和误解。他们的行为使解放军在当地群众中的形象受到极大冲击,严重影响了军民关系。这种冒充行为不仅增加了剿匪工作的难度,也使得群众对解放军的信任度下降,给后续的群众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为了有效应对这一局面,我军及时调整了剿匪方针,不再单纯依赖军事手段。新的策略重点在于实施民族政策,通过争取当地民众的信任来巩固治理基础。具体措施包括向群众传授识别解放军与土匪的方法,帮助他们分清敌我。这种转变不仅增强了军民关系,也为剿匪工作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这一做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绝大多数本地居民并不倾向于参与匪患,尤其是长期居住在此的蒙古上层人士。只要向他们明确解释,我方部队进驻的唯一目标是清除匪徒,他们不仅不会阻挠,反而会给予协助。
即便是本地的蒙古族居民也提到:
党的民族政策真心实意为各民族着想,把我们当成一家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别被那些不靠谱的言论误导了。
这样一来,当地的土匪就被彻底孤立了。
我军随后展开的剿匪行动进展非常顺利,不仅在军事上取得显著成效,还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广泛拥护。

在我军严密的包围和追击下,奇正山的土匪们无处可逃,最终被一一抓获。张廷芝虽然受伤后侥幸逃脱,躲进了当地百姓家中,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行踪已经被解放军掌握。
1951年夏天,奇正山等31名蒙汉土匪在经过公开审判后被处决。相比之下,张廷芝因其罪行深重,被中央政府特别点名,最终被押送到绥远省省会归绥处理。
1953年3月,法院对张廷芝案件作出最终裁决,决定对其处以极刑。
 云霞育儿网
云霞育儿网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