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病故后,追悼会如何称呼?将军、老红军都不行,被称呼:老人
1949年秋天,就是十月那会儿,湖南中间的衡宝这块地方,就是衡阳到邵阳那儿,国民党那边的“小诸葛”白崇禧带着他的桂军主要部队,靠着他们老早建好的防御工事和还算完整的队伍,还在硬撑着,不打算投降。他们摆下的这个阵势,简直就是给第四野战军往南走设置了一个大难关。
丁盛那时候是第四野战军第45军135师的师长,他带着手下的兵马,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勇敢地插进了敌人的心脏地带,目的是要把敌人切开、绕过去,把他们的阵脚给搅乱。不过呢,因为通讯设备不太给力,情报也来得慢,再加上他们行军速度太快,135师在往前冲的时候,没能及时搞清楚敌人主力的位置和变动情况。

部队一到衡宝公路南边的灵官殿和沙坪,没想到直接掉进了白崇禧早就设好的圈套里。桂军的第7军、第48军等四个厉害得很的师,就像一把收紧的铁夹子,从各个方向猛扑过来,把135师给牢牢地困在了中间。平时挺镇定的司令员林彪,一听135师处境那么危险,心里也急得不行。前线的情况看起来已经很难扭转了,135师的生死存亡就在眼前。
碰到这突如其来的死胡同,丁盛发现自己被敌军紧紧围在核心地带。他瞅了瞅战场上的形势,又琢磨了琢磨敌我两边的长处短处,心里头有了个特别胆大的主意:咱得翻个身,把被动变主动,瞅准敌人包围圈还没合紧、各部队之间乱糟糟、配合不上的空子,把咱们的精兵强将聚到一块儿,专挑敌军最弱的地方下手,狠劲儿打过去,再穿插分割他们。

桂军虽然人数上占了上风,但因为他们匆忙集结,指挥和部队之间的配合肯定有些乱,这就是咱们可以钻的空子。丁盛见状,立马改变了战术,让手下队伍收拢防线,把劲儿往一块儿使。他下令以团、营为单位,就像是一把把尖刀,借着夜色和复杂的地势,朝着敌军连接的地方还有他们指挥的中枢,发起了凶猛的反向突袭。
丁盛的部队像把锋利的刀,把桂系军队的包围圈一处又一处地给划开了,让各部队之间没法再互相联系,整个指挥系统乱成了一锅粥。特别是白崇禧特别看重的那支“铁打”的王牌军,国民党第7军,在135师的快速灵活、猛烈攻势下,队伍全乱了套,编制都被打散,彻底没了还手之力。

这次战斗让桂系的精锐部队损失惨重,一共干掉了他们1.75万人,里头还有不少大官,比如敌军的师长被打死,第七军的副军长凌云上也被俘虏了。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毛主席听到这个战报后,对丁盛的果断指挥和135师的勇猛表现是赞不绝口。
雪地显神威,瓦弄突袭让印军震惊在那片被白雪覆盖的土地上,我方部队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瓦弄地区,一场精心策划的突袭行动,如同一道闪电,瞬间击中了印军的防线。这次行动不仅彰显了我们的英勇无畏,更让印军深感震撼。在雪地的掩护下,我们如同幽灵般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了攻击。印军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显得手足无措,防线瞬间崩溃。瓦弄之战,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次精神上的鼓舞。它向世人展示了我们的决心和实力,也让那些试图挑衅我们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到了1962年,印度那边的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边那块地方,越过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一点点侵占咱们中国的地盘,最后还搞起了大规模的打架冲突。眼瞅着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就要被占便宜,情况万分火急,这时候,丁盛已经不当师长了,他升级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的军长。在这节骨眼上,他又被委以重任,带着他手下这支超厉害的部队,火速赶往喜马拉雅山南边、西藏的东南方向,他们的任务是,在中印边境东边那块,进行自卫反击战,保护咱们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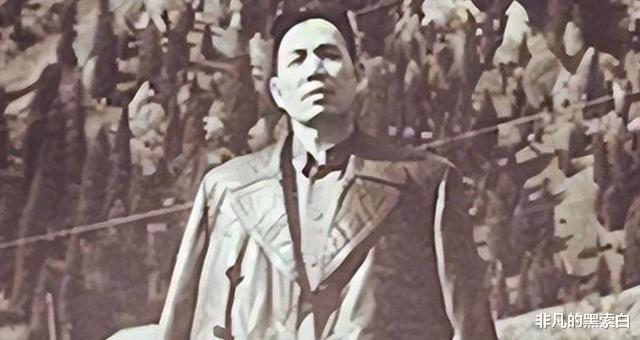
战斗快开始前,瓦弄那边天气变得特别糟糕,大雾浓浓的,看得特别模糊,有时候连十米远的东西都看不清。印度军队觉得自己那边工事修得牢,地形又有利,想着解放军在这种鬼天气里肯定没法好好打仗。54军里有些领导心里也犯嘀咕,想着队伍刚到高原,那些大炮啥的还没完全运来,再加上大雾挡着,炮兵都看不清也打不准,所以他们就去问军长丁盛,看能不能等天放晴了,或者那些大炮都到了,火力更足了,再打过去。
丁盛在好好研究了下地形,琢磨了敌情和我军情况后,觉得现在漫天的大雾,一般人可能觉得会妨碍进攻,但他却觉得这是个天然的好掩护。大雾不光会让解放军看不清楚,也会让在高地上、看得远的印军变成“瞎子”,没法好好发挥火力优势。这样一来,解放军就能悄悄地靠近敌人,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条件可太好了。

丁盛一下令,第54军的战士们就用他们擅长的山地游击方法,灵活地绕来绕去,把守在瓦弄各处的印军切成小块,逐个包围起来。丁盛自己跑到前线指挥的地方,看着战场上的情况变来变去,他很快就调整了兵力,让部队从好几个方向一起进攻,而且大胆地选择在近处和夜里打,把印军的防线搞得乱七八糟。
打了差不多十个小时的硬仗,解放军54军终于拿下了瓦弄地区印军的所有地盘,把那里的印军主力给打垮了,这就是有名的瓦弄大胜。听说这场仗给印度军队留下了超深的印象,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印军内部都把“54军”这个名字当成假想敌来练,可见这场仗对他们的心理打击有多大。

情况急转直下,上海这一趟将决定未来的走向。
丁盛曾经身居军长、兵团副司令等重要岗位,后来到了和平建设年代,他更是挑起了大梁,担任起守护南疆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一职。广州军区地理位置极为关键,丁盛掌舵那会儿,他尽心尽力,把军区的各项工作都搞得红红火火,赢得了上下一致的好评。这段时光,可以说是他军事生涯里的一段高光时刻,让他得以大展身手。
1973年的时候,为了实施“军队干部轮换交流”的政策,中央军委做了个大决定,要把八大军区的头头们换个位置。丁盛就这么接到了调令,他要和南京军区的司令员许世友将军换岗,许世友那可是出了名的性子直、脾气硬。就这样,丁盛收拾行囊,奔向了历史悠久的南京,去那里开始他的新工作。

1976年,也就是三年后,一场大风波真的来了。这一年,丁盛因为工作的事情去了上海。他住在上海市中心的延安饭店里。有一天晚上挺晚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还有上海其他的几个头头脑脑,一块儿跑到延安饭店去找丁盛。这事过了没多久,丁盛在上海延安饭店那次晚上的见面,还有他之前可能跟上海那边的一些跟军队有关的事情,就成了大家调查的重点。他一下子就被卷进了这场政治大风波的最中心。
在调查阶段,丁盛被扣上了参与策划“对抗政府武装行动”的帽子。对这些异常沉重的政治罪名,丁盛屡次向相关部门解释,拼命表明自己和那所谓的“武装行动”计划没有半毛钱关系,不断重申像是“他们分发枪支的事,跟我有啥联系?”这样的话,想要把事情说清楚,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在那个时候,“两个凡是”的观点还是主流,政治上的清查活动也有些过头。在这样的历史大环境下,个人想要解释清楚自己的立场,真的是难上加难。丁盛怎么辩解,也没能扭转审查部门的看法。到了1977年,正式的审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出来了:说丁盛在政治上犯了大错,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掉他所有的党内外的职位。他被硬是从军队里赶了出来,生活过得大不如前,听说每个月只能靠150块钱过日子。
年迈之时,将军境遇凄凉,但那份军人的傲骨依然未变。
尽管丁盛被组织边缘化,像是被丢在一旁,但他心里对党和军队的忠心,还有对自己清白的坚持,一点都没变。他深信自己是无辜的,现在受的这些处分,不过是特殊时期的一场误会。他差不多每周都会拿起笔,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这些地方写信,把自己的事儿一五一十说清楚,反驳那些冤枉他的假话,希望组织能再好好查查他的案子,把他的党籍和名声给恢复回来。

1998年,他意外收到了一份来自老战友的特别邀约,这位战友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把手,黄火青。他满怀期待地去了北京,心里盼着能借此机会恢复党籍。可惜,最后这事儿没能如愿。不过,好在那些老战友们一直没忘了他,给了他不少关心和实质性的帮助,让他的生活稍微宽松了点。从北京回到南京没多久,原广州军区也伸出了援手,念在他过去的贡献和眼下的难处,给他换了套符合师级干部规格的住房,居住环境因此大为改善。
1999年9月那会儿,他因为病情太严重,被紧急送去了医院。医生护士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可到最后,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将军。丁盛将军这一辈子啊,可以说是都在战场上度过的。从土地革命那会儿的小战士,到抗日、解放战争里的勇猛将领,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级指挥官,他为咱们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军队的建设,真的是立下了大功。他走了以后,给他办个配得上他地位和贡献的追悼会,那也是应该的。

他生前经历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波折,并且留下了一些直到离世都未能厘清的历史问题。因此,怎么给他办追悼会,特别是该怎么称呼他,就成了个相当难办又敏感的事情。家属向有关部门询问追悼会的相关事宜后,得到的回应是:追悼会主要由家里人自己张罗。
要办追悼会,那就得准备讣告,还得布置灵堂。讣告和灵堂横幅上怎么写称呼,这很关键,直接反映了逝者的身份和大家对他的看法。丁盛的家人呢,按照党里军里一直以来的规矩,一开始想用“丁盛同志”这个称呼。这个称呼挺普通的,但拿去审查的时候,却说不能用“同志”这两个字。为啥呢?因为丁盛在1977年就被开除出党了,一直到去世都没恢复党籍。

家人们没办法,想着丁盛活着的时候是个大功臣,当过高官,就想用“丁盛将军”这个称呼。但这主意被否决了,可能是因为他已经被撤了所有职位,官方上不再认他的将军头衔和身份。接着,又有人说,丁盛1930年就加入了红军,是老一辈的革命者,能不能用“老红军”来称呼他?这代表着他早期的革命经历和贡献。可惜,这个提议好像也没被采纳。
经过一番商量和琢磨,大家最后琢磨出一个既不偏向哪边、也不涉及政治,同时还能表达敬意的叫法——“老人家”。就这样,这个挺简单的称呼被定了下来,“丁盛老人家”成了大家公认的、可以在公开地方喊他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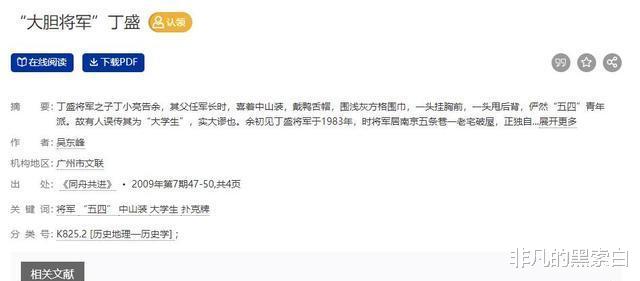
 云霞育儿网
云霞育儿网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