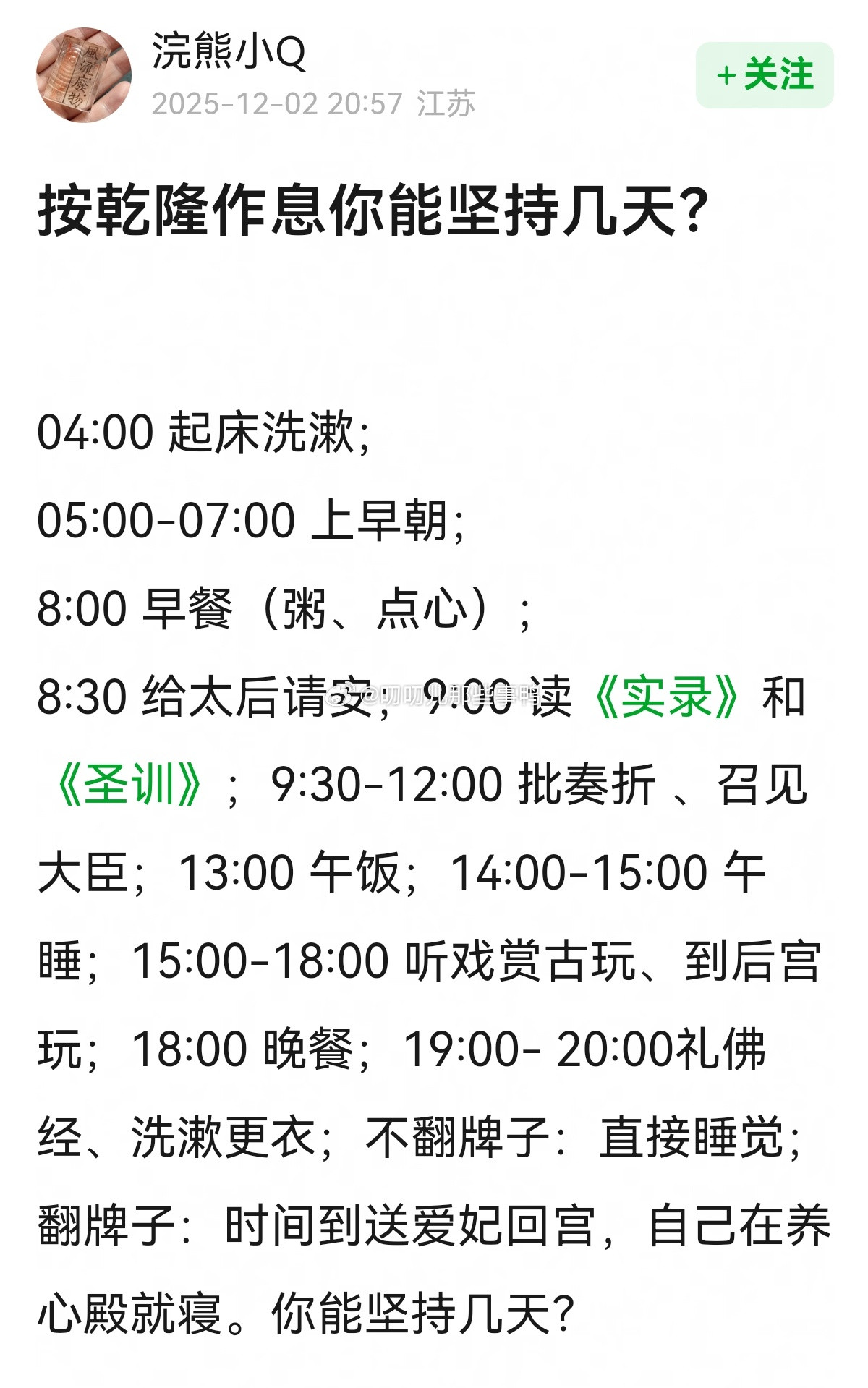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圆明园丧钟鸣,乾隆新立,首旨便是释放被囚十四载的十叔胤䄉、十四叔胤禵。寿皇殿后院,胤禵端着凉粥闻“开释”二字,碗磕牙碎——铁门嘎吱洞开,阳光晃得他如坠异世。 铁门的锈味还缠在鼻尖,和亲王弘昼的素缎袍角已扫过门槛。“十四叔,轿子备在角门。”弘昼的笑温软如江南丝绸,胤禵却盯着对方袍上暗绣的金线蝠纹——这料子,比他当年出征时的帅帐帷幔还亮。 青呢金蝠轿一晃,他脚踝的老茧蹭得靴筒生疼。十四年前锁镣磨出的疤还在,此刻竟被自由硌得发酸。轿帘掀起时,街角葱油饼的焦香蛮横钻进来,他喉头滚动,才惊觉自己已十四年没闻过市井烟火。 弘昼递来油纸包的酱肘子,油汁浸着粗麻纸。胤禵三口吞下,肉香混着葱花气呛得他眼眶发热——原来自由不是冰冷的“恩旨”,是能咬出肉汁的实在。他抹嘴时,轿已过了三个街口,叫卖声、车轱辘声织成网,网住一个久违的人间。 和亲王府的澡桶换了三回热水,他才把那身“黑甲”(囚服结的硬壳)泡软。绸缎衣被他扔在榻尾,捡了件青布袍套上,领口磨着脖颈,竟比囚服的粗麻还扎人。夜听堂会锣鼓响,他猛地攥紧拳头——当年这动静是提审的信号,如今戏台上的花脸唱到“将相和”,他手指才敢跟着鼓点轻叩桌面。 次日天未亮,他揣着半块剩饼往正阳门走。箭楼墙砖上的箭痕还嵌着砂粒,像极了准噶尔战场上射进甲胄的流矢。“当年从这儿出兵时,砖缝里还长着狗尾巴草。”他蹲下身,用指甲抠下块带痕的砖末,混着唾沫研墨,在宣纸上写“天光云影共徘徊”,笔锋沉得像拉满的弓。 消息传到养心殿,乾隆让太监送十刀宣纸,砚台盖刻着“放鹤”二字。胤禵摸着砚底的云纹笑:“这鹤,怕不是圈养的?”他把砚台锁进木匣,却每日用那砖末研墨,字越写越稳,仿佛把十四年的郁气都揉进了笔锋。 老十胤䄉拎着酒来串门,醉醺醺拍他肩膀:“皇帝侄子待咱不薄,该进宫谢恩。”胤禵给他满上酒,自己却抿了口茶:“进宫?那门坎比当年的囚牢门槛还高,我这双破脚,怕迈进去就拔不出来了。”胤䄉骂他胆小鬼,却也再没提过谢恩的事。 乾隆元年万寿节,胤禵还是被抬进了宫。太和殿角落里,那杆豹尾枪擦得锃亮,枪缨红得像血。乾隆走过来,指尖划过枪杆:“十四叔当年用它平了准噶尔,如今教朕几招枪法?”胤禵膝盖一软跪下去,额头贴着冰凉的金砖:“臣老了,拉不动枪,能提笔给皇上抄经已是天恩。” 叔侄俩在寿皇殿写“四海一家”,胤禵的笔在“家”字那一捺上顿了顿,墨点晕开像滴泪。出宫时,他看见墙角蒲公英飞絮,伸手接了朵,对着风轻声问:“你们飞出宫墙,能落在哪儿?” 四年后深秋,胤禵在和亲王府病逝。家人收拾遗物时,见那“放鹤”砚台底刻着行小字:“鹤已放,人当归。”出殡那日,旧部自发在路边摆了香案,红缨帽沿的霜花沾了泪,倒比当年出征时的旌旗更显真切。 他终究没能再回正阳门箭楼,那方带痕的墙砖,却成了京城里无人知晓的“自由碑”——碑上没有名字,只有风吹过砖缝时,隐约传来的、像极了十四年前铁门开启的嘎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