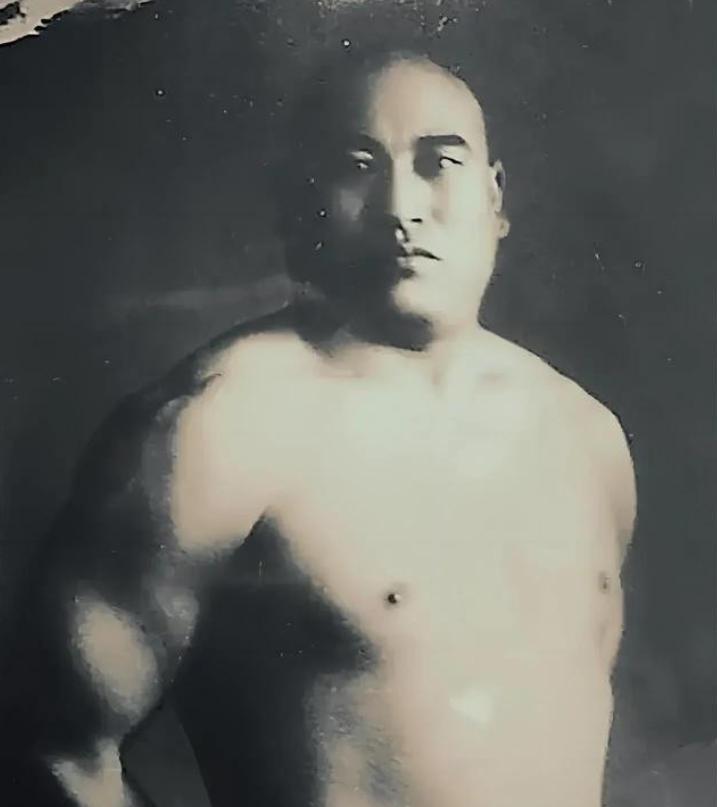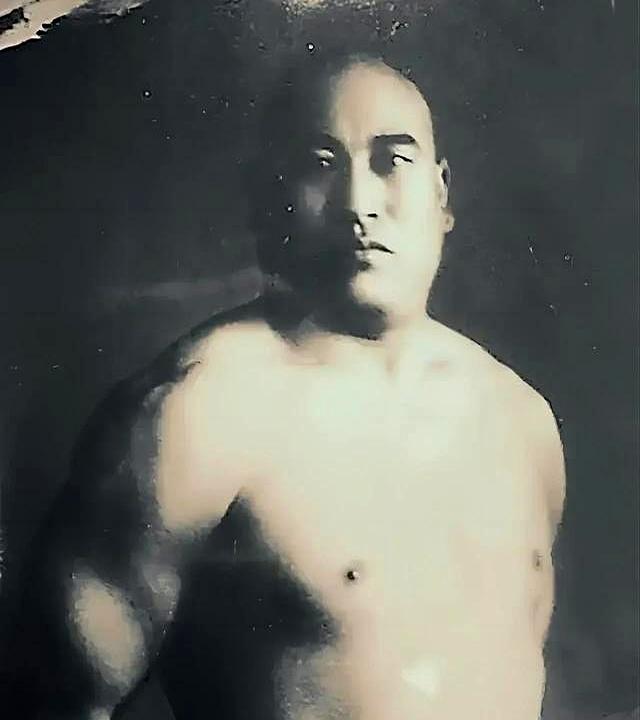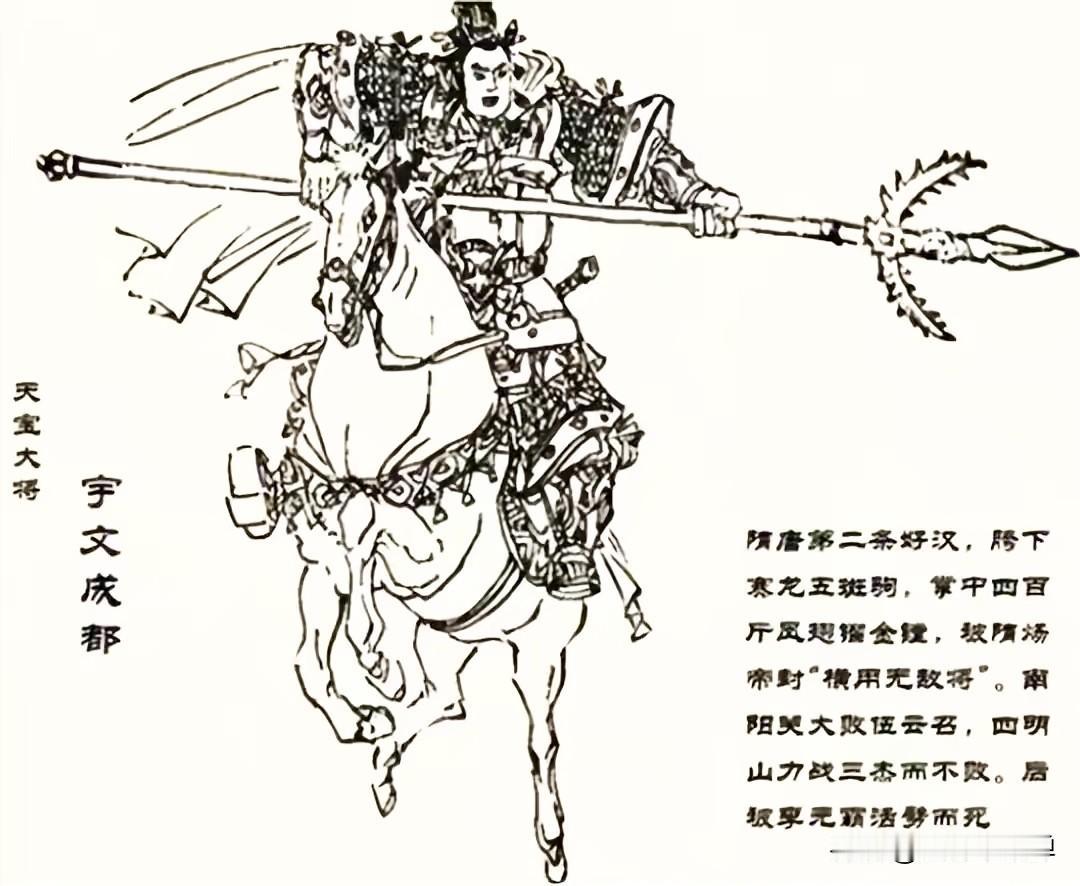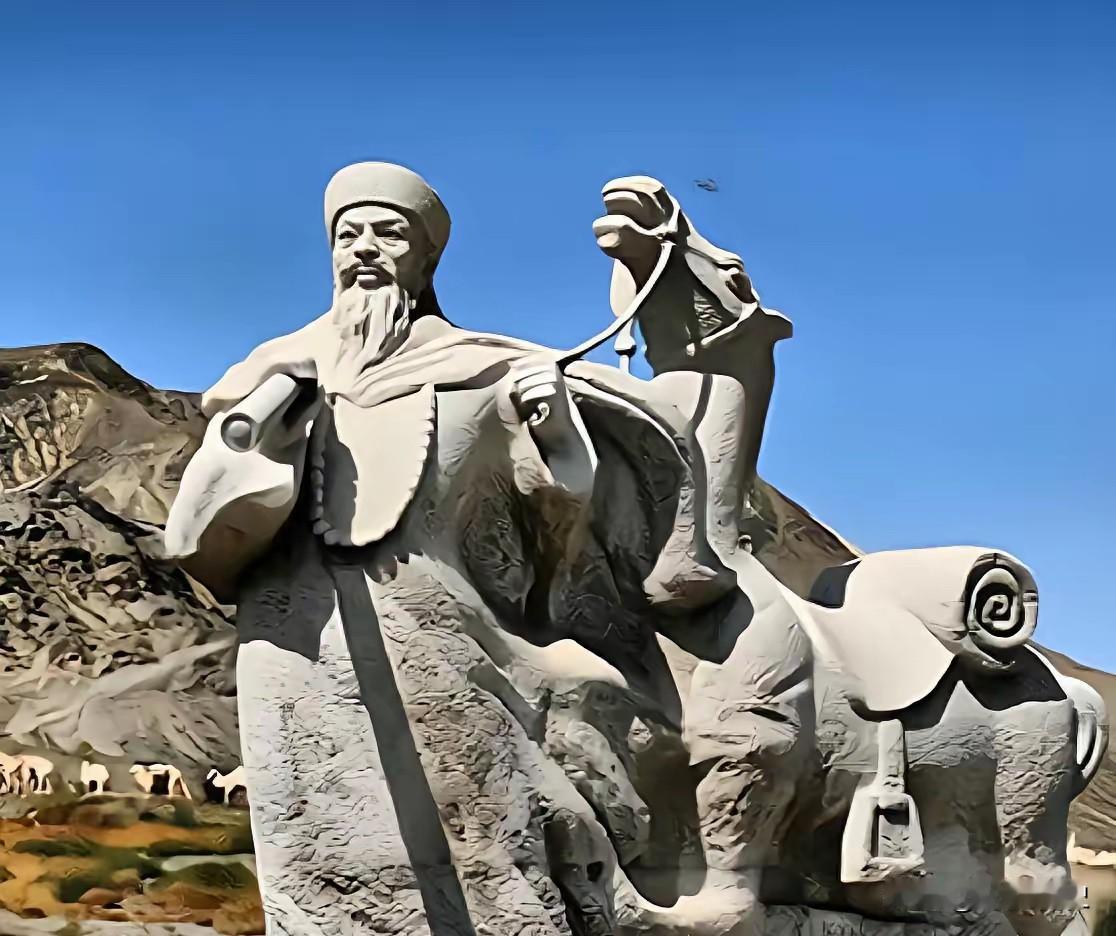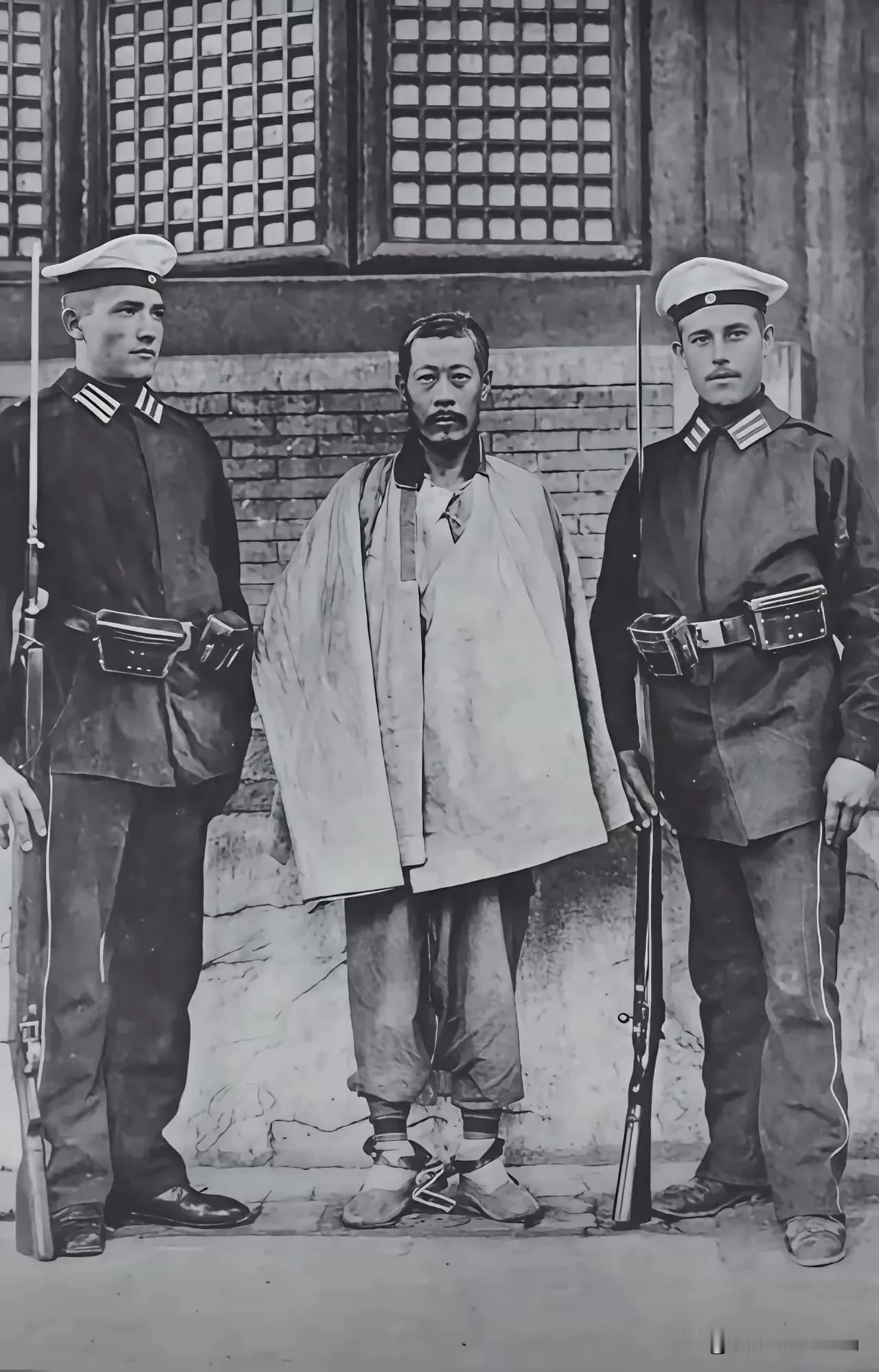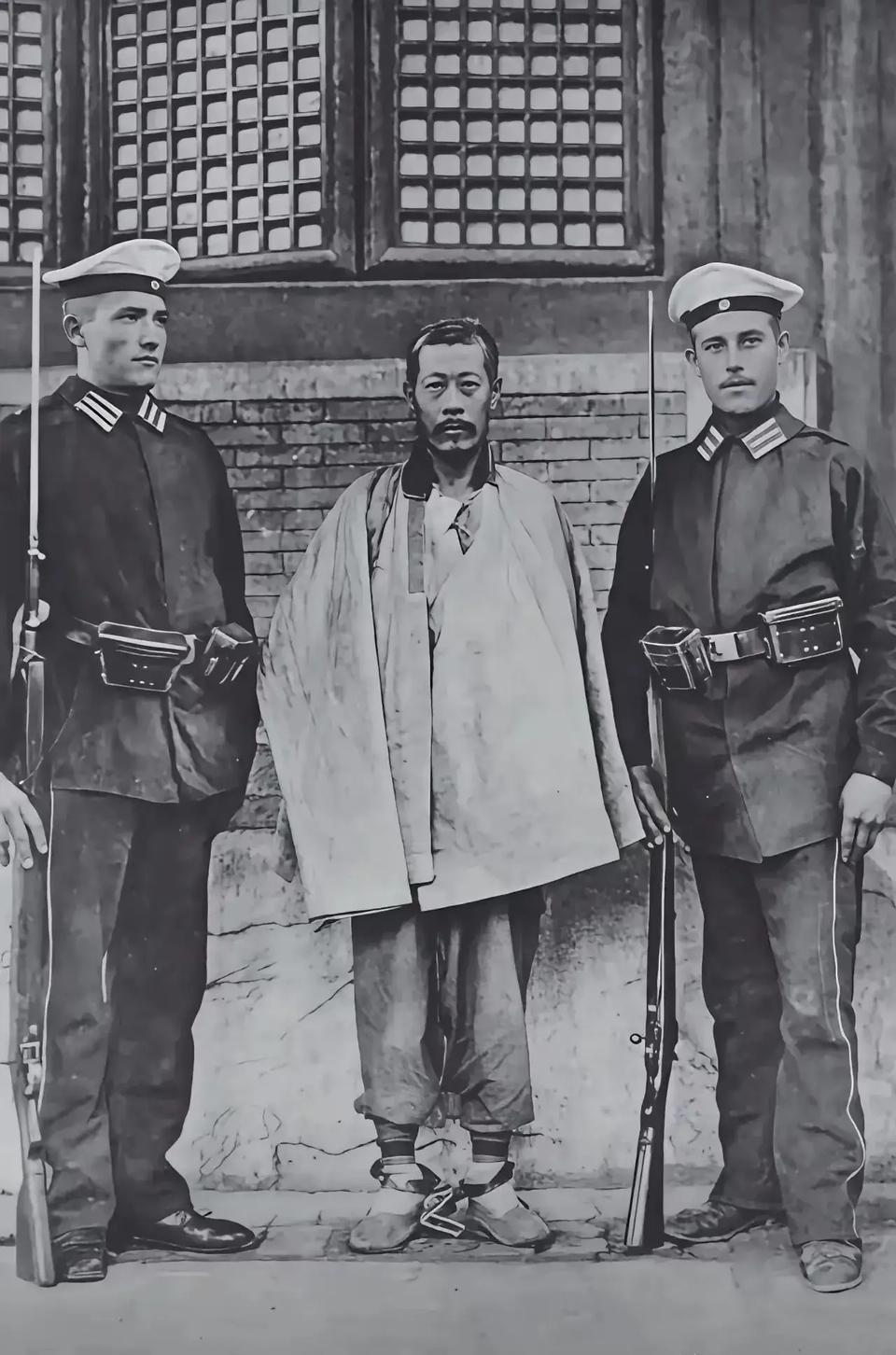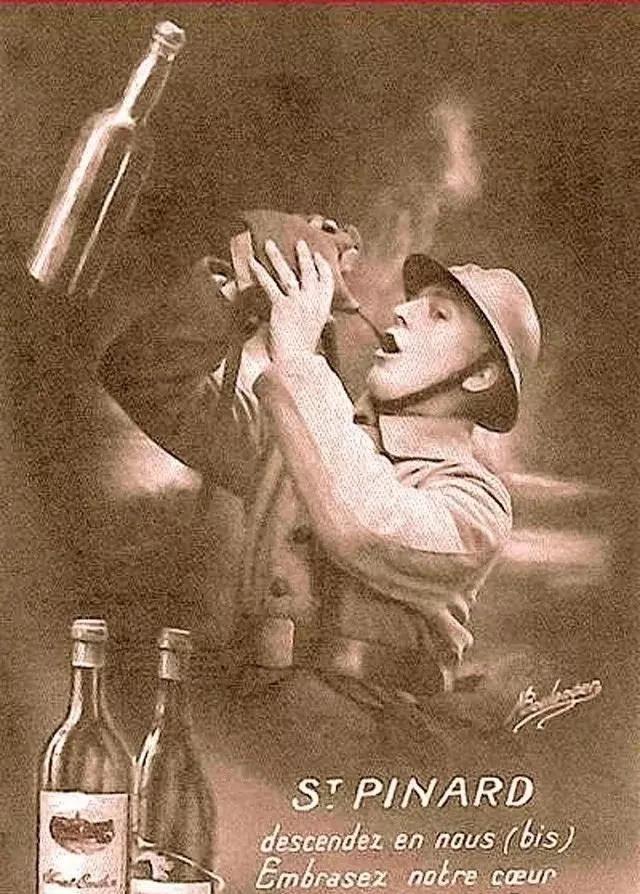清末的武术大师都是人精,比如外号“杨无敌”的杨露禅,自己身强体壮,天天蹲下抓石碾子站起来往上举来训练自己腿背以及肩部的力量,这和现代的中重量级拳击手或摔跤手训练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教别人的时候,尤其是在京城,基本都是教套路为主。 1872 年杨露禅临终前,让弟子抬来半块石碾子。 这是他从陈家沟带进京的 “练武器”,藏着 60 年练武的秘密。 石碾子上的抓痕,刻着他从庄稼汉到 “杨无敌” 的路。 弟子们围在床前,看着他枯瘦的手抚过石碾子凹痕。 “我 10 岁摸这东西,到 60 岁还没摸够。” 他声音微弱。 没人知道,这半块石碾子,陪他熬过了最苦的求艺时光。 1812 年,10 岁的杨露禅在陈家沟帮工,第一次见人练拳。 陈家沟的武场边,他总偷偷看陈长兴练 “炮捶”。 别人休息时,他就蹲在石碾子旁,模仿着抓握的动作。 陈长兴见他痴迷,问:“想练拳?先把这碾子抓起来再说。” 那碾子足有百斤重,他抓得手心流血,也没松开。 从 10 岁到 20 岁,他每天天不亮就去武场。 先蹲在土坑里抓石碾子,抛起再接住,重复百次才练拳。 冬天手冻裂,他就揣把雪搓一搓;夏天中暑,喝碗凉水接着练。 陈长兴看他肯吃苦,终于收他为徒,教他真功夫。 20 岁那年,他开始练 “太极推手”,却先练了半年站桩。 陈长兴说:“腿上没劲,推人先倒,站桩是根。” 他每天站桩两个时辰,腿抖得像筛糠也不挪步。 后来跟师兄弟试手,他一站桩,没人能推动他分毫。 25 岁时,他已能单手抛起百斤石碾子,再接住放回去。 陈长兴教他 “揽雀尾”,说:“发劲要像抛碾子,快且稳。” 他把练劲的窍门记在心里,每天对着树练 “按劲”。 树皮被他按得脱落,掌心却练出了硬茧。 1832 年,30 岁的杨露禅离开陈家沟,第一次与人比拳。 对方是当地武师,出拳又快又狠,他却只出了一招 “单鞭”。 武师被他一推,倒退三步摔在地上,爬起来就拜他为师。 可他知道,自己的功夫还没到家,又回陈家沟接着练。 回陈家沟后,他把石碾子挖深坑埋了半截,增加抓举难度。 每天要练到汗透三重衣,才肯停下来喝碗牛尾汤。 “穷文富武”,他把攒的钱全花在补身体上。 牛尾汤、鸡蛋羹,都是为了扛住高强度的训练。 1840 年,40 岁的杨露禅终于出师,开始在河北传拳。 有人不服气,找他比 “散手”,他只用 “云手” 就化解攻势。 对手出拳打他胸口,他稍一发力,对手就飞了出去。 “这不是花架子,是把石碾子的劲藏在里面了。” 他说。 1850 年,50 岁的他被请进京城,教王公贵族练拳。 见贵族们吃不了苦,他改了教法,先教 “云手”“单鞭”。 有人嫌动作慢,他说:“慢是为了找劲,快了就乱了。” 私下里,他仍在小院练石碾子,保持着每天百次的习惯。 60 岁那年,他在广东府表演推手,对手是当地武举。 武举长得高大,想凭力气赢他,却被他一按就倒。 报纸写:“杨露禅发劲如电,对手似弹丸飞出。” 没人知道,他表演前一天,还在小院练了半宿石碾子。 1872 年临终前,他把半块石碾子分给两个儿子。 “班侯性子急,多练站桩;健侯性子稳,多练抛碾子。” 他还叮嘱:“教拳要看人,能吃苦的教真劲,不能的教套路。” 这话成了杨家传拳的规矩,也让太极拳传得更广。 如今,那半块石碾子被藏在陈家沟太极拳博物馆。 游客们看着石碾子上的抓痕,听讲解员说杨露禅的故事。 他的练武经历,成了太极拳传承的 “活教材”。 后人练拳时,仍会提起那百斤石碾子,提起他掌心的血泡。 杨家后人还保留着他当年的练拳笔记,记着 “抛碾子百次,站桩两时”。 公园老头练的 24 式太极拳,虽没了石碾子训练,却藏着他的智慧。 没人再像他那样抓石碾子练劲,却都记得:“真功夫,得下苦功。” 杨露禅的名字,和他的练武故事,还在太极拳界流传着。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冀人冀事】太极宗师——杨露禅 人民网《青年太极传人探索武术推广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