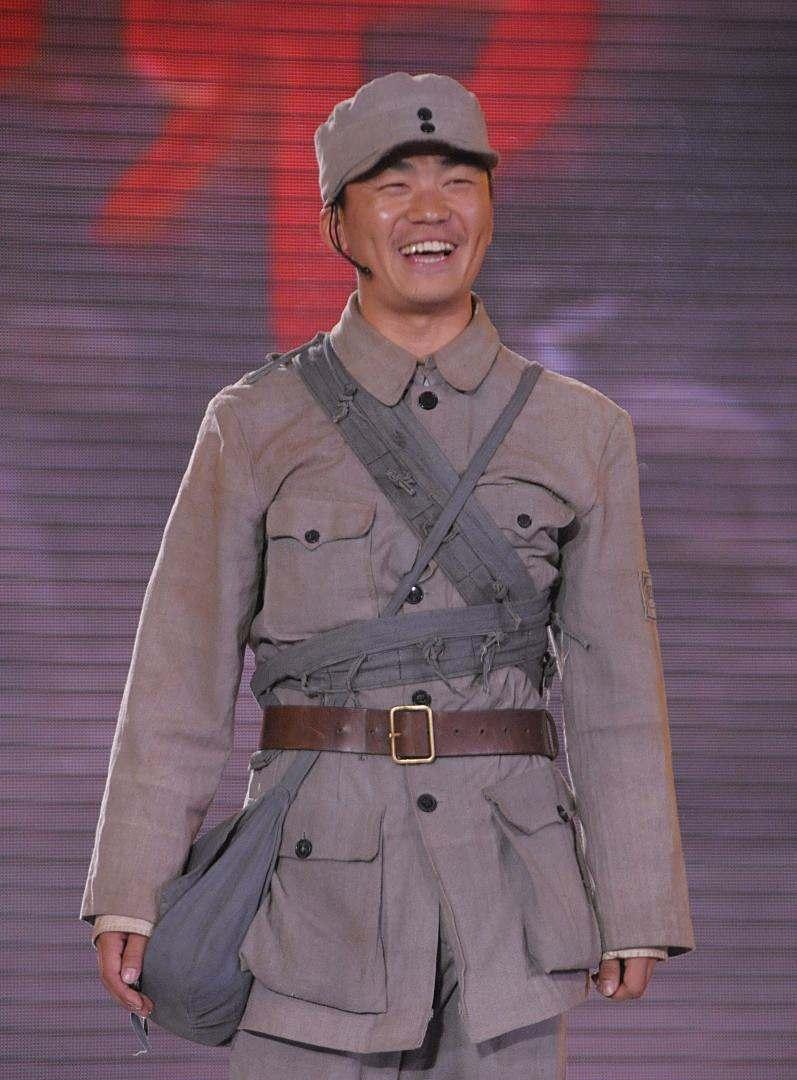1940年初,八路军政委王季龙骑马时,忽发现山梁上有闪光。王心头一震,表面上却假装什么也没发生,继续从容骑马。走了一会,王季龙才遇到部队:“山梁有埋伏,快部署反击!”事后才知道,那里埋伏着70多日军。 王季龙打小在河北曲阳的庄稼地里长大,读过几年私塾,字写得周正,可拿起枪来也不含糊。1937年鬼子进了县城,他正给地主家当账房先生,眼睁睁看着鬼子把粮仓里的粮食往马车上搬,账房里的算盘被一脚踩碎。当晚他就卷了铺盖,揣着母亲给的窝窝头,摸黑找到了正在招兵的八路军,报名时说“我不算账了,我要算鬼子的命”。 在部队里,他是政委,可没人把他当“只会耍嘴皮子”的。上回在涞源打伏击,他跟着突击队摸哨,手里的盒子炮比连长打得还准,硬生生把鬼子的岗楼端了。战士们常说“王政委的眼睛毒”,行军时他总爱盯着山尖尖、树杈子看,说“鬼子的刺刀反光比星星亮,藏不住”。有回宿营,他瞅着村东头那棵老杨树不对劲,让战士们挪到村西,后半夜果然有鬼子摸过来,对着空院子扫了半梭子子弹。 那天他是去师部送情报,就带了两个警卫员。马蹄子踩在冻土上,“嗒嗒”响得清楚,山梁上那一闪,快得像流星,可王季龙的眼没错过。他太熟悉那光了——去年在黄土岭,一个鬼子狙击手趴在石头后,望远镜镜片就这么亮过,差点打中他们的营长。 他勒马的手稳得很,甚至还跟警卫员笑了句“这天够冷的,等会儿到前面村子喝口热粥”。心里头却跟烧着似的,山梁的坡度、光照角度,还有那一闪的高度,都在脑子里转:不是石头反光,不是碎玻璃,是金属,十有八九是鬼子的步枪或望远镜。70多号人,要是呈扇形铺开,部队顺着山沟走,正好钻进人家的口袋阵。 马蹄子没慢下来,可他的耳朵支棱着,听山梁上的动静——风刮过树林的“沙沙”声里,好像混着布料摩擦的“窸窣”声。他故意让马偏离了原定路线,往右侧的斜坡上靠了靠,这样既能保持“闲逛”的样子,又能离山梁远些,给后面的部队争取反应时间。 遇到先头部队时,他脸上的笑瞬间收了,声音压得低却急:“让一营抢占左侧的土坡,架起机枪对着山梁;二营绕到山梁背后,别出声,摸过去就扔手榴弹;告诉炊事班,把锅碗瓢盆都收起来,别弄出响动。”通讯员刚要跑,他又补了句“告诉连长们,等鬼子动了再打,别提前暴露”。 那会儿部队刚走了一夜,战士们眼皮都在打架,可一听王政委的话,没人敢含糊。一营的机枪手老张,冻得手指发僵,愣是用嘴咬着拉开枪栓,把机枪架在了土坎后。 没过半个时辰,山梁上的鬼子果然动了,黑压压一片往下冲,想把八路军堵在山沟里。可他们刚露头,土坡上的机枪就“哒哒”开了火,山梁背后的手榴弹“轰轰”炸成一片。70多个鬼子被前后夹击,没撑一个时辰就垮了,跑掉的没几个。 清理战场时,战士们在山梁上捡到个摔碎的望远镜,镜片还沾着泥。老张拍着王季龙的肩膀笑“政委,你这眼睛比望远镜还厉害”,他却蹲在地上,摸着那镜片叹口气“要是慢一步,倒下的就是咱的人”。 有人说,政委管思想就行,打仗是指挥员的事。可王季龙们不这么想。在敌后那片土地上,政委的眼睛得能看敌情,手里的枪得能护弟兄,嘴里的话得能鼓士气。他们不是天生就沉着,是肩上的责任逼着自己——身后是战友,是百姓,慌一秒,可能就是一条命、一个村的安危。 你说,那山梁上的一闪,换个人会不会当成眼花?王季龙的从容,到底是胆子大,还是心里装着太多人,不敢不沉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