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青首创骑兵集团纵深突袭战术,在漠北决战中以武刚车结阵、弩兵远程消耗、骑兵反冲击的协同作战,击溃匈奴单于主力。七战七捷的战争艺术,广为传颂。
卫青位极人臣却始终低调,将汉武帝赏赐分予士卒,宽容李敢行刺,敬重直臣汲黯。其“不养士、不结党”的作风,避免了汉初韩信式的悲剧。
如此丰功伟绩,司马迁和苏轼却似乎看不上,评价卫青时甚至有些刻薄。
司马迁暗讽其“以和柔自媚于上”。

两位文史大家的评价,多少反映出当时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
宋代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武将地位一落千丈,文官集团通过科举制度垄断话语权。卫青作为外戚(汉武帝皇后卫子夫之弟)崛起,触动了文人“凭本事上位”的优越感。苏轼认为卫青的成功是“关系户”对“做题家”规则的破坏,其评价本质是文人对武将阶层的系统性歧视。

此外,汉唐外戚干政的教训(如王莽篡汉、杨国忠乱唐)令宋人对外戚武将充满警惕。卫青虽功勋卓著,但其出身卑微、因姐姐得宠而受提拔的经历,被后世苏轼视为“破坏政治伦理”的典型。卫青的传奇(奴隶→将军→善终)打破了“出身决定论”,而文人阶层更倾向赞美周瑜(士族出身)这类符合士大夫审美的将领。这种选择性记忆,以出身论英雄的逻辑,忽视了卫青逆袭的军事才能。
还有,苏轼个人的身世和处境也是一大因素。苏轼屡遭贬谪的经历,使其借批判汉武帝“无道”暗讽宋神宗变法。卫青作为汉武帝的“忠犬”,成为苏轼宣泄政治不满的靶子。他甚至要求武将既需战功赫赫,又要如汲黯般“铁骨铮铮”,否则便是“奴才”,这种道德绑架暴露了文人的双重标准。
同样,卫青以奴隶出身通过姐姐卫子夫得宠进入权力中心,其崛起路径触动了司马迁的士大夫身份认同。汉代虽未形成严格门阀制度,但司马迁出身世家(司马氏为周朝史官后裔),对“裙带关系”存在本能的排斥。卫青被归入《佞幸列传》的写法(尽管强调其“材能自进”),本质上是对非正统晋升渠道的否定。相比之下,李广作为陇西李氏之后,其世家背景更符合司马迁对“正统将领”的想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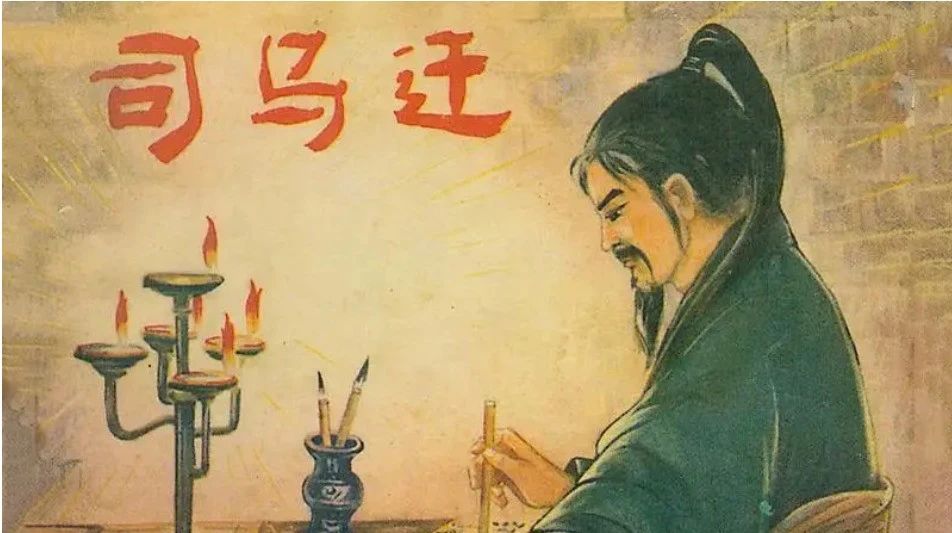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