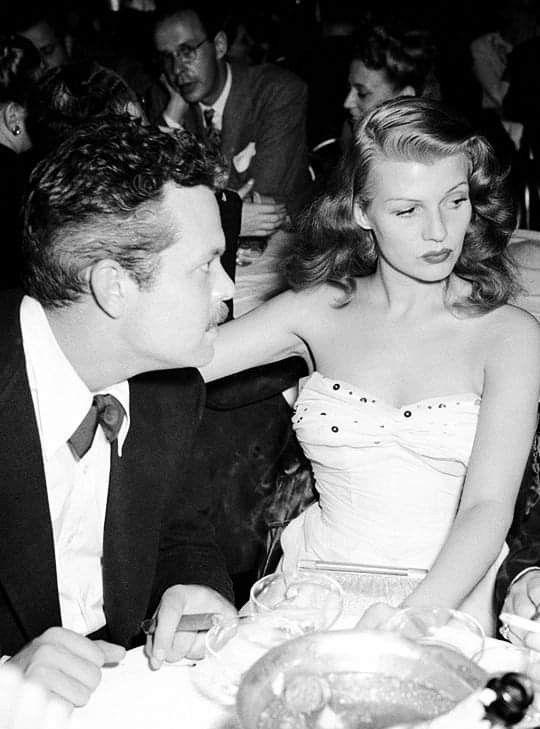勃列日涅夫死的那天,没人惊讶,保镖梅德韦杰夫站在卧室门口,看着床上的躯体一动不动,心跳已经停了几个小时,他早就等着这一天,但真来了,还是像掉进冰窖。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2年11月10日的清晨,莫斯科的郊外仍笼罩在一场夜雪之后的寂静中,白色的积雪覆盖了扎列奇耶别墅的屋顶与庭院,一切都显得格外安详而冷峻,别墅内部却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凝滞气息,那天早上,没有人敲响门铃要求报纸,也没有熟悉的铃声召唤警卫送来咖啡,屋内的静默,仿佛在预示一种沉重的终结早已悄然降临。 当贴身人员进入卧室时,床上的人已无呼吸,身体平躺,面容蜡黄,嘴角还残留着前夜未擦净的泡沫,似乎在沉睡中悄然离世,医生赶到时,仅看了一眼便断定,心跳早已停止数小时,没有仪式感,没有哀恸的哭声,甚至没有一丝混乱,这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一段时代的句号已经落下。 事实上,死亡并非突如其来,三天前在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纪念阅兵,是一次公开的警示,站在列宁墓前的那位苏联最高领导人,穿着厚重呢大衣,双手紧紧握着扶手,试图维持身体的平衡,他的站姿僵硬,连基本的军礼动作都无法完成,人群中并未发出哗然,但所有目光都在注视着那副早已无力支撑的身躯。 阅兵场上,一枚勋章从他的手中滑落,发出清脆一响,跌入静默的空气中,身边的医护人员神色骤变,护卫们下意识将急救药物握在手里,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那天结束时,他的脸色发青,言语模糊,几乎无法完整表达一句话,然而仅仅几个小时后,他依然准时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桌前,签署官方文件,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健康状况便如溃堤之水般一发不可收拾,心脏病、肺气肿、白血病接踵而至,他的身体逐渐成为药物维系下的躯壳,尽管医生多次强烈建议休养,政治局内部也屡有低声议论交班之事,但终究没有任何改变,他拒绝住院,照常出席会议、主持文件审阅,仿佛只要坐在那张办公桌前,就能将死亡拒之门外。 1982年5月的一次中风,使他的语言能力和肢体动作受到严重影响,讲话含糊不清,半边身体行动迟缓,每次出席公共活动,都要依赖他人搀扶,他仍坚持每日工作数小时,哪怕需要别人翻页、执笔,哪怕签字时手指不住颤抖,哪怕钢笔失手掉进火盆,他依旧要坐在最高位上,维持那层外在的权威与象征。 他的坚持并非出于责任感,也不完全是权力欲的驱使,那更像是一种对终结的抗拒,对交棒的不信任,他知道,一旦离开岗位,身后那张权力的椅子便不再属于他,而后继者的每一步动作,都可能彻底否定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他而言,位置即生命,坐着才能存在。 勃列日涅夫的晚年在沉重与重复中度过,每天服用大量安眠药与镇静剂,按时注射激素,饮食清淡至极,身体却依旧日渐衰败,他不再拥有清晰的意识,也无法维持基本的工作节奏,可在外界眼中,一切仍然有条不紊地运行着,正如苏联政府长久以来维系的那种表面秩序——即使内部早已腐朽,表面依旧要挺直脊梁。 死亡的清晨,苏联的高层反应迅速,九点前,克里姆林宫已收到消息;十点半,紧急会议召开;中午前,讣告草拟完毕,整个过程冷静、精准,仿佛只是在执行一项早已演练过无数次的程序,第二天上午十一点,苏联全国广播系统开始播报死讯,电视画面切换为黑白纪录片,背景配乐是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庄严肃穆,却毫无情感波动。 街头的人们并未表现出惊愕,广播喇叭下,行人低声交谈,语气平常,公交车照常运行,只是车厢内安静了些,大多数人的反应是轻声说一句“终于结束了”,然后继续自己的日常,对他们而言,这位在位长达十八年的领导人,早已成为某种远离现实的象征,失去了活力,也失去了意义。 国葬在雪未融化的红场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政要云集,场面宏大却沉默,军乐低缓,旗帜垂落,灵柩缓缓通过广场,站在队伍后方的身影,没有流泪,也没有动作,只是眼眶微红,国家仪式在形式与程序中完成,仿佛在告别一个人,也在送走一个时代。 勃列日涅夫统治苏联的十八年,是稳定的十八年,也是停滞的十八年,他以集体领导起家,最终却把权力集中于一人,他喜欢勋章,喜欢荣誉,晚年几乎将所有头衔都收入囊中,他反对改革,厌恶变动,将整个国家钉在计划经济的旧轨上,任由效率下滑、体制老化、人民不满,他的身体如同国家机器,在药物和惯性中维持着表面的运转,直到彻底崩溃。 他的死亡,并不是苏联崩溃的起点,却是一个历史节点的确认,随后上台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皆年老多病,改革受限;戈尔巴乔夫虽有雄心,却未能稳定局面,国家的问题早已积重难返,死亡不过是将裂缝照进了阳光之中。 信息来源:梅德韦杰夫,《任务:守卫勃列日涅夫》,莫斯科红星出版社,1995年版。


![马筱梅那么瘦吗[???]???看她以前的老照片,都是圆脸的,脸蛋胶原蛋白满满挺](http://image.uczzd.cn/604410436000324264.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