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红婵拟保送暨南大学”的评论区,我看到了最恶心的一幕
北京时间5月6日,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公示了1101名拟保送大学的优秀运动员名单,在这份凝聚着汗水与荣誉的名单中,18岁的跳水奥运冠军全红婵赫然在列,她拟被保送至暨南大学运动训练专业,这本该是体教融合的典范案例,却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掀起了一场关于“公平”的腥风血雨,说真的,在“全红婵拟保送暨南大学”的评论区,我看到了最恶心的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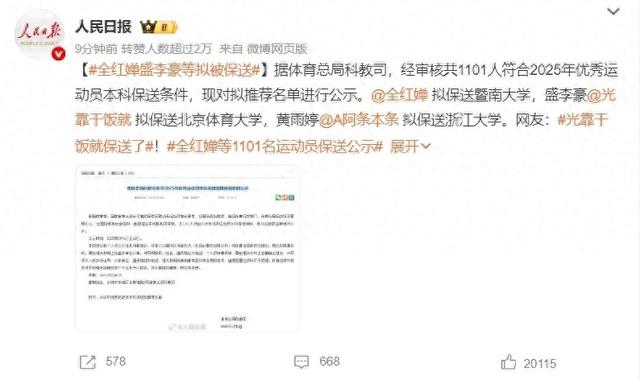
“小学都没好好上!”“读完了一样是文盲!”“寒窗苦读的学子情何以堪?”……在相关新闻的评论区,类似的言论如潮水般涌现,全红婵,这位14岁打破世界纪录、18岁手握三枚奥运金牌的“天才少女”,被推向了舆论的暴风眼,有人质疑她仅有“小学学历”,有人嘲讽她“听不懂大学课程”,甚至将她的保送资格称作“对教育的侮辱”
然而,这些质疑大多建立在对事实的误读之上,全红婵并非“小学学历”,自东京奥运会夺冠后,她便被广东实验中学录取,通过网课和定制化教学完成了高中学业,符合保送政策中“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的要求,而暨南大学的运动训练专业,本就是国家特设的“冠军班”,课程涵盖运动康复、赛事管理等实践性极强的科目,与她的职业经历高度契合
苏炳添、谢思埸等前辈均从该校毕业,并将竞技经验转化为学术成果,例如苏炳添的课题《不同湿度环境下田径运动员肌肉激活模式》

运动员保送大学并非“特权”,而是一项已实施近40年的制度设计,早在1986年,原国家体委便规定奥运奖牌获得者可免试入学;2002年,政策进一步扩大至全国赛事前三名选手,这一制度的核心逻辑,是解决运动员因封闭训练导致的文化教育缺失,以及退役后的生存困境,数据显示,中国现役专业运动员中仅5%能通过保送进入高校,而退役运动员中60%面临就业难题
全红婵的案例正是这一政策的典型体现,她以国际级运动健将身份保送,符合《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2025年高校保送录取优秀运动员工作的通知》中“奥运项目破世界纪录”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她的选择并非孤例:射击冠军盛李豪拟入读北京体育大学,巴黎奥运冠军黄雨婷保送浙江大学,这些运动员的专业选择均与自身项目紧密相关,且需通过高校的综合考核

争议的背后,实则是社会对“成功”定义的撕裂,一方面,竞技体育的极致成就被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精英教育”;另一方面,公众对学历的焦虑蔓延至奥运冠军身上,有网友质问:“凭什么他们能跳过高考?”却忽略了运动员的付出,全红婵每天训练7小时,春节仅休息3天;为克服发育关,她曾增重7公斤并重塑技术动作,最终在巴黎奥运会卫冕,一块奥运金牌的难度,某种程度上远超高考状元;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争议暴露了对运动员“工具化”的潜意识,过去,运动员被视为“荣誉机器”,退役后往往陷入困境:韩国速滑冠军卢善英在便利店打工,日本体操名将池谷幸雄街头卖艺……反观中国,邓亚萍取得剑桥博士学位后投身体育产业,李宁从北大硕士转型为商业领袖,全红婵们在巅峰期入学,正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为人生下半场铺路

除此以外,“运动员保送挤占普通考生名额”的说法,实为误解,高校为运动员开设的单招通道与普通高考录取互不冲突,且录取人数仅占极小比例(2025年保送名单共1101人),此外,高校对运动员学生的管理并未放松;教育的终极目的,本应是让每个人找到适配的成长路径,当社会争论“全红婵该不该上大学”时,或许更该追问: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成功不止一种模样?毕竟全红婵用汗水书写了另一种人生答卷

 云霞育儿网
云霞育儿网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