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餐厅已沦为阶级的标尺:有钱人根本不会吃这种食物
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布朗斯维尔社区,12岁的罗斯·奎格利每天放学后都会戴上手套,走进学校三楼的教室。
这里没有课桌和黑板,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LED灯照耀下的水培农场架子。
她熟练地采摘莴苣、羽衣甘蓝和薄荷,这些蔬菜将被送到学校食堂或低价卖给社区居民。
对罗斯来说,这是她第一次知道“食物沙漠”这个词——在这个快餐店比超市更多的社区,新鲜蔬菜曾是奢侈品。

罗斯的故事只是美国贫富食物差距的冰山一角。
在这个国家,肥胖率高达45.6%,但讽刺的是,越贫穷的人越容易发胖。
富人瘦、穷人胖,美国餐厅已成为阶级的标尺。

走进美国任何一家超市,货架上最显眼的永远是薯片、汽水和冷冻披萨。
一包2美元的薯片足够让人吃饱,而同等价格的菠菜可能只够做一盘沙拉。
这种价格倒挂并非偶然。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美国政府大力补贴玉米种植,过剩的玉米被加工成高果糖玉米糖浆:这种甜味剂成本极低,迅速占领了食品工业。从碳酸饮料到面包酱料,它无处不在。
在纽约布朗斯维尔,学校周围500米内有20多家快餐店。
校长格雷戈里·杰克逊发现,许多学生一日三餐都靠鸡块和薯条度日,导致糖尿病前期患者激增。
“当快餐是唯一选择时,你怎能责怪孩子们不健康?”他无奈地说。

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贫困性肥胖”:2023年,美国4600万人依赖食品券生活,但这些补贴主要覆盖汉堡、热狗等高热量食品。
穷人不是吃不饱,而是被廉价糖分和脂肪填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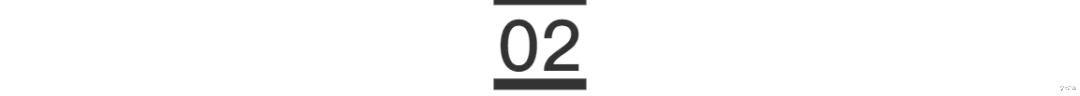
当罗斯在校园农场忙碌时,曼哈顿上东区的精英们正享用着每磅20美元的有机羽衣甘蓝。
富人的餐桌上,草饲牛肉、野生三文鱼和冷压果汁是标配,他们甚至愿意花300美元上一节“冥想饮食课”。
这种差异直接反映在身体上:年收入5万美元以下人群的肥胖率是收入15万美元以上人群的2.3倍。
这种分化不仅是金钱游戏。
在印第安纳州门西市,64%的居民生活在“食物沙漠”——最近的超市需要转乘两趟公交才能到达。
当他们终于拎着变形的面包和蔫掉的蔬菜回家时,富人们正通过生鲜配送App,让农场直送的新鲜食材一小时抵达厨房。
健康成了需要支付运费的奢侈品。

食品工业的逐利本能将这场差距推向极致。
麦当劳的“超大套餐”策略是个经典案例:只需多付1美元,薯条和可乐的份量就能翻倍。
这对精打细算的穷人极具诱惑,却让他们摄入超过日均所需的热量。更隐蔽的是,大公司通过游说让披萨被认定为“蔬菜”——因番茄酱含蔬菜成分,使学校午餐标准形同虚设。
这种扭曲的市场逻辑甚至改变了文化。
在休斯顿的墨西哥裔社区,“美式中餐”用糖醋酱包裹炸鸡块,用重油炒饭替代杂粮。
而原本以清淡著称的亚洲饮食,也在廉价热量改造下成为肥胖推手。

“我们不是在吃文化,而是在吃资本的流水线产品。”社区活动家玛利亚·冈萨雷斯感叹道。

当穷人用汉堡填饱肚子时,他们也在吞下健康代价。
2024年《美国医学会内科学》的研究显示,食物不安全人群的早逝风险比正常人高81%,预期寿命缩短4.5年。
在布朗斯维尔,糖尿病发病率是曼哈顿的3倍,而这些患者往往因无力支付胰岛素费用被迫截肢。
这种健康差距还带着种族烙印。
非裔和拉美裔社区因历史性歧视政策,更易陷入“快餐疾病贫困”的循环。
正如公共卫生专家托里安·伊斯特林所说:“当一个人的邮政编码比基因更能预测寿命时,我们就该反思这是否还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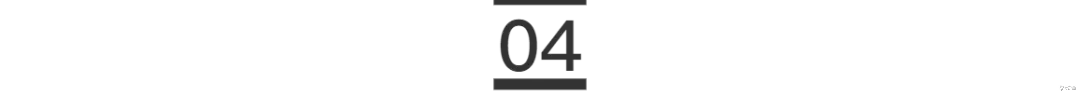
面对系统性的不公,普通人正在用泥土和种子发起反击。
在布朗斯维尔协作中学,学生们建起的水培农场每周产出数十磅蔬菜。
这些作物不仅进入食堂,还以市场价一半的价格卖给社区。
17岁的卡洛斯通过项目学会了农业和营养学,现在他每周给邻居做健康烹饪示范:“我们要证明穷人配得上更好的食物。”

类似的草根运动在全美开花。
明尼苏达州的“SparkY”组织在学校建造了130个水培系统;纽约太阳工程帮助96所学校建立室内农场。
这些项目不仅提供食物,更重塑认知:当孩子们亲手种出羽衣甘蓝时,他们开始拒绝自动贩卖机里的薯片。
当罗斯把农场蔬菜带回家时,她的母亲仍习惯性地走向快餐店,毕竟改变数十年的饮食惯性需要时间。
但数据带来希望:参与校园农场的学校中,42%的学生增加了蔬果摄入量,有些社区甚至推动地方政府通过《健康食品法案》。
这场餐桌上的贫富战争,本质是关于“谁有权利健康生活”的较量。
当资本用汉堡建造肥胖帝国时,普通人正用菜园挖开裂缝。
活动家杰奎琳·汉诺曼说:“饥饿不是因为食物不够,而是因为公平获取的通道被堵死了。”
或许在某天,当每个社区都有新鲜的羽衣甘蓝,当健康不再是金钱的附庸,罗斯们才能真正告别“贫穷性肥胖”的魔咒。
本文作者 | 老A
责任编辑 | 蓝橙
策划 | 蓝橙
 云霞育儿网
云霞育儿网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