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照顾了瘫痪邻居苏姨整整11年。
看着她将760万拆迁款全数给了久无音讯的侄女。
她去世后,我以为自己11年的付出就此无声落幕。
直到银行打来电话,通知我去办理一份苏姨设立的定向遗赠手续。
在会客室里,我看清屏幕上的条款,瞬间僵在原地。
01
我从银行走出来,手里紧握着一个暗黄色的文件袋,午后的阳光白晃晃地刺眼,可我却觉得浑身一阵阵发冷。
苏姨走了,就在昨天清晨,我发现的她。
她静静躺在床上,面容安详得仿佛只是睡着,床头柜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五个用钢笔写下的字:“小江,谢谢你。”
我陪了她整整十一年,看着她把七百六十万拆迁款一分不剩地给了那个十几年杳无音信的侄女,看着她在公证处佝偻着背、颤抖着手签下名字,也看着那个叫孙丽的女人在拿到钱后,笑容如何一点点冷却,身影如何一次次淡出。
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一个心软的老人被所谓的血缘捆住了手脚,一个傻子的十一年时光轻飘飘地,换不来半点回响。
直到今天上午,那通来自银行的电话打断了这一切。
02
记忆被拉回到二零一二年五月,我刚搬进安宁小区的第三天。
老旧楼道的窗玻璃蒙着厚厚的灰,阳光透进来也是昏昏沉沉的。
我正收拾着三楼的屋子,忽然听见头顶传来“咚”的一声闷响,紧接着是细微的、断断续续的呼救声。
我冲上六楼,推开那扇虚掩的房门,看见苏姨连人带轮椅翻倒在地上,额角磕破了皮,渗着血丝。
她喘着气说只是想倒杯水喝,轮椅滑了一下。
我问她家里怎么没人照顾,她只是摇摇头,苦笑着说:“就我一个啦。”
从那之后,我每天上下楼都会特意绕到六楼看一眼,后来干脆每天多做一份饭菜给她送上去。
她总过意不去,拉着我的手说:“小江,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
而我总是回答:“我父母走得早,能照顾您,我心里反倒踏实些。”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
每天早上七点,我准时敲响她的门,有时候是清粥小菜,有时候是面条煎蛋。
她的女儿远在海外,很少打电话来;她从小养大的侄女孙丽,自从结婚后就再没露过面。
我渐渐成了她唯一能说说话、依靠一下的人。
我记得一五年冬天特别冷,半夜里她心脏病发作,我背着她一口气冲下六层楼梯,她在背上气若游丝地说:“小江……我要是走了,你别难过……”
好在送医及时,她捡回一条命,我垫付了两万多的医药费。
她醒来后一直念叨要还钱,我握着她的手说:“您好好活着,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
03
二零二三年开春,小区里贴出了拆迁公告,整栋楼都沸腾起来。
苏姨家房子面积大,算下来能拿到七百六十万补偿款。
消息传开后没多久,那个十几年没联系的侄女孙丽就出现了。
她提着大包小包的营养品,一进门就抱着苏姨掉眼泪,口口声声说:“姑姑,都是我不好,这些年太忙了没顾上看您……”
苏姨被她哭得心软,拉着我的手悄悄说:“小江,我知道你对我好,可丽丽毕竟是我弟弟唯一的女儿,血缘亲情是断不了的。”
我没再劝她,只是陪着她去了公证处。
看着她在赠与协议上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名字,手抖得厉害,我就站在她身后一步远的地方,什么也没说。
孙丽拿到公证书后,脸上的笑容明显淡了不少,从开始的“天天来陪您”慢慢变成“这周加班”,后来连电话都很少接了。
苏姨的身体渐渐不如从前,有一次她想问孙丽借点钱去医院做检查,电话那头的声音一下子冷了下来:“姑姑,钱是您自愿给的,现在怎么又要往回要呢?”
那天晚上,苏姨坐在窗边发了很久的呆,最后轻声对我说:“小江,我这辈子好像总在讨好别人,可到头来,什么都没留住。”
第二天清晨,我去送早饭时,发现她已经静静走了。
我给她女儿发了消息,隔了七八个小时才收到回复:“知道了,我会尽快安排时间回国。”
我打给孙丽,她只“哦”了一声,便挂断了电话。
葬礼那天,只有我和隔壁两位老邻居到场,风很大,吹得人眼睛发酸。
04
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我正在整理苏姨留下的几件旧物,手机忽然响了。
是一个本地的固定电话号码。
“请问是江远先生吗?”对方是个声音温和的女声。
“我是。”
“您好,这里是商业银行安宁支行,关于苏婉茹女士在我行设立的一份定向遗赠,需要您本人前来办理相关手续。”
我愣住了,一时没反应过来。
“遗赠?”
“是的,苏女士生前在我行办理了业务,指定您为唯一受益人。请问您今天方便过来一趟吗?”
我看了眼窗外明晃晃的天,说:“好,我现在过去。”
银行里冷气开得很足,我跟着工作人员走进一间安静的会客室。
她递给我一杯温水,客气地请我出示身份证件,又让我在电子屏上按下指纹验证。
等待系统响应的几秒钟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直到屏幕亮起,跳出一行清晰的账户信息,旁边附着一行细小的备注文字。
我看清那行字的瞬间,整个人像被钉在了椅子上,动弹不得。
窗外依然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可我耳朵里却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
05
我看着屏幕上那行字,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呼吸都有些困难了。
那行备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本账户为不可撤销生前信托,受益人为江远先生,自受托人苏婉茹女士身故之日起,每月可支取人民币三万元作为生活补助,本金部分永久锁定,仅可由受益人本人用于医疗、教育、购房三项指定用途,详细条款见附件。”
旁边显示的总资产数额,是整整齐齐的一千万元。
不是七百万,是一千万。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连握着平板边缘的指节都泛白了。
银行的工作人员轻声提醒道:“江先生,您需要查看一下具体的文件内容吗?苏女士还留下了一封亲笔信。”
我这才回过神来,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些:“好,请给我看看。”
工作人员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个米白色的信封,上面的字迹我认得,是苏姨用那支老式钢笔写的,墨水有些晕开,但每一笔都透着认真:“给小江。”
我小心地拆开信封,里面是三页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
信的开头这样写道:“小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姨应该已经走了,别难过,我这把年纪走得很安心,尤其是想到最后这些年有你陪着。”
“那一千万里,有七百六十万是拆迁款,剩下的二百四十万,是我这些年来一点点攒下的退休金,还有早些年卖掉老伴儿留下的几件老物件换的钱。”
“我知道你会奇怪,为什么明明还有这笔钱,我却非要把那七百万给丽丽,其实姨不糊涂,姨只是想最后试一试,看看血缘到底还值不值得。”
“结果你也看到了,丽丽那孩子让我寒了心,但这样也好,试过了,我就彻底不欠我弟弟什么了,这笔钱给得心甘情愿,只是委屈了你,陪着我这个老太婆演了这么一出戏。”
“剩下这些钱,姨留给你,不是报答,姨知道你这孩子不图这个,这是姨的一份心意,也是姨最后能为你做的一点事。”
“每月三万块,不多,但足够你过得轻松些,不用再为了加班费累到半夜,也不用再省吃俭用地给我垫医药费了,本金留着,将来娶媳妇、买房子、或是家里有个急用,都能应应急。”
“别推辞,也别觉得有负担,你就当是姨提前给你准备的结婚红包,姨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能亲眼看到你成家,找个好姑娘,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信的后半部分,苏姨絮絮叨叨地叮嘱了许多生活琐事,让我天冷了记得加衣,胃不好要按时吃饭,别总吃外卖。
最后一行字,墨迹格外深些:“小江,谢谢你,让我这最后的日子,过得像个有家的老人,下辈子要是还能遇见,姨给你做亲妈。”
我的视线模糊得厉害,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一滴一滴砸在信纸上,晕开了那些温暖的笔迹。
06
办理完所有的手续,走出银行大门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夕阳把天空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色,街道上车流如织,行人匆匆,世界依然在按照它原有的节奏运转着。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彻底改变了。
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沿着街道慢慢走着,手里紧紧攥着那个装着所有法律文件和银行卡的信封。
苏姨说得对,我确实从没想过要什么回报,这十一年来的每一天,我是真心实意地把她当成长辈来照顾的。
那种在她需要时被需要的感觉,那种每天有人等着我送饭去的牵挂,早已成了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现在,这笔突然降临的财富,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我内心层层叠叠的波澜。
我不是圣人,我需要钱,每个月超市理货员那点微薄的薪水,扣除房租水电后所剩无几,我甚至不敢轻易生病。
这一千万,哪怕只是每月三万的生活费,也足以让我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同时,一股沉甸甸的负担感也随之而来。
这笔钱背后,是苏姨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托付,她希望我过得好,希望我轻松些,希望我拥有她没能亲眼看到的安稳未来。
我该怎么用这笔钱,才不算辜负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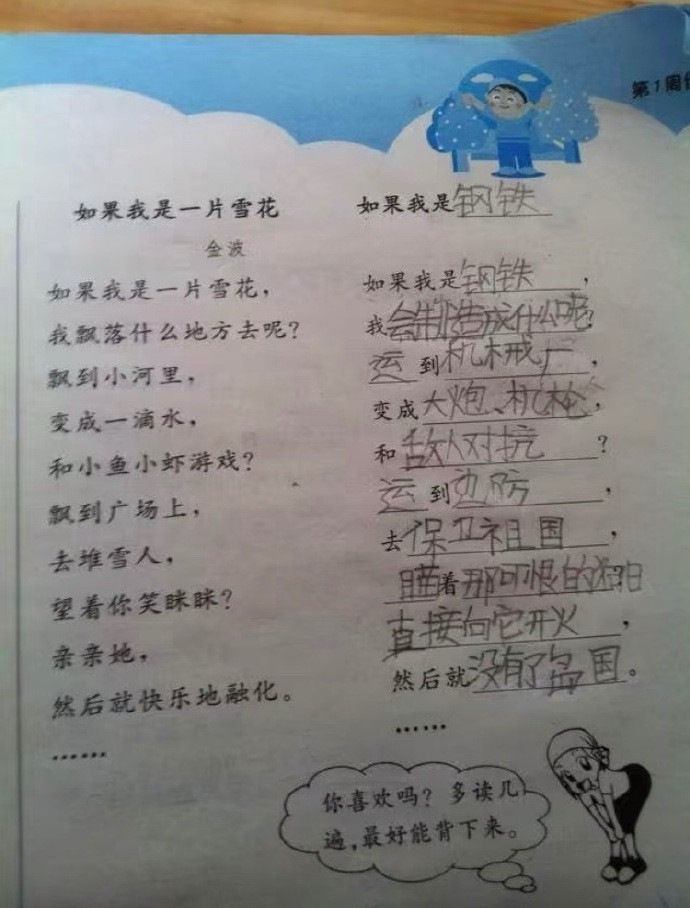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