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夏天的上海,法租界外滩的洋行大班们正焦灼等待消息——北方的战火已经烧到天津,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突然放出话来:要与各国领事签订协议,“保全东南中外商民”。六天后,《东南保护约款》签字,长江沿岸与苏杭内地划入“督抚保护范围”,上海租界则由列强自行看守。
这场被称为“东南互保”的事件,历来被很多文章写成“地方督抚对抗中央的叛逆之举”。但翻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张之洞档》影印件、上海图书馆藏《刘坤一未刊函札》残页,再看《申报》1900年6月26日的社论,你会发现:所谓“抗旨”不过是表面文章,真正暴露的是晚清中央与地方之间一道早已裂开的制度缝隙——当朝廷的决策与地方的实际利益无法调和时,双方都在用“沉默”与“默契”做一场心照不宣的交易。
一、从一封电报说起:督抚的“私下共识”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发布《宣战诏书》,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这道诏书传到武昌时,张之洞正在签押房看《京报》。据《张之洞全集》收录的电稿,他当天就给南京的刘坤一发去一封急电:“北事已不可为,东南各省若再与列强开衅,糜烂更甚。似宜与各领事订约,共保中外商民,以维大局。”
刘坤一的回电比想象中快。次日,上海图书馆藏《刘坤一未刊函札》残页里夹着他的亲笔回笺(缺后半段,但与英国国家档案馆藏英译电可缀合):“香帅(张之洞字香涛)所见极是,坤一早有此意。唯需稳妥接洽,免生枝节。”这里没有“抗旨”的激昂,只有老官僚式的务实——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时,张之洞就与刘坤一通过盛宣怀暗中通气;1900年春义和团起事,两人又在电报里多次提及“东南不可乱”。
真正把共识变成文本的,是上海道台余联沅。6月26日,他与英、美、法、德、日等国领事签订的《东南保护约款》,第一条就写得明白:“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这份约款的草稿,后来被盛宣怀收进《愚斋存稿》,其中夹着张之洞的批注:“妥矣,速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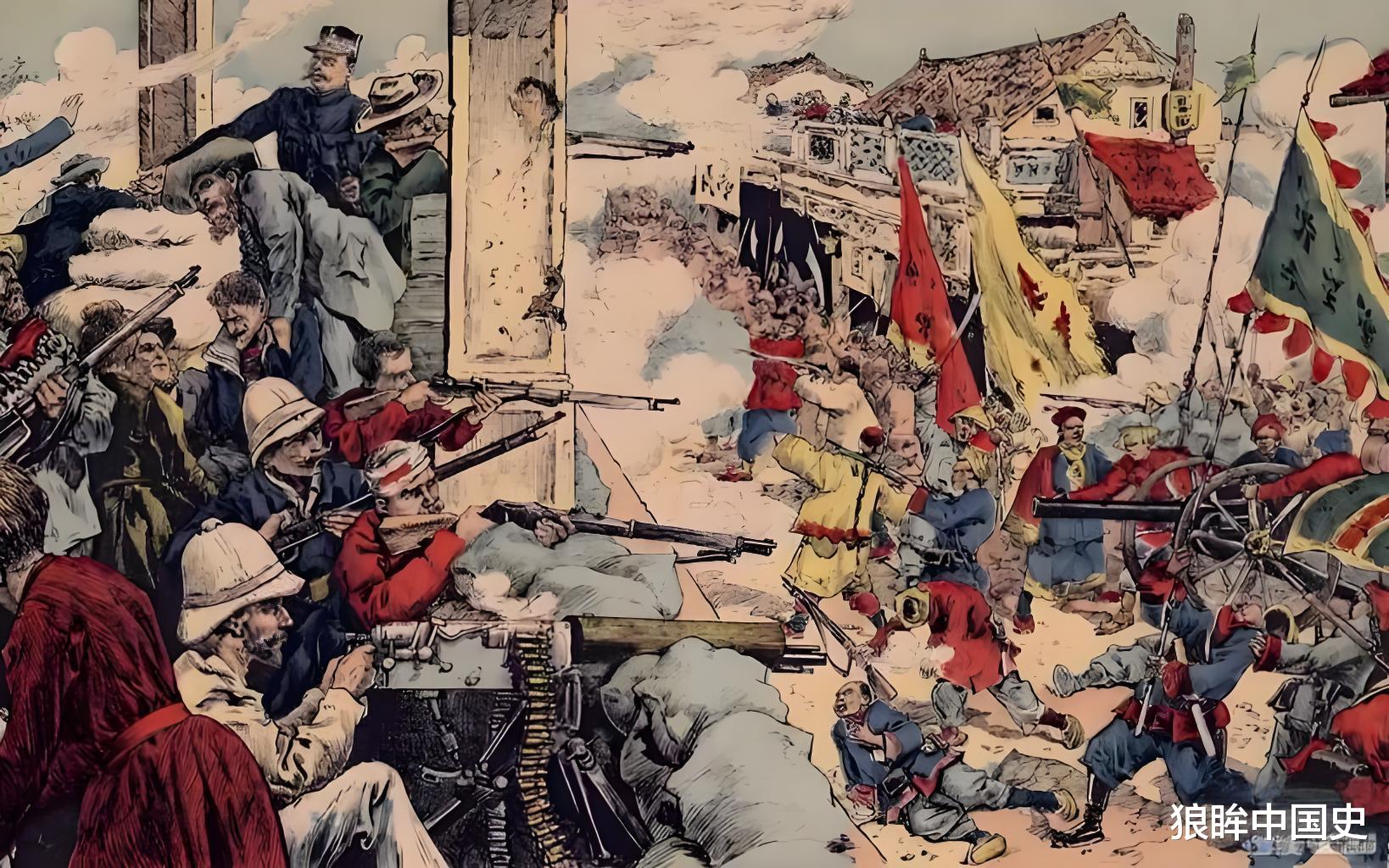
二、朝廷的“沉默”:不是默许,是不敢反对
有意思的是,慈禧的《宣战诏书》传到东南后,并没有后续追责。据《光绪朝东华录》记载,直到7月14日天津陷落,朝廷才发来一道谕令,问“东南各省何以未遵旨力筹战守”——语气更像询问,而非斥责。这种“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态度,藏在当时的财政账本里。
晚清中央财政早已入不敷出。据《清史稿·食货志》统计,1900年全国岁入约8800万两,而军费开支已达1.2亿两;东南五省(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北)的厘金收入就占了全国三分之一,仅江苏一省的漕粮就供应京师十分之一。如果东南督抚真与列强开战,不仅关税、厘金断绝,连南方的粮食都运不到北京。慈禧比谁都清楚:她可以骂义和团“拳匪”,可以杀许景澄、袁昶,但不能拿东南的“钱袋子”冒险。
这种现实的算计,在《申报》的报道里也能找到蛛丝马迹。1900年7月1日,《申报》发表《论东南互保之善后》,直言“朝廷之所以未深究者,盖以东南安则天下安,舍此无以维大局也”。所谓“大局”,从来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忠君”,而是实实在在的钱粮与稳定。
三、地方的“自保”:不是叛逆,是权力的延伸
东南督抚的“互保”,本质是权力边界的一次试探。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就已经让中央不得不承认“督抚有权节制军队”;甲午战争后,张之洞在汉阳建兵工厂、刘坤一在两江练新军,地方军权进一步膨胀。到了1900年,这种膨胀终于碰到制度的天花板——朝廷要他们“宣战”,但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力基础在地方:
其一,财政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创办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每年能为地方带来百万两收入,这些钱他可以自行支配,不用报户部审批;刘坤一的两江总督辖区更是“财赋甲天下”,仅苏州织造局的丝绸出口就能抵得上北方一个省的田赋。
其二,人事权。东南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多由督抚推荐,甚至道员一级的官员任免,督抚也能说上话。比如1900年6月,张之洞未经中央批准,就把湖北按察使调为洋务局总办,理由是“办理互保需得力之人”——朝廷事后并未追究。
其三,舆论权。上海的《申报》《中外日报》都是商人投资,背后站着江浙士绅。当报纸连续发表《论互保乃保民之策》《东南无事幸赖贤督抚》时,督抚的形象已经从“朝廷命官”变成了“地方保护神”。这种舆论的支持,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的自保底气。

四、裂缝的本质:制度的齿轮卡壳了
很多人把东南互保看成“中央与地方的决裂”,但从制度运行的角度看,它更像一次“齿轮卡壳后的临时调整”——当朝廷的政策指令(宣战)与地方的执行能力(保境)无法匹配时,双方只能用“变通”来维持系统的运转。
这种“变通”的背后,是晚清制度的三重错位:
一是决策层的脱节。慈禧为首的军机处制定政策时,依据的还是“康乾盛世”的天下格局——以为只要下一道谕令,地方就会像从前那样服从。但他们忘了,经过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地方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
二是信息传递的扭曲。从北京到武昌的电报要走三天,而上海的洋商消息半天就能传到督抚衙门。当慈禧还在看“义和团刀枪不入”的奏报时,张之洞已经通过盛宣怀拿到了英国领事的照会:“若贵国督抚能保证上海安全,我方绝不派兵北上。”信息的快慢差,让地方总能比中央更早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三是激励机制的失效。清代督抚的考核标准是“政绩”与“忠诚”,但到了晚清,“政绩”越来越依赖地方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而“忠诚”的代价可能是丢官甚至掉脑袋(比如反对义和团的许景澄)。当“保地方”的收益远大于“遵圣旨”的风险时,选择其实早已注定。
五、后来的事:裂缝没有愈合,只是被掩盖了
东南互保之后,朝廷给了督抚一点“甜头”:张之洞加太子太保衔,刘坤一赏加直隶总督衔(虽未到任,但荣誉足够)。但这种“事后补偿”并没有修复权力裂缝——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东南督抚联名上书“新政十条”,要求改革财政、练兵、兴学,其实就是想把互保时的“自保权”固定下来。
1909年,袁世凯罢官时,张之洞曾对人说:“北洋倒了,东南还能撑着;可要是东南也倒了,这大清就该散架了。”这句话里的清醒,恰恰来自1900年的那场交易:当地方督抚意识到自己能影响朝廷的决策时,中央的权威就已经不是“天威难测”,而是“可以商量”的了。

历史从不是非黑即白:
回头看东南互保,没有“忠臣”与“逆贼”的标签,只有一群在制度缝隙里寻找生存空间的参与者:慈禧要保皇位,就得忍东南的“不听话”;督抚要保权力,就得跟朝廷玩“默契游戏”。那些写在档案里的电报、函札,那些印在报纸上的评论,串起来就是一幅晚清权力的真实图景——它不是一个崩溃的王朝的挽歌,而是一个旧制度在时代变迁中挣扎变形的缩影。
就像《清史稿·刘坤一传》里写的:“坤一晚节弥厉,东南底定,其功不可没也。”但“底定”的背后,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有些规矩,早就该改了。
史料来源说明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张之洞档》影印件(收录于《张之洞全集》卷195-196,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上海图书馆藏《刘坤一未刊函札》(《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丛刊》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3.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庚子事变英译外交电》(编号FO 228/1612,转引自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申报》1900年6月26日、7月1日社论(上海图书馆数字资源库);
5.《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
6.《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
7.盛宣怀《愚斋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