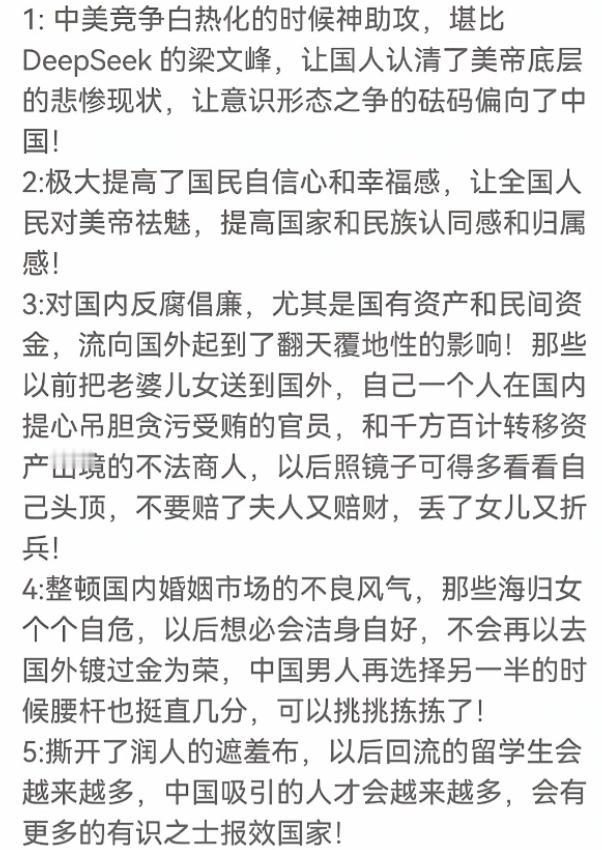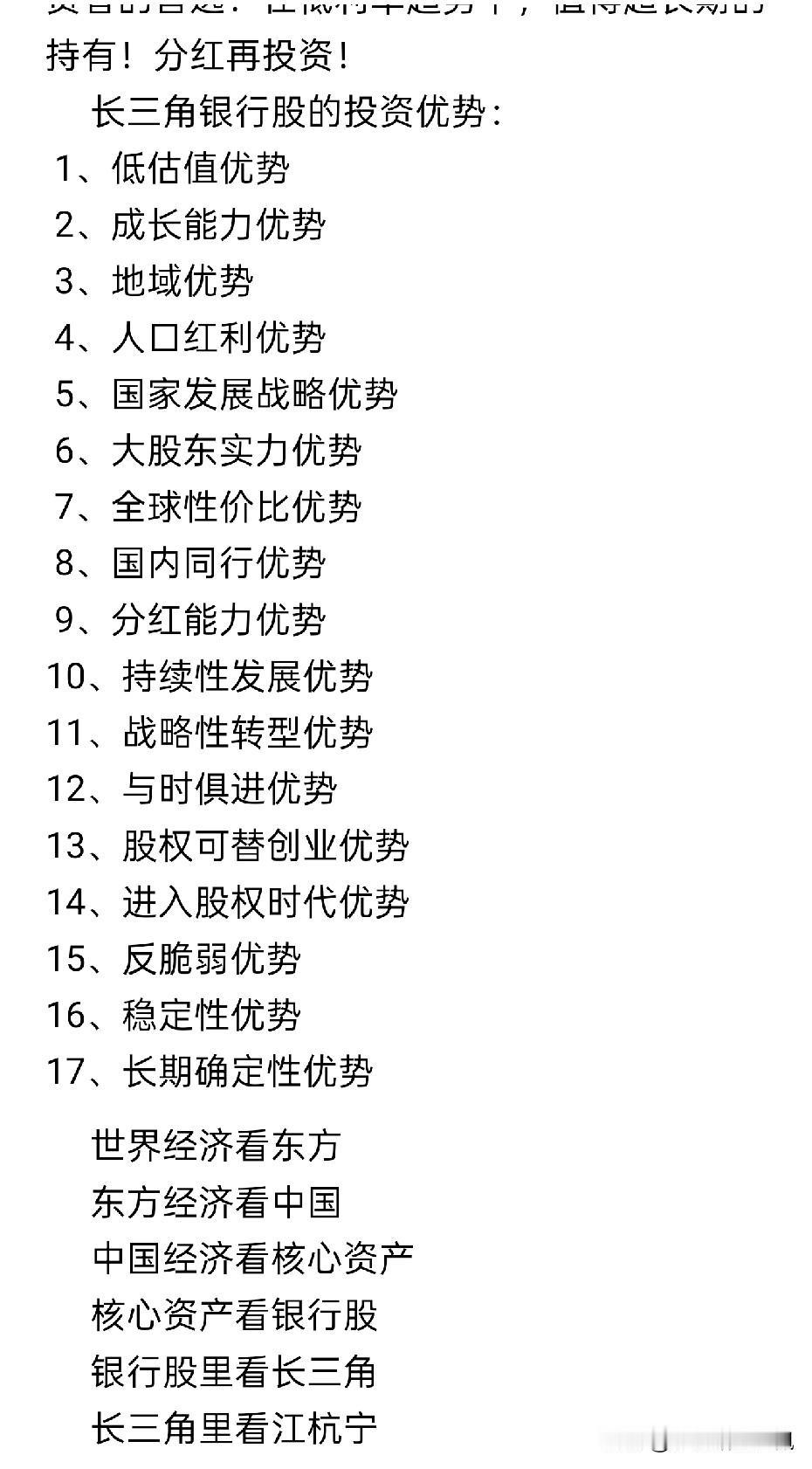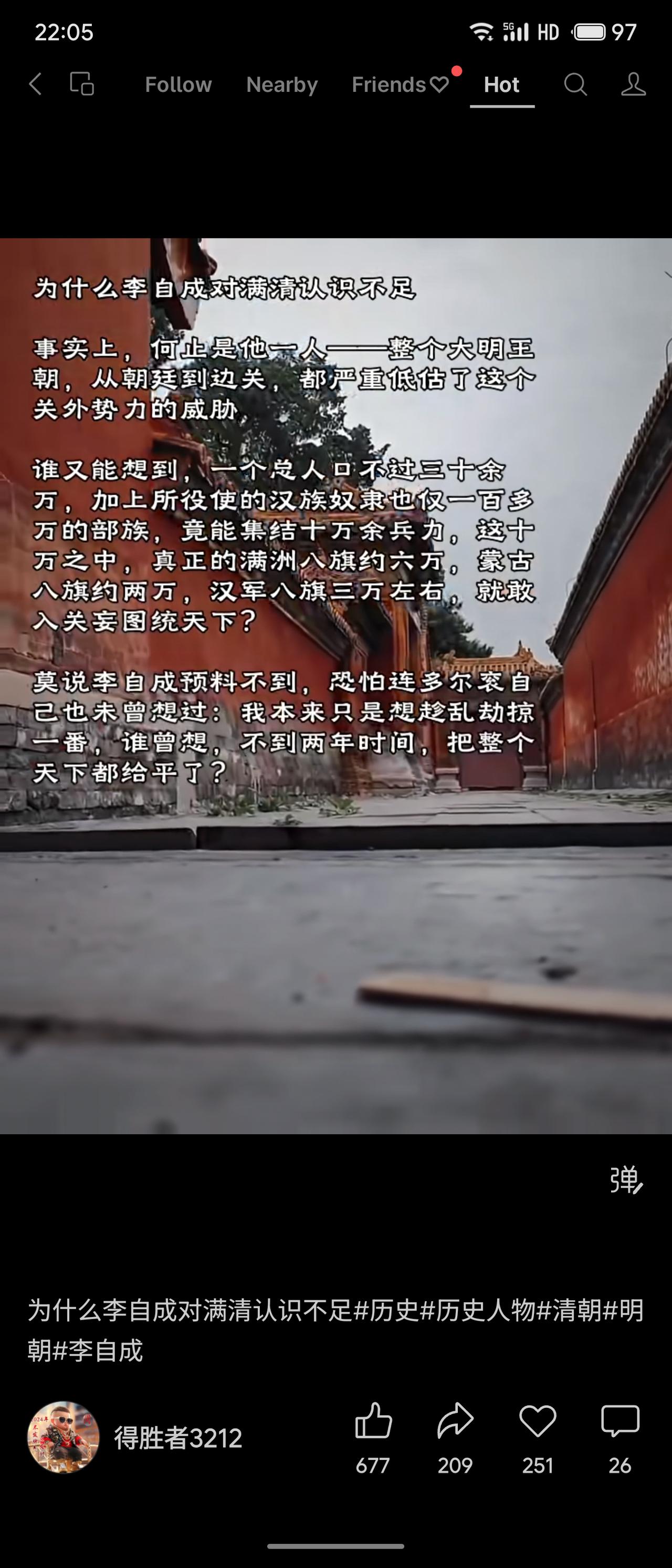有说毛主席晚年不重视生产力发展?理论上说,“抓革命、促生产”,二者是并列的,还是后者本来就是目的?仁者见仁。 很多人一提那段岁月,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停摆”“折腾”这类词,好像全国上下只剩政治口号。 可要是摊开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一年的陵水县,看一眼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就会有种古怪的错位感:社会在摇晃,账本却在往上走,这种拧巴的状态,本身就挺耐人寻味。 一九六七年,局势正乱,陵水干脆先把一个“生产指挥部”搭起来,专门管工农业生产。 那一年,这个小县一下子做了七座桥:陵隆线的隆广桥,米谷线的港坡桥、坡尾桥,文群线的南顶桥、群英桥,再加上海榆东线的六利桥和曲新线的新村桥。 南顶桥和群英桥做成双曲拱,其余五座是永久式石拱桥,不再靠临时木桥凑合。表面上是修路架桥,骨子里是给那个“乱”字压块石头。 同一年,海边也忙得很。县里办起海陵珍珠养殖场,先划出十亩养殖基地,再沿着海南岛海岸慢慢摸索,专门找那种体型大的白蝶珠母贝。野生母贝一批批捕回来,放在养殖区里,培育贝苗,做插核试验。嘴上挂的是“发展养殖事业”,心里明白这是在替集体找一条能挣外汇、能出产值的新路子。 水电方面,动作更早。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梯村工程干渠两公里处弄起一座群英水电站,只有一台十二千瓦机组,年发电量一万千瓦时,看着不起眼,算是给后面的大手笔探了探路。歇了一口气,到了一九七〇年三月,吊罗山脚下的大里水电站投产,单机二十千瓦,年发电量三万千瓦时,给不少村庄的灯和小作坊都续上了电。 水利工程像接力赛一样往前推。 一九七〇年五月上旬,竹利水库合闸蓄水,总库容七百四十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五千亩;紧挨着的田仔水库,库容一千零七十万立方米,灌溉面积七千四百四十二亩。 到了第二年一月,小妹水库大坝启动复工,县革委会专门成立工程指挥部,县委副书记林志光挂帅,这种配置说明,很清楚把水当成了命根子。 水利在地下做文章,粮食要在地面见分晓。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八日,《海南日报》点名报道陵水县良种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技术人员凑一块儿,靠群众路线一点点试验,折腾出来一个花生高产品种,取名“陵一号”。这个品种在全县推广后,亩产飙到六百五十斤,而一九六三年以前,花生亩产才五十到八十斤,硬是多出五百多斤。数字不说话,可一对比,高下立判。 县里对“生产”两个字的态度,在文件里也露了底。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日,陵水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创造“四好”单位、“五好”个人运动的决定》,里面清清楚楚写着:完成生产任务,要算在单位和个人政绩里。 荣誉要拿,产量得先上来。 这样一设计,“抓革命”和“促生产”立刻拴到一根绳上,干部心里明白,光会喊口号拿不到“好”的牌子。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陵水县开了一个不小的四级干部会,代表一千八百七十七人挤满会场。会上学海南区会议精神,要掀生产建设高潮,要把小妹水利工程重新干起来,还给全县画了一张工业蓝图:当年“土法上马”办七个厂、两座矿,小化肥、小化工、小电子、小肥皂,加上光坡、提蒙、本号三个公社农械厂,再把黎安煤矿、新村铁矿开采出来,力争年底前全部投产。 紧接着,又盯上下一年——一九七一年定为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目标开得不客气:粮食作物面积四十五点五万亩,总产一亿四千七百七十八万斤,工业总产值八百万元。 和这些数字一起往前推的,还有那座后来成了“门面”的陵水大桥。 一九七〇年三月,大桥开工。 县革委会专门成立工程指挥部,县委、县革委都盯在上面,当地驻军也拉上来,一边干义务工,一边把自己掌握的混凝土石料无偿搬到工地。大桥的账写得很细:混凝拱结构,全长二百一十一点七米,双车道,桥面宽十米,桥高十米,一共六个拱。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大桥竣工通车,旧木桥和渡口退场,车辆通过数量翻了一倍,这成为陵水河上的第一座永久式大型桥梁。很多年后再回头看,这座桥像一张“投票纸”,替当地干部表了态:哪怕形势起伏,这种实打实的东西,还是要硬着头皮做下来。 工业线上的“小动作”也不少。 一九七〇年四月,陵水县陶器厂照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说法干事,鼓着劲“树雄心、立壮志”,用土办法上马,只花了十八天就砌出一座年产一千吨的水泥窑,水泥达到三百标号。 对外讲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对内讲就是想有自己的一把水泥,今后修桥、建库、盖厂房不必样样求人。 农口这边除了种出来、收上来,还得交得出。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陵水县仅用十七天征购粮食十二点八五万斤,超额完成全年征购任务,得到海南行政区革委会生产组的通报表扬。同月二十二日,《海南日报》又刊出一条消息:黎安公社的干部、社员趁着秋雨突击植树,在沿海沙滩种下了一千二百多亩树。 征购也好,造林也罢,背后都顶着指标,说白了,都是生产任务的一部分。 一个时代是怎么对待生产力的,看标语不算,看桥梁、水库、电站、花生亩产、工农业总产值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