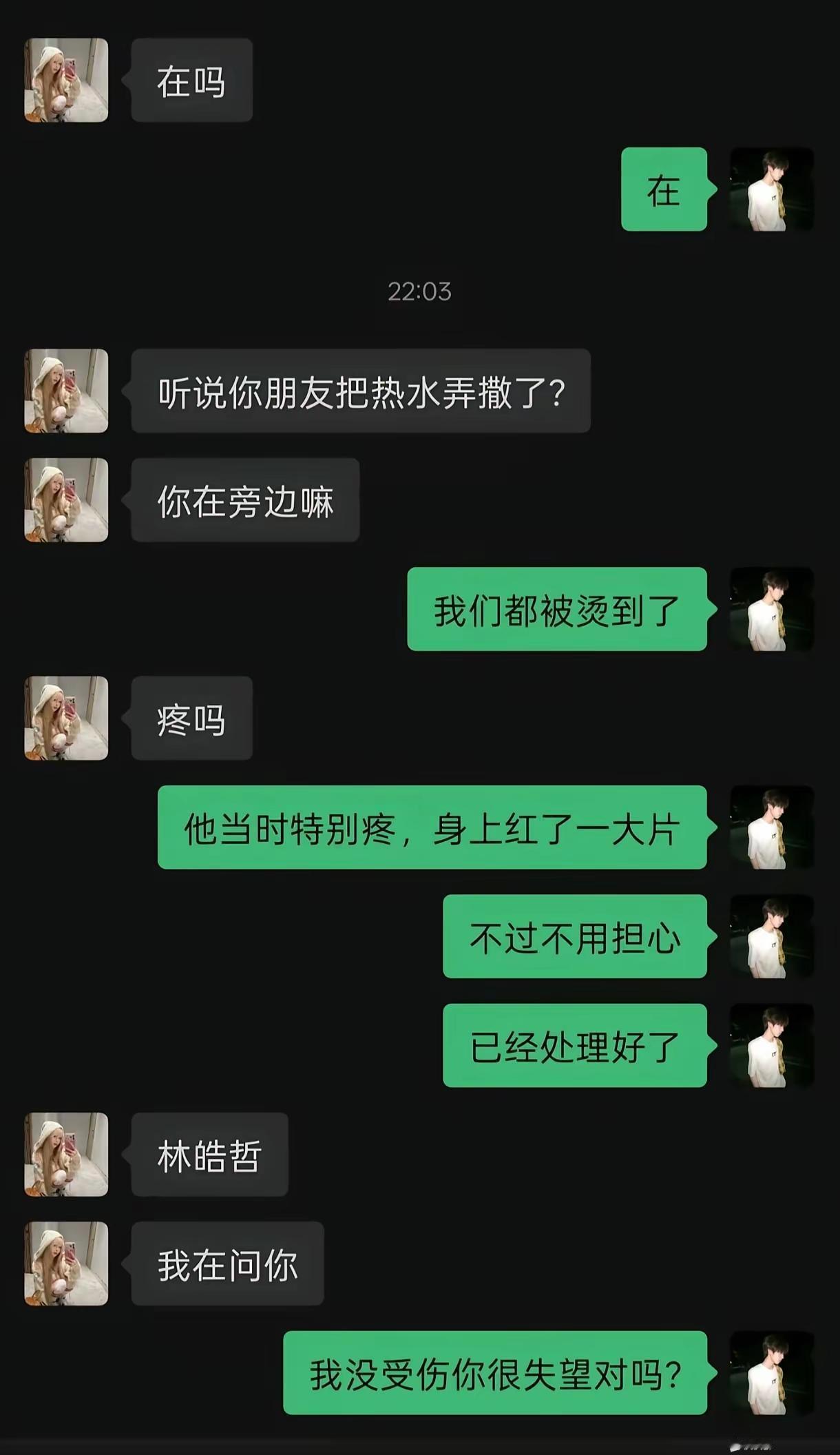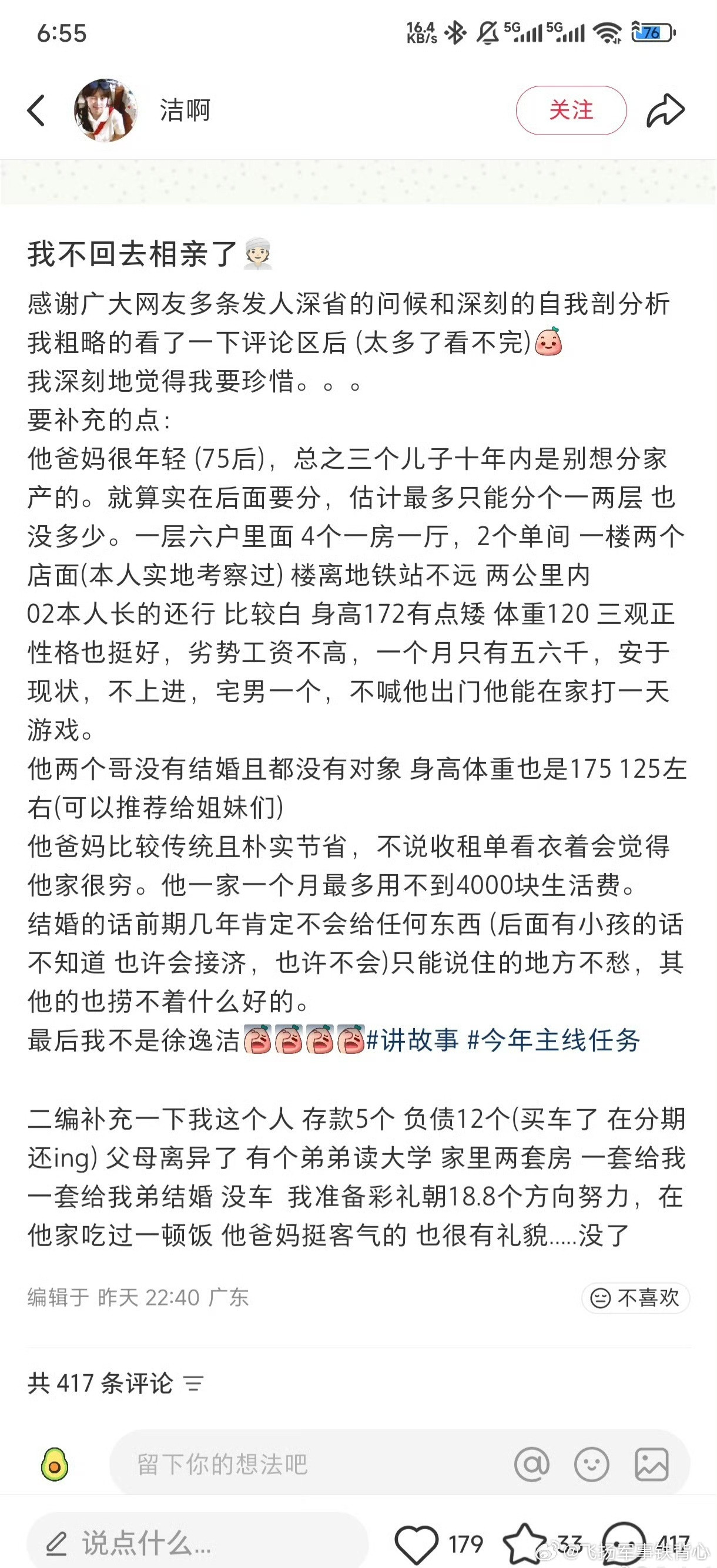父亲的葬礼那天,院子里忽然来了百来个他的老战友。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在灵前三鞠躬后,挨个儿拍了拍我的肩膀,却谁也没留下礼金,就像当年紧急集合哨响时那样,匆匆消失在巷口的晨雾里。 父亲走的那天,天没亮透,院子里的香烛燃得噼啪响,我蹲在灵堂边折纸元宝,手指被粗糙的黄纸磨得发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又说不上来。 他走得突然,我翻遍家里的旧相册,除了一张泛黄的集体照,竟找不出多少他和老战友的联系,那些年他总说“当兵的,聚散都听哨子”,我当是句玩笑。 然后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晨雾裹着一群身影涌进来——不是亲戚,不是同事,是百来个穿着旧军装的老人,肩上的星杠磨得快要看不清,袖口却烫得笔挺。 他们没说话,整齐地在灵前三鞠躬,动作不算标准,膝盖却弯得郑重,领头的老伯伯摘下军帽,露出满头白发,我才认出是照片里站在父亲左边的人。 接着挨个儿走过来拍我的肩,掌心带着老茧,力道不轻不重,像在传递什么信号,有人说“小子,站直了”,有人只点点头,眼里的红血丝比香烛的烟还浓。 我等着他们递信封——乡下办丧事总讲究这个,可直到最后一个人转身,灵前的礼金簿上还是干干净净,他们像约好了似的,脚步轻得像怕踩碎地上的晨露,朝着巷口走去。 怎么会不留礼金呢?我望着空荡荡的巷口,晨雾里还飘着他们身上淡淡的肥皂味,和父亲衣柜里那件旧军装的味道一模一样。 后来母亲从里屋翻出一个铁皮盒,打开时“咔嗒”一声响,里面没有钱,只有一沓泛黄的信,最上面那封写着“紧急集合,勿念”,落款是三十年前的日期,信纸边角有个浅浅的牙印——那是父亲当年咬着笔写的,他总说“战友情,记心里比揣兜里稳当”。 原来不是不重视,是他们那代人习惯了“哨声起就出发,任务完就归队”,连告别都带着点冲锋的利落,礼金太轻,压不住他们心里的分量。 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来,不是为了排场,是想让老伙计最后再看看“队伍”;没留礼金转身就走,是怕眼泪掉在灵前,让他走得不安心。 我摸着那沓信上的牙印,忽然懂了父亲总说的“聚散听哨子”——哨子是命令,也是牵挂,散是为了各自的生活,聚是因为心里那面没褪色的军旗。 那天早上,巷口的晨雾慢慢散了,我站在灵前,第一次觉得父亲没走远,他和他的老战友,只是换了个地方“紧急集合”。 后来每次整理父亲的遗物,摸到那件旧军装的袖口,总会想起他们拍我肩膀的力道,像在说“小子,以后这队伍,你也算半个兵了”。 其实人这一辈子,最该记的不是谁送了多少礼,是有人愿意在你最难的时候,穿着旧军装,带着一身晨雾,为你站成一排——这比什么都重。 香烛还在燃,噼啪声里,我仿佛听见远处传来一声清亮的哨子,和父亲相册里那张集体照上,他们年轻的笑脸重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