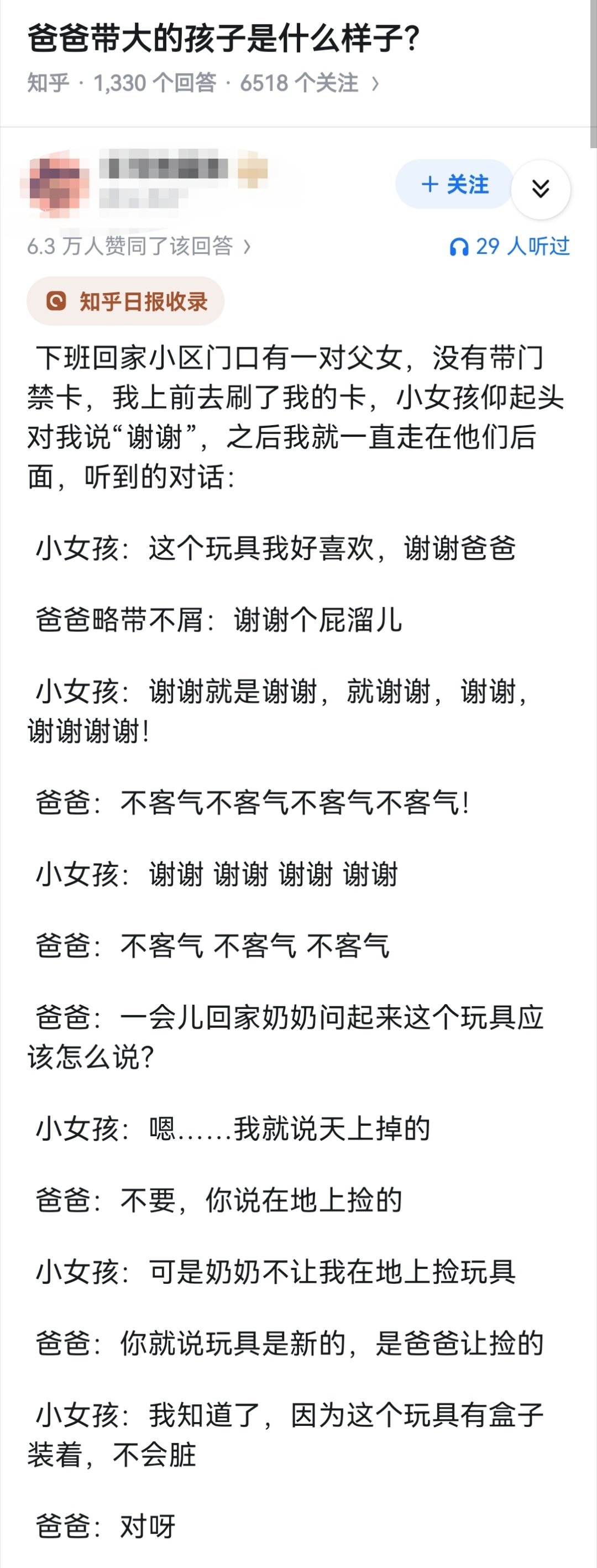我生儿子时,护士教我两次用力,我太疼不会控制呼吸,她就说“不到了”,转头跟别人说不管我,让我自己用力。那天早上八点多,我被推进产房时,宫缩已经变得很密,每三分钟就来一次,疼得我浑身发抖,手紧紧抓着产床的栏杆,指节都捏得发白。 那天早上八点多的产房,空气里飘着消毒水和血腥味,混着我越来越急的喘息。 宫缩像被一只大手攥住肚子,每三分钟就狠狠收紧一次,疼得我浑身发抖,后背抵着产床的硬木板,却找不到一点支撑。 手死死抠着旁边的金属栏杆,指节用力到泛白,像是要把那冰冷的铁条捏出印子来——那是我当时唯一能抓住的东西了。 护士过来时带着一次性手套的手碰了碰我的膝盖,声音有点急:“跟着我呼吸,宫缩来的时候用力,像拉大便一样往下使劲。” 我张着嘴想吸气,可疼得脑子一片空白,吸进的气全堵在喉咙里,根本用不上力;她又教了一次,我还是只会发抖,眼泪混着汗往下掉。 她突然直起身,把手里的产钳往托盘上一放,“哐当”一声——“不到了”,她转头跟旁边的助产士说,“让她自己用力吧,教不会。” 我当时懵了,是我太没用了吗?后来想,或许她那天接了好几个产妇,已经很累了?又或者产房里太吵,她没看到我攥栏杆的手在抖,没听到我牙齿打颤的声音? 事实是我疼得失去呼吸控制,推断是她觉得我不配合,影响是我更害怕了:肚子里的孩子还在动,可我连怎么用力都不会,栏杆被我抓得更紧了,好像一松手就会沉进无底的水里。 最后是怎么生下来的?忘了,只记得孩子哭出声的那一刻,我抓栏杆的手突然一松,整个人软了下去。 现在偶尔看到产房的新闻,还是会想起那天的消毒水味,想起那个泛白的指节——原来女人生孩子,不止是身体在受苦,心里的慌才更磨人。 要是能重来一次,我会提前把呼吸法练熟,不是为了“不被嫌弃”,是为了疼的时候,能少一点“抓不住”的恐惧;而那些在产房里的声音,能不能慢一点、软一点?毕竟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的。 后来给孩子换尿布,看到他攥紧的小拳头,突然想起那天我抓栏杆的手——原来生命最初的相遇,都带着点狼狈的勇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