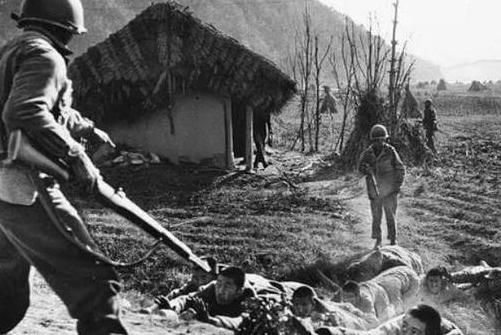1973年深秋的北京,中南海收发室收到一封来自广西的挂号信。 信封上“毛主席亲启”的字样让工作人员皱起眉头,展开信纸看到“广西女儿岑云端”的落款时,有人当即判断这又是一起冒充熟人的诈骗。 这个让领袖惦记十六年的名字,背后藏着一段红土地与中南海的特殊情缘。 1939年岑云端出生在广西贺县八步镇的壮族农家,土改时分到三亩水田的父母坚持送女儿读新式学堂。 每到瑶族“达努节”,寨老敲响铜鼓时,这个梳着翘辫的小姑娘总能最先踩着鼓点跳出《铜鼓舞》的祭祀步伐,乡亲们说她是“铜鼓里蹦出来的山雀”。 在东北军区护士训练班的日子里,岑云端白天学包扎护理,晚上在煤油灯下编舞。 1954年沈阳军区文艺汇演,她把朝鲜族《农乐舞》的鹤步融入壮族《蚂拐舞》,创作出反映战地卫生员生活的《雪夜送药》,一举拿下二等奖。 两年后选拔空政文工团成员时,首长看着档案里“能歌善舞,贫农成分”的评语,又翻到她在野战医院荣立三等功的记录,当即把这个广西姑娘的名字圈了出来。 第一次走进中南海春藕斋时,岑云端紧张得攥皱了演出服。 当毛主席问起她的名字时,她小声回答“岑荣端”。 ”这个即兴的改名,成了她艺术生命的新起点。 1966年夏天,岑云端主动申请调往新疆春蕾文工团。 在乌鲁木齐的六年里,她把哈萨克族的《黑走马》与壮族《师公舞》融合,创作出《天山放歌》。 1972年转业回广西艺术学院时,行李箱里装着三十多本舞蹈笔记,其中1965年在百色采风时记录的《瑶族铜鼓舞教学纲要》,后来成了民族舞蹈系的教材范本。 1974年那次中南海会面,毛主席已经81岁高龄。 多年后人们才明白,这三个字既是对明代瑶族起义历史的铭记,也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期许。 2004年,这三个字被镌刻在迎巽山的悬崖上,与357亿元建成的大藤峡水利枢纽遥相呼应。 回到南宁后,岑云端把更多精力放在教学上。 她带着学生在百色地区采风,用录音机记录即将失传的《铜鼓舞》鼓点。 1986年,她编排的《黔江魂》在全国舞蹈大赛获奖,演员全是大藤峡工地的农民工。 那些年她每月都会匿名给自卫反击战烈士家庭汇款,汇款单附言永远是“一个广西女儿的心意”。 直到2010年广西艺术学院成立“云端舞蹈工作室”,人们才从她捐赠的教案里发现那些泛黄的汇款存根。 扉页上“文艺为工农兵”的批注,与玻璃柜里37次修改的《蚂拐舞》教案,构成了一位艺术家最朴素的人生注脚。 ” 如今黔江两岸的壮族乡亲仍会说起,每年铜鼓节敲响第一声鼓点时,仿佛能看见一位白发老人在云端起舞。 那舞姿里,有红土地的坚韧,有中南海的温情,更有一个民族对文化根脉最执着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