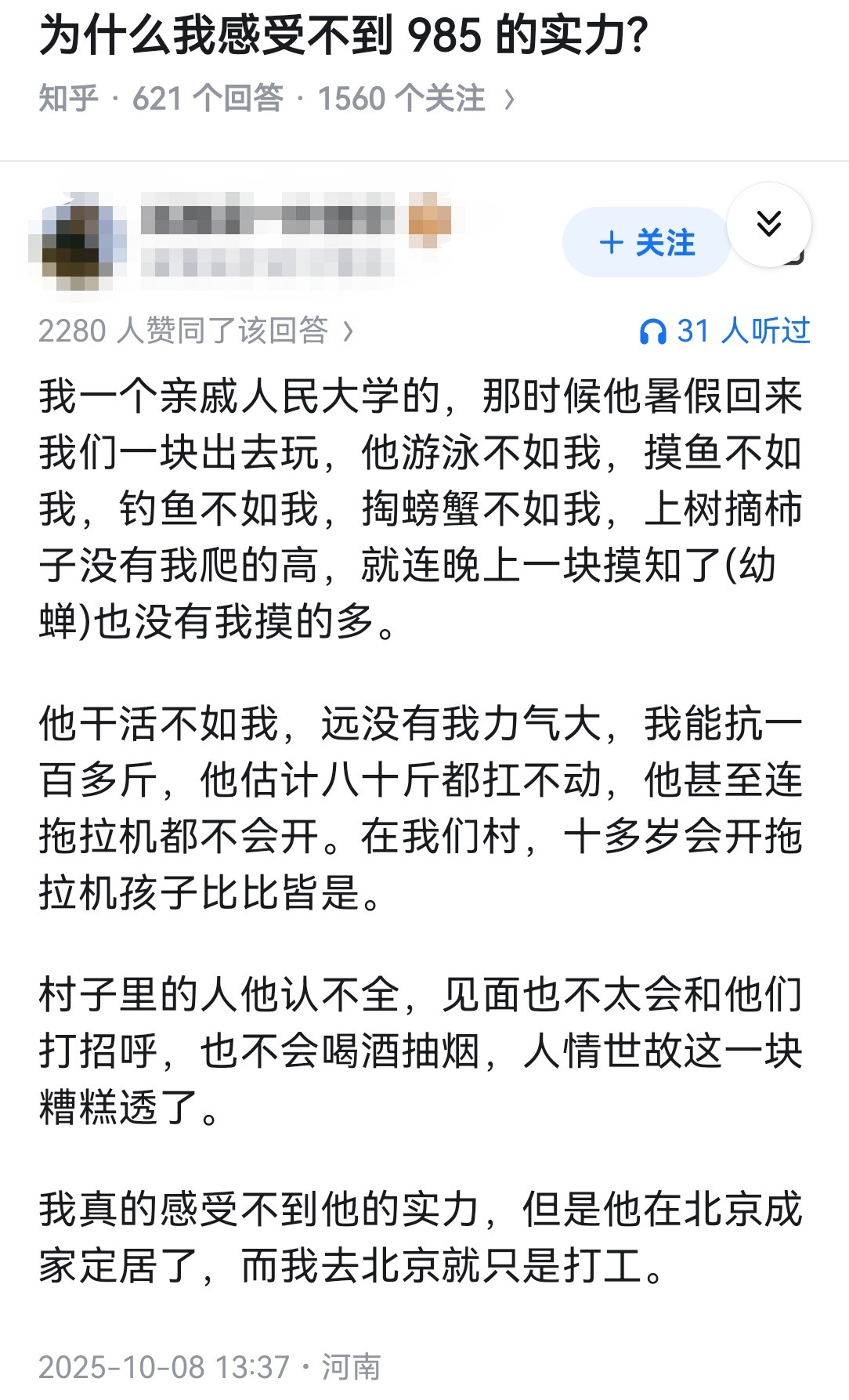1997年,邓亚萍退役后去清华大学读书,第一堂课,老师问她:“你的英语如何?”邓亚萍尴尬的回答:“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97年的秋天,北京城里的银杏树叶刚开始泛黄,邓亚萍背着书包走进了清华大学的教室。 这位刚刚退役的乒乓球世界冠军,此刻坐在一群比自己小七八岁的同学中间,显得格外特别。 英语老师看着花名册上这个熟悉的名字,抬头打量着眼前这位个子不高的女生,随口问道:"你的英语水平怎么样?" 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邓亚萍身上。 她平静地回答:"老师,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 这句话让在场的同学都愣住了,谁也想不到,这位在国际赛场上叱咤风云的世界冠军,在英语学习上竟是从零开始。 那时的邓亚萍刚结束辉煌的运动生涯。 她手握4枚奥运金牌,18个世界冠军头衔,曾经连续8年保持世界第一的排名。 但这些耀眼的成绩在她选择进入清华学习时,都成了过去式。 更重要的是,她刚刚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这个新身份让她意识到,如果不能突破语言关,将来如何在国际体育舞台上为中国发声? 从那天起,邓亚萍开始了艰苦的英语学习之路。 她特意把课本拆成单页,每天带着几页纸和单词卡片,利用一切碎片时间学习。 清晨天还没亮,她就已经在操场边背诵单词。 食堂排队打饭时,她手里总捏着写满英文短语的小纸条。 晚上宿舍熄灯后,她还要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复习当天的内容。 同寝室的同学常说:"亚萍的复读机总是吱吱作响,一个月就能用坏两盒磁带。" 这样高强度的学习让她的身体出现了预警信号。 原本在运动队练就的好视力,从1.5骤降到0.6,体重也跟着往下掉,比打球时还轻了十来斤。 教练见到她蜡黄的脸色,忍不住心疼地劝她别太拼命。 但她心里明白,学习英语这场战役,比当年在球场上对付外国选手还要艰难。 毕竟打球时还有队友加油鼓劲,而现在只能独自面对厚厚的词典和读不懂的课文。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998年,邓亚萍争取到去剑桥大学交换学习的机会。 初到英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她首先遭遇的是生活上的种种不便。 记得第一天上课,她骑着二手自行车在剑桥小镇上迷了路,冒着大雨转了近一个小时,赶到教室时早已浑身湿透。 在邮局寄信时,因为看不懂英文表格,她捏着信封在原地站了半小时,最后只能红着眼睛离开。 为了节省开支,她在郊区租了间便宜的房子,每天要坐很久的公交车到学校。 午饭常常就是一个冷三明治,但她从不抱怨。 课堂上,她把老师的板书一字不落地抄下来,晚上回到住处再逐个单词查阅词典。 房东老太太时常摇着头说:"冠军小姐,你何必这么辛苦呢?" 她总是笑着回答:"正因为是冠军,所以更输不起啊。" 2001年,邓亚萍选择进入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这所大学以其高质量的外语教学闻名,导师在面试时直言不讳地表示怀疑:"一个运动员能做好学术研究吗?" 邓亚萍不卑不亢地回答:"别人用一年完成学业,我愿意花两年时间,但保证每篇论文都认真对待。" 她的硕士论文选题是《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 为了这个课题,她跑遍了各大图书馆,甚至找到了上世纪60年代女乒运动员的日记手稿。 3.5万字的英文论文在答辩时获得了考官们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项研究填补了中国女性体育史的空白。 得知这个消息,萨马兰奇先生特意来信祝贺,称她"真正掌握了与国际社会对话的钥匙"。 2003年,邓亚萍又向更高的学术目标发起挑战,开始攻读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奥运经济。 此时她还兼任北京奥组委的工作,不得不频繁往返于中英两国。 最忙碌的时候,她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 申请博士时还有个插曲:萨马兰奇先生起初不愿写推荐信,认为她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实际工作上。 邓亚萍连夜飞往瑞士,向这位体坛前辈解释:"研究奥运经济,正是为中国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铺路。" 最终她的诚意打动了萨马兰奇,也得到了剑桥大学的录取通知。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邓亚萍站在国际奥委会的讲台上,用流利的英语向与会代表阐述她的奥运经济模型。 一位欧洲委员惊讶地说:"难以置信,你就是当年那个连字母表都认不全的中国姑娘?" 她微笑颔首,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一刻,距离她在清华课堂上坦诚自己英语水平的那天,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一年。 这十一年间,邓亚萍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永不言弃"。 从运动员到学者,从世界冠军到国际体育事务的参与者,她完成的不只是身份的转变,更是一次次对自我的超越。 当有人质疑"运动员学什么外语"时,她用实际行动证明:学习没有界限,只要肯付出,任何人都能在新领域开辟天地。 主要信源:(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