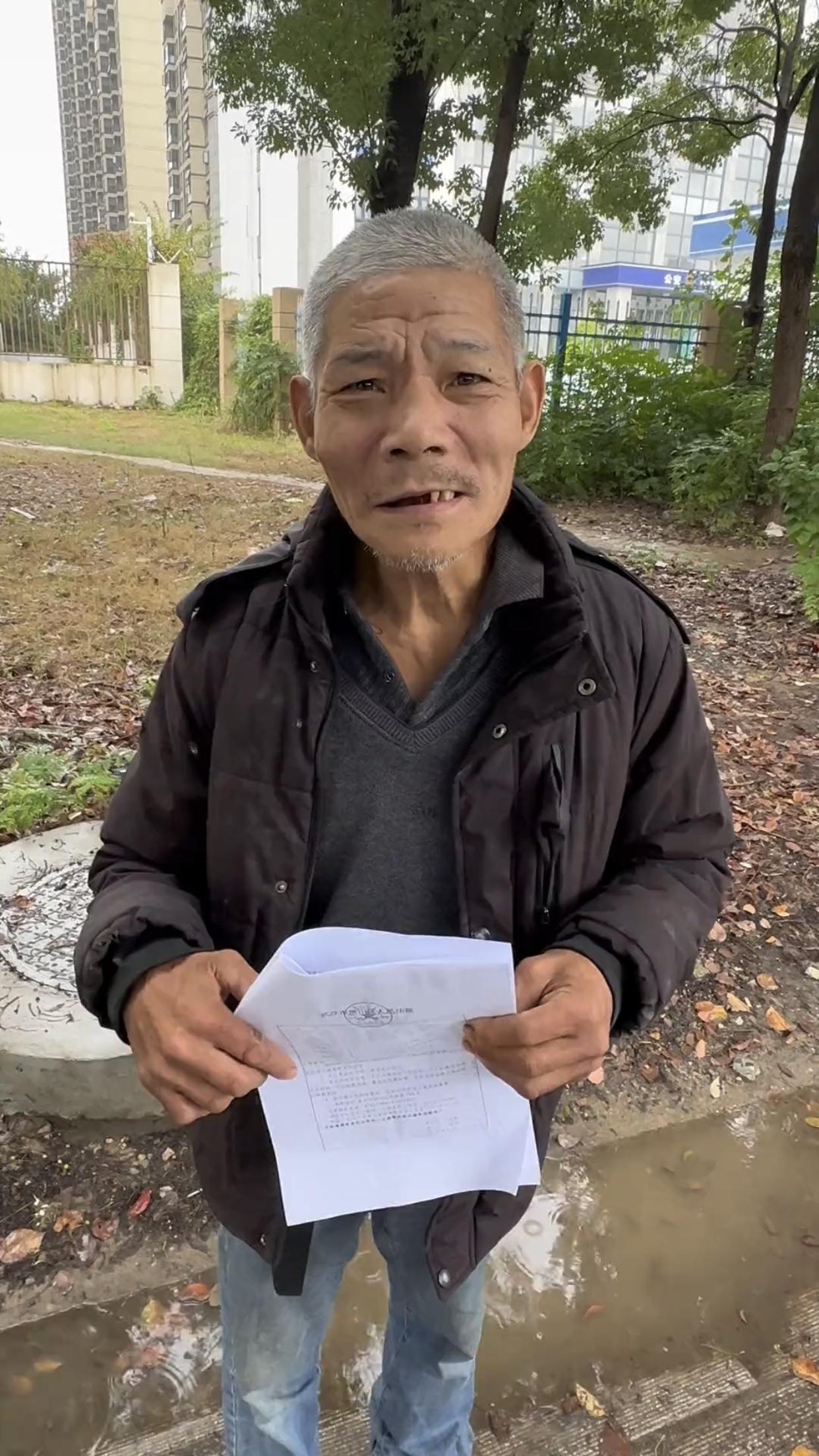1985年,杨振宁把母亲罗孟华从合肥接到了香港。老人家得了多发性骨髓瘤,这病会让骨头像被虫蛀了一样,稍微动一下就钻心地疼。内地当时治疗条件有限,他决定带母亲去香港养和医院看病。 1986 年香港养和医院病房,杨振宁握住母亲罗孟华的手。 床头摊着南开理论物理研究所筹建方案,钢笔还搁在页边。 “振宁,又在忙国家的事?” 老人声音轻得像羽毛。 他把方案折好塞进口袋:“妈,等您好点就去南开看看。” 护士进来换止痛针,账单上的数字又添了一笔。 这支针剂抵内地工人半年工资,他签字时没皱眉。 妹妹杨振玉走进来:“美国那边催您去开交流基金会的会。” 他摇头:“基金会的事能等,妈疼得睡不着可等不得。” 1971 年中美关系初解冻,杨振宁是首个回国的华裔学者。 见到邓稼先,得知原子弹是自力更生造的,他当场落泪。 返美后他在 30 多所大学演讲,掀起华裔学者访华潮。 母亲那时写信说:“你架起了桥,比拿诺奖更让我骄傲。” 1980 年他在纽约创立对华教育交流委员会。 十年间资助近百位中国学者赴美进修,全是个人募集资金。 母亲翻着受助学者名单:“这些孩子,多像你年轻时的模样。” 他想起留美时母亲卖首饰凑学费,眼眶一热。 1986 年深秋,母亲病情稍稳,他推着轮椅去医院花园。 轮椅上放着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的筹建信。 “你爸留美五年,每月寄钱回家从不断。” 母亲轻声说。 他望着远处海面:“我现在做的,和爸当年是一回事。” 深夜病房,他趴在床边改研究所章程,手里攥着病历。 母亲醒来看见,伸手摸他头发:“别熬坏了,国家还要靠你。” 他直起身帮母亲掖被角:“您教我的,做事要对得起良心。” 窗外月光洒进来,照在 “人才引进计划” 那页纸上。 1982 年他致函中央,为科研事业提战略性建议。 信里字迹工整,和现在记医疗账的笔迹一模一样。 母亲那时来美国看他,翻到信稿:“这字,随你爸的认真。” 他记得父亲教他记账:“每一笔都要明明白白,对人对事都一样。” 有次记者采访,撞见他给母亲削苹果,案头摆着基金报表。 “您怎么平衡孝心和国家事务?” 记者问。 他把苹果递到母亲嘴边:“妈教我爱国,爱国先学孝顺。”母亲笑着补充:“他从小就知道,家和国是连在一起的。” 1987 年母亲能坐起来了,他把清华寄来的聘书给她看。 “以后要回清华教书,培养咱们自己的物理人才。” 老人摸着聘书封面:“好,回来好,根就在这儿。” 那天他给母亲唱清华校歌,跑调的样子逗笑了病房里的人。 1979 年他在华盛顿主持欢迎邓小平的宴会。 致词时强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全场掌声雷动。 事后给母亲打电话,她只说:“振宁,说的都是该说的。” 这份沉稳,是母亲在父亲失联时教给他的担当。 香港的雨夜,他陪母亲聊起 1971 年第一次回国。 “看到北京街头的红旗,我就知道回来对了。” 母亲点头:“国家好了,咱们家才真的好。” 他把这话记在笔记本上,后来写进给学生的寄语里。 1989 年他任亚太物理学会首任主席,设立 “杨振宁奖”。 颁奖那天给母亲打电话,她在电话里笑:“奖励年轻人,好。 ” 那时母亲已能出院,在公寓里种他买的紫藤花。 花盆边,摆着他获诺奖时母亲缝的丝绸垫布。 有人问他捐工资帮清华引进人才值不值,他指了指母亲。 “我发烧时,她用湿毛巾敷我额头,算过值不值吗?” 母亲在一旁补充:“国家需要,就该去做,别算账本。” 这话传开后,比任何科研成就都让人动容。 1997 年清华高等研究院成立,他任名誉主任。 每次去苏州祭拜父母,都带着研究院的成果报告。 墓碑前摆上紫藤花,他轻声说:“妈,您看,人才都来了。” 风吹过墓碑,像母亲当年温柔的回应。 现在的杨振宁,虽年事已高仍关心清华科研发展。 办公室里,母亲的照片和受助学者的感谢信挂在一起。 他常对学生说:“爱国不是空话,要做具体的事。” 那些照料母亲的日夜,那些为国奔波的岁月,都成了最珍贵的人生注脚。 他捐出的工资培养出大批顶尖人才,设立的基金仍在资助学者。 母亲种过的紫藤花,如今在清华园开得正盛。 这棵藤,连着他的孝心,也连着他对家国的深情。 就像他说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从来都分不开。 信源:中央电视台《杨振宁专访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