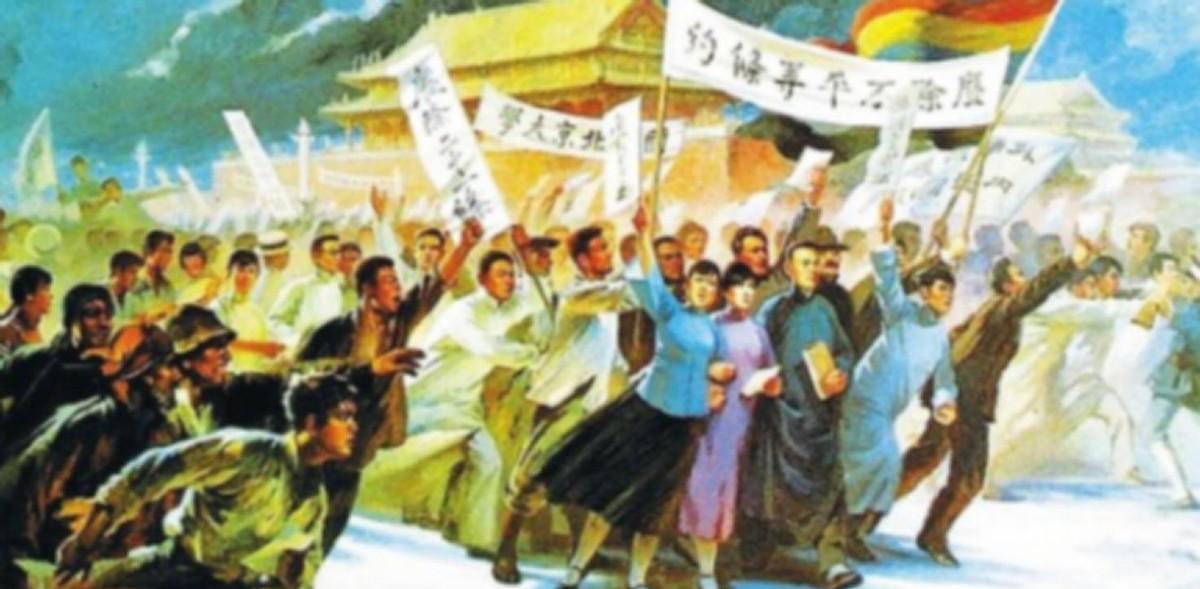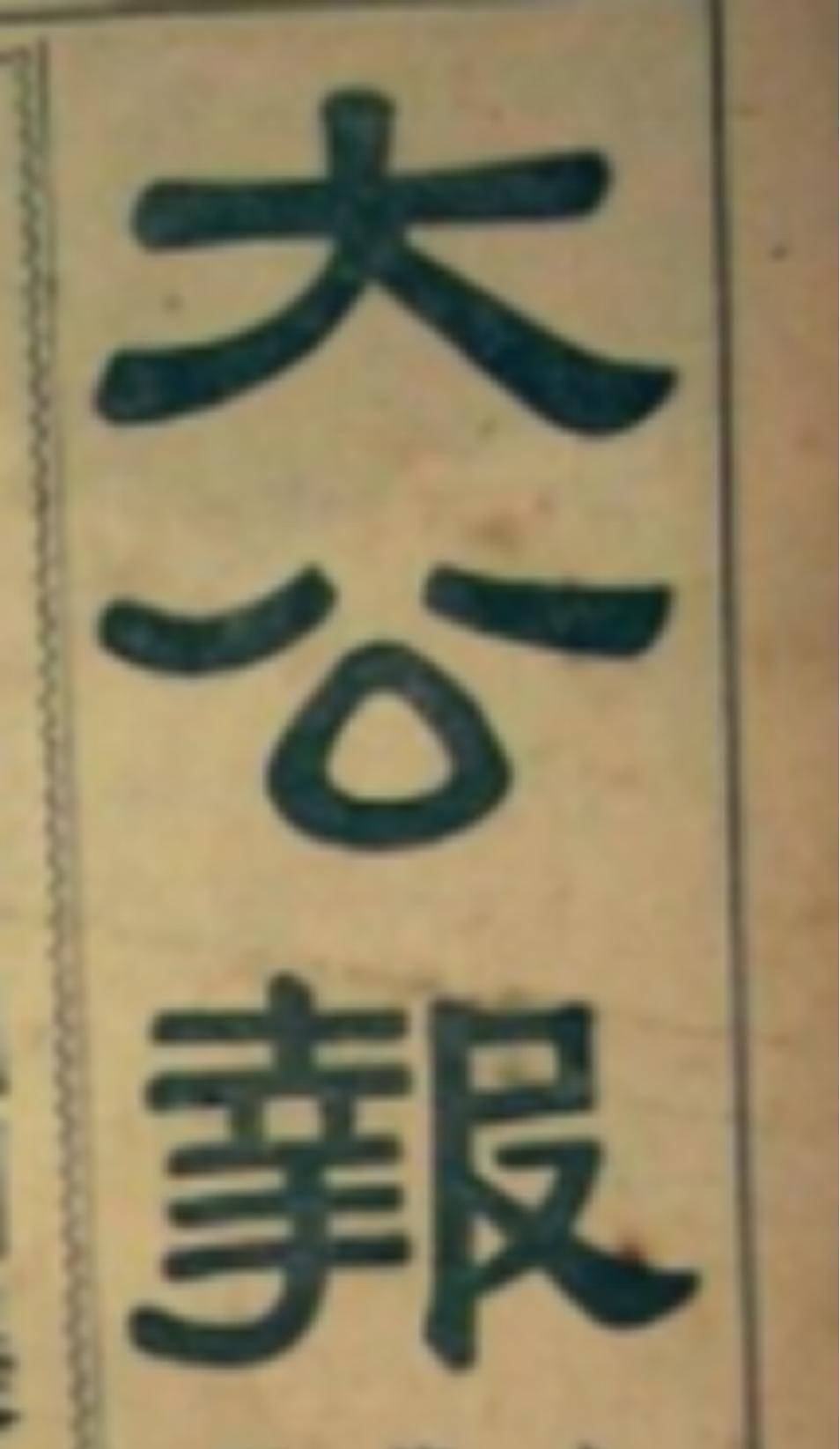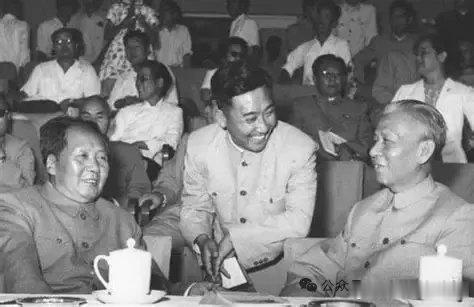1925年刘少奇于长沙被捕,营救会议上何叔衡:这件事还得要你出马 “1925年12月16日傍晚,我看见院子里那几张生面孔,心里咯噔一下。”易礼容把门栓插好,压着嗓子对楼上的刘少奇说。长沙文化书社外,冷风直灌,几名荷枪便衣正佯装翻书,其实目光紧盯后楼。五分钟后,木板楼梯一阵猛响,特务破门而入,刘少奇被五花大绑押往戒严司令部。消息飞速传遍湘区党组织,随即在夜色中点燃了营救行动的导火索。 当晚,李维汉在坡子街一间小阁楼召集紧急会议。昏暗灯芯里,几个人轮番发言,气氛绷得像琴弦。何叔衡一直没开口,他在纸上写写划划,忽然抬头盯住角落那个身影:“这事还得要你出马。”灯光下,何宝珍的脸微微发白,又瞬间定住,“我明白,先说目标。”一句干脆的回答,为营救定下了基调。 为何让一个女同志挑头?原因说来并不复杂。欧鸣高——湖南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前三女师校长,既与省议会交好,又曾公开斥责赵恒惕,如能出面,湖南省主席即使恼火也不敢轻举妄动。何宝珍是欧鸣高的得意门生,这层关系成了撬动顽石的支点。会议结束已近子夜,寒风带着湘江水汽直往窗缝钻,众人匆匆散去,各自奔向既定岗位。 第二天拂晓,何宝珍与易礼容步行数里,敲开了盐仓街欧宅的朱漆大门。听完来意,欧鸣高重重拍桌:“赵恒惕胆大包天。”他苦笑一声,“我已辞官,他未必见我,但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得听一句。”于是,师生三人直奔议会。午后的议事厅内,欧阳振声把玩手中折扇,听罢先是沉默,随即点头:“走,我陪你们去省公署。” 与此同时,另一条战线也在酝酿。长沙《大公报》主编冒着停刊危险,决定翌日公开刊发《刘少奇被捕记》。排字房的油灯连夜不灭,铅字哐啷落槽。17日清晨,报纸摆上街头,消息像投石进湖,迅速激起全国工会的连锁反应;北京、上海、武汉的电报雪片般飞往长沙,最密集时赵恒惕一天竟收到四十多封。舆论风暴逼得这位军阀省主席坐卧不宁。 镜头先暂时拉回几个月前。5月,刘少奇、何宝珍夫妇以全国总工会干事身份在上海领导五卅工人罢工,正值斗争最激烈之际,刘少奇积劳成疾,经组织批准回乡休养。长沙文化书社因此成为临时栖身之所。其实赵恒惕对这家小小书社早有“黑名单”,只是苦无借口动手。如今刘少奇亲临,其反革命算盘立即拍板——抓捕后迅速处置,噤声封口。 然而逼仄的公署走廊里,局势超出了他的掌控。欧阳振声冷着脸交涉,何宝珍言辞犀利,逐一拆解“煽动工潮”“危害治安”等指控。赵恒惕自知理亏,又怕再添把火,只得含糊其辞:“查明身份后自会处理。”场面僵持两小时,终以“继续审讯”拖延收场。但外面浪潮已起,他的拖字诀很快破功。 1926年1月26日,省公署门前挤满探究的市民。午后两点,戒严司令部卫兵无奈打开铁门,刘少奇步出牢房,面色略显憔悴,却神情坚定。站在门口的何宝珍没有多话,只递上一件棉衣。一旁记者低声问她感想,她摇头:“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夫妻俩当天即离开长沙,前往宁乡乡下暂避。对外,赵恒惕以“证据不足”解释释放,实则被全国声援迫得骑虎难下。 短暂的胜利背后,暗流仍在滑行。七年后,上海,何宝珍已经改名王芬芳,身份是小学教师,真实职责则是全国互济会营救部部长。1933年春,一个清晨,陌生脚步在弄堂回响,十几名便衣堵死了唯一出口。她迅速将小儿子托付给隔壁大嫂:“几天便有人来接。”话音未落,铁链声逼近,她抬头挺胸迎向门口。之后的漫长牢狱岁月里,她用一双空手组织秘密通信,拉拢女看守,传递情报。对外界而言,她消失了;对狱中同志而言,她是那条隐形的生命线。 命运转折发生在1934年秋。互济会一位女联络员被捕并供出“王芬芳”真实身份。南京模范监狱里,敌人的拷打刀具齐上阵,何宝珍只是反问:“你们真的怕一个弱女子?”酷刑之下,她依旧只报一句“姓名王芬芳,职业教师”。同监难友回忆,当晚她靠着湿冷的墙壁悄声念一段《国际歌》,哑到几乎听不见。 1935年春,雨花台-那块被血染红过无数次的土地——迎来又一次枪声。押赴刑场途中,一个宪兵低声嘀咕:“早说就不用走这条路。”何宝珍笑得平静,“路在脚下,不在你嘴里。”两枪过后,年仅三十三岁的她倒在初春的泥土中。衣袋里唯一的遗物是一张早已模糊的合影,照片上,刘少奇抱着幼子,背景是安源矿区灰黑的天。 多年后,幸存者回忆此次营救,常提到一个细节:会场昏灯下,何伯衡那句“这事还得要你出马”本是一种判断,更是一种信任。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信任往往和生命捆在一起,一旦扣动,便再也收不回。有人活着走出牢门,有人永远留在了雨花台。每一道选择,都在悄悄写下新中国未来的注脚,而他们从不自诩英雄,只称自己为“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