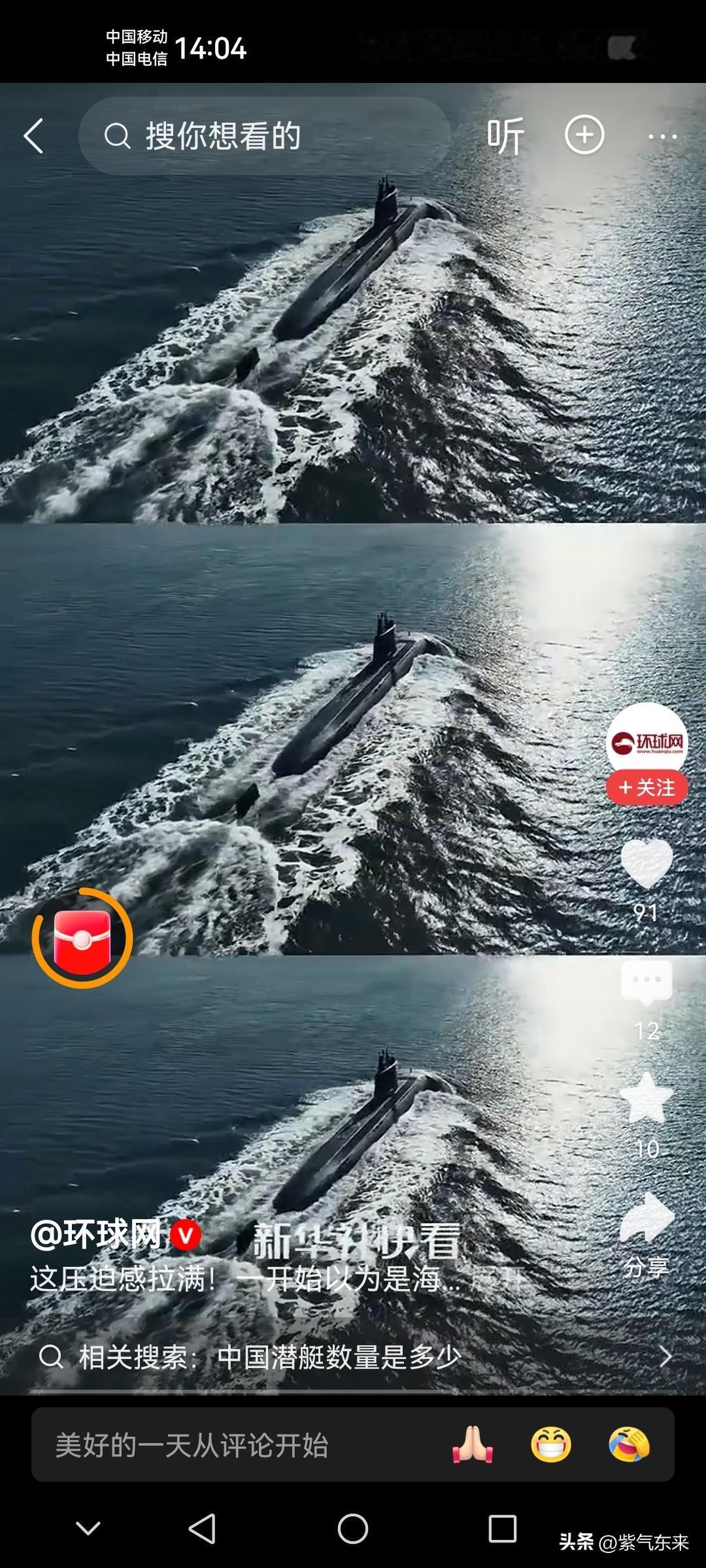标签: 黄旭华
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
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探视自己的母亲,95岁高龄的老母亲,望着自己的儿子,说不出一句话来。1958年春,那时候黄旭华32岁正干得起劲,突然就被调到北京去搞一个"绝密项目",他跟家里说了声"单位派差",转身就走了,但谁也没料到,这一走就是大半辈子。当时,西方那边把技术捂得死死的,苏联虽说曾经帮过忙,但涉及核心机密时也翻脸不认人,黄旭华手里就三样东西:没图纸、没设备、没外援,就这条件,还得造出核潜艇。葫芦岛那个基地,冬天冷得像冰窖,他们住的泥房子连暖气都没有,吃的是土豆白菜轮流转,但这些都不算啥,最头疼的是没计算机。想验证一个数据,全靠算盘一下下拨。有个细节特别荒诞——他们为了称重,居然用家用体重秤去称潜艇零件,这要是让外国同行知道了,估计笑掉大牙。更绝的是,有次一个爱国华侨冒着风险从海外带回来一个玩具模型。就这么个小玩意儿,成了他们验证设计思路的唯一参照物。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角落里,黄旭华把自己变成了透明人,家里发生什么事他都不知道,父亲过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忙着解决一个技术难题,葬礼没参加,最后一面也没见着。1970年那个冬天,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了,中国挤进了全球拥有这玩意儿的前五名俱乐部,黄旭华在现场哭得稀里哗啦,那种感觉大概就是"终于能直起腰了",可他还是不敢回家。直到1987年,有家媒体披露了这批科学家的事迹,母亲拿着那份报纸,手抖了半天,原来儿子这些年不是躲着她,而是在干一件没法说的大事。第二年,南海试验结束后,黄旭华终于踏进了家门,老母亲看见他的那一刻,眼泪往下掉,话却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过了好久,她才憋出一句话,是跟其他子女说的:"三哥的事,你们得理解。"这句话比任何道歉都管用。后来有人问他值不值,黄旭华的回答很简单:"国家的账我算清了,家里的账永远还不完。"这话听着挺苦涩,但也没办法,在那个年代,总得有人去填补那些空白。到了晚年,他还在电视里给小孩讲核潜艇的故事,90多岁的人了,说起这些事儿眼睛还会发光,他大概是想告诉后辈,有些账必须得有人去扛,哪怕代价是一辈子的遗憾。主要信源:(环球网——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我的一生属于祖国)
忻州实验中学升旗仪式:听黄旭华故事,学守纪担当,做时代脊梁!
孟金松老师以“国之脊梁—黄旭华的故事”为主题,深情讲述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隐姓埋名三十载,为国家核潜艇事业奉献毕生心血的光辉事迹。这是一堂生动而深刻的纪律修养与精神涵养课,我们以主题升旗仪式凝聚...
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自己
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自己的母亲,谁知95岁高龄的老母亲,望着多年未见的儿子,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那年的南海,碧波之下藏着中国人的底气——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长征一号”完成极限深潜试验,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深潜能力的国家。指挥完试验的黄旭华,鬓角还沾着海风带来的盐霜,就急匆匆往广东海丰的老家赶。这一别,竟是30年。1958年,34岁的黄旭华接到秘密任务,要研制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组织上只给了他一句话:“这项工作要严格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他没敢跟母亲道别,只留下一封“外出工作,归期不定”的信,就钻进了与世隔绝的葫芦岛荒岛。岛上没有图纸,没有资料,甚至没人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黄旭华和团队成员拿着从报刊上剪下来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在空地上用木棍比划,靠着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一点点推算核心数据。最难的时候,连粮食都不够吃,他们就挖野菜、啃窝头,夜里裹着薄被在简易工棚里加班,蚊虫叮咬得浑身是包也没人抱怨。这30年里,黄旭华成了家里的“失踪人口”。母亲托人四处打听,只得到“在外地工作”的模糊答复。有邻居议论:“怕是犯了什么事跑了吧?”母亲总是红着眼反驳:“我儿子不是那样的人。”她把儿子的照片摆在床头,每天擦拭,逢年过节就对着照片念叨:“阿华,你什么时候回来啊?”黄旭华不是不想家。每次收到家人的来信,他都躲在角落里反复读,看着母亲日渐苍老的字迹,看着妻子说“孩子们都长高了,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他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可他不能回信,不能透露半个字,只能把思念压在心底,化作研制核潜艇的动力。有一次,他在试验中突发急性阑尾炎,手术刚结束就挣扎着回到工作岗位,他说:“多耽误一天,国家就少一分保障。”1987年,一篇报道《赫赫而无名的人生》刊登在报纸上,文中隐晦提到了核潜艇研制团队的艰辛,还配了一张黄旭华的工作照。妻子拿着报纸,反复看了好几遍,指着照片对孩子们说:“这是你们的爸爸!”母亲得知后,让家人把报纸念了一遍又一遍,她颤抖着抚摸报纸上的字迹,喃喃道:“我的阿华,是在做大事啊。”所以当1988年,黄旭华出现在家门口时,95岁的母亲愣了许久。她拄着拐杖,一步步挪到儿子面前,浑浊的眼睛紧紧盯着他,嘴唇动了又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30年的牵挂、思念、担忧,在这一刻全都堵在了喉咙里。黄旭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抱住母亲的腿,哽咽着说:“妈,儿子不孝,让您等了这么久。”母亲伸出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抚摸着儿子的头发,从发根摸到发梢,像是要把这30年的空白都摸回来。她的手指冰凉,却带着滚烫的牵挂,泪水顺着眼角滑落,滴在黄旭华的背上。邻居们都围了过来,有人抹着眼泪说:“老伯母,您的儿子是大英雄啊!”那天的晚饭,母亲坚持要亲自下厨,她颤巍巍地炒了黄旭华小时候最爱吃的青菜,煮了一碗鸡蛋面。黄旭华一口一口吃着,味道和记忆里一模一样,可母亲的动作却早已不如当年利索。饭桌上,母亲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却清晰:“阿华,你做的事,妈懂了,不怪你。”这30年,黄旭华错过了太多。他没参加过孩子们的家长会,没在妻子生病时陪在身边,甚至没能在父亲去世时送最后一程。可他用这30年,让中国拥有了核潜艇,让中华民族在世界海洋中站稳了脚跟。他常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黄旭华的故事,不是个例。在那个年代,有无数像他一样的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默默奉献,把个人的青春和家庭的幸福,都献给了国家的国防事业。他们用隐忍和坚守,筑起了共和国的安全屏障,让我们能在和平年代安居乐业。今天,我们享受着岁月静好,不该忘记那些在幕后负重前行的英雄。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人知,但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舍小家为大家”,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自己的
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自己的母亲,谁知94岁高龄的老母亲,望着多年未见的儿子,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1988年春天,黄旭华站在老家斑驳的木门前,手里拎着的旅行袋还沾着南海试验场的沙粒。这位刚完成核潜艇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已经有三十年没踏进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院落。当他轻轻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九十四岁的老母亲正坐在院里那棵老榕树下的藤椅上打盹。阳光透过榕树的枝叶,在老人银白的头发上洒下细碎的光斑。黄旭华的脚步放得极轻,轻到怕惊扰了母亲这片刻的安宁,可旅行袋上的沙粒还是不小心滑落,落在青石板上发出细微的声响。老母亲缓缓睁开眼,浑浊的目光先是茫然地扫过院落,当落在黄旭华身上时,突然定住了。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有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可最终只化作一阵急促的呼吸。黄旭华快步上前,半跪在藤椅旁,握住母亲枯瘦如柴的手——那双手曾无数次为他缝补衣裳、擦拭脸颊,如今却布满了老年斑,指关节僵硬得几乎无法弯曲。“妈,我回来了。”他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沙哑,三十年的思念与愧疚,在这一刻冲破了所有伪装。老母亲盯着他的脸,眼神从茫然逐渐变得清晰,再到泛起泪光。她抬起另一只手,颤抖着抚上黄旭华的额头,又滑到他的脸颊,像是在确认眼前这个两鬓染霜的男人,就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背着行囊离家的少年。“你……你是阿华?”老人的声音微弱得像风中残烛,却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之前看到你寄来的杂志,才知道你在为国家做大事,妈不怪你。”黄旭华用力点头,泪水再也忍不住滚落:“是我,妈,我对不起你。”这三十年,他不是不想回家,而是不能。1958年接到秘密任务那天起,他就成了“隐形人”——核潜艇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不能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不能透露自己在做什么,就连1961年父亲临终前,他都因为试验进入关键阶段没能赶回去奔丧,父亲到死都不知道三儿子在做什么。每次收到家人的来信,看着信中询问“你究竟在忙什么”的字句,他都只能把心酸咽进肚子,用“一切安好,勿念”草草回复。试验场的日子有多苦?没有计算机,几万组数据全靠算盘和计算尺一遍遍核验,为了一个精准数值,团队能连熬好几天;没有现成图纸,就从外国杂志的模糊照片里“大海捞针”,边设计边施工。1988年这次极限深潜试验更是凶险,美国“长尾鲨”号曾在同类试验中艇毁人亡,129人无一生还。当时62岁的他坚持亲自下潜,“我不下潜,将士们怎么敢下?”潜艇不断向深海挺进,舱体传来“咔嗒咔嗒”的承压声,每一秒都惊心动魄。直到成功上浮,他在试验快报上写下“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笔尖的颤抖藏着三十年坚守的释放。可面对母亲,这份“乐在其中”却显得格外沉重。老母亲慢慢收回手,从藤椅旁的小桌上拿起一个褪色的布包,颤抖着打开,里面是一沓沓泛黄的信纸,还有一张黄旭华年轻时的黑白照片。“这些年,我每年都给你写信,写了好多好多,可不知道寄到哪里去。”老人的声音带着哭腔,“1987年看到你寄来的《文汇月刊》,读到那篇讲核潜艇总设计师的文章,提到你爱人的名字,我就知道是你,召集子孙说一定要谅解你。”黄旭华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每一封信都写满了母亲的思念与牵挂,有些信纸上还有泪痕。他突然想起,自己离家时,母亲也是这样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是煮好的鸡蛋和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三十年光阴,国家的核潜艇从无到有,从浅海到深海,成为震慑强敌的“水下移动长城”,中国也跻身世界核潜艇俱乐部第五位,可他对母亲的陪伴,却亏欠了整整三十年。现在总有人说“家国难两全”,可真正能做到像黄旭华这样,把家国放在首位,甘愿用三十年隐姓埋名、用亲情缺席换来国家安宁的人,又有多少?我们总羡慕国家的强大,赞叹科技的进步,却很少想过,这份强大的背后,是多少像他这样的科研工作者,在荒岛上啃着窝窝头、算着算盘珠,把青春熬成白发,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命运。他们不是不懂得亲情可贵,而是深知“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黄旭华在老家待了三天,这三天里,他每天都陪着母亲说话,给她梳头、喂饭,像小时候母亲照顾他那样照顾母亲。可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试验场的紧急电报催他归队,他不得不再次告别。临走时,母亲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愿松开:“阿华,下次回来,早点说。”他重重点头,转身的那一刻,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他知道,自己欠母亲的这辈子都还不清,可他不后悔——当祖国需要有人“一滴一滴流血”,他愿做那个默默奉献的人,这份牺牲,值得。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自己的
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自己的母亲,谁知95岁高龄的老母亲,望着多年未见的儿子,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1988年,南海碧波万顷。一艘中国自行研制的核潜艇,正进行着极限深潜试验。指挥舱里,指令简短而克制,所有人屏住呼吸,仪表上的指针一格一格下沉。就在这次关乎国家战略安全的试验间隙,艇上一位满头白发、神情坚毅的科学家,请了一个极短的假——顺道回家,看望阔别多年的母亲。他叫黄旭华。当车子停在老家的门前,95岁的母亲被人搀扶着走出来。她早已耳背眼花,却仍努力睁大眼睛,辨认眼前这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四十多年未见,儿子从青壮走到白发,母亲从中年等到暮年。她张了张嘴,嘴唇颤抖,却终究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只是泪水无声地滑落。黄旭华跪在母亲面前,重重地磕了头。那一刻,他不是“中国核潜艇之父”,只是一个久别归来的儿子。这一幕,凝结着他一生的选择与付出。时间倒回到19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际形势风云诡谲。核潜艇,这种能在深海长期潜航、具备强大威慑力的国之重器,被西方严密封锁,连一张完整的图纸都不可能得到。国家决定自主研制,黄旭华被点名参与。他原本可以在高校从事教学研究,生活安稳,但当组织征询意见时,他只回答了一句:“国家需要,我就去。”这一去,便是与世隔绝的三十年。项目代号隐秘,地点偏远,参与者对家人也只能含糊其辞。黄旭华给家里写信,从不提具体工作,只说“在外搞研究,一切都好”。母亲病了,他不知道;父亲去世,他没能送终;兄弟姐妹对他长期“失联”也曾埋怨不解。有人问他是否后悔,他只是平静地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研制核潜艇,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没有外援、没有资料,连基本的参数都要一点点摸索。黄旭华和同事们白天画图、计算,夜里在油灯下反复推演。为了解决艇体结构强度问题,他们在算盘上敲出一串串数字;为验证设计合理性,他带头下到模型舱里,亲自体验空间布局。为了节省经费,他建议用最朴素的办法做试验,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最惊心动魄的,是深潜试验。核潜艇要承受的是成百上千米水深的巨大压力,任何一个微小失误,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有人劝他不必亲自下水,作为总设计师,只需在岸上指挥即可。黄旭华却坚持登艇:“设计是我负责的,风险也该我来承担。”那一次,潜艇下潜到极限深度,舱体发出令人心悸的声响,像是钢铁在低声呻吟。黄旭华站在控制台前,双手紧握,目光沉稳。最终,潜艇安全上浮,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之一。成功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清苦。长期高强度工作,让他的身体落下多种疾病;封闭环境中的压力,也让不少同事承受着心理煎熬。但每当看到潜艇入列、看到国旗在深海力量的护航下更加挺立,他就觉得一切都值得。1988年那次回家,是他第一次以“活着的身份”向家人证明:自己并非无情无义,而是把一生交给了国家。母亲说不出话,却在他临走时,紧紧抓住他的手,久久不放。那双苍老的手,仿佛在无声地说:我懂了。后来,随着核潜艇事业逐渐解密,黄旭华的名字才被世人知晓。荣誉、奖章接踵而来,他却依旧低调。他说,核潜艇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代人隐姓埋名、默默奉献的结晶。回望他的一生,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坚定选择;没有惊天动地的个人传奇,只有把国家需要放在一切之前的自觉。那三十年的沉默,换来了深海中的钢铁长城;那一次跪在母亲面前的无言痛哭,承载的是一个科学家对家国最沉重、也最纯粹的担当。
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自己的
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自己的母亲,谁知95岁高龄的老母亲,望着多年未见的儿子,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1988年春天,黄旭华站在老家斑驳的木门前,手里拎着的旅行袋还沾着南海试验场的沙粒。这位刚完成核潜艇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已经有三十年没踏进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院落。当他轻轻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九十五岁的老母亲正坐在院里那棵老榕树下的藤椅上打盹。春日的阳光透过榕树的枝叶,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洒下细碎的光斑。听到门响,老人缓缓睁开眼,浑浊的目光落在黄旭华身上,起初是一片茫然,过了好一会儿,那双眼睛里才慢慢泛起波澜。黄旭华蹲下身,握住母亲枯瘦如柴的手,哽咽着喊了一声“娘”。母亲的嘴唇微微翕动,想回应什么,可话到嘴边,却只是化作了几声轻轻的叹息,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滚落下来。这三十年,对母亲来说是数不清的日夜牵挂,她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不知道儿子在做什么,只知道他在为国家做事,要守着一个不能说的秘密。邻里间偶尔会问起,她也只是摇摇头,说儿子忙,忙点好。黄旭华看着母亲,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当年接到研制核潜艇的任务时,他二话不说就背起了行囊,这一去就是三十年。核潜艇是国之重器,关乎国家海防安全,项目的保密级别高到极点,他不能写信,不能打电话,甚至连一张照片都不能寄回家。多少次夜深人静,他看着窗外的月亮,想起母亲在榕树下盼归的身影,只能把思念埋在心底,转身继续投入到复杂的图纸计算和试验数据核对中。这次深潜试验,他亲自随艇下潜,几百米深的海底,水压巨大,任何一点微小的失误都可能酿成灾难,可他心里除了试验的成败,最惦记的就是家里的老母亲。试验成功的消息传来,他第一件事就是向上级申请,要回一趟家。院子里的老榕树还是当年的模样,树下的石凳磨得发亮,墙角的青苔长得愈发厚实。母亲拉着他的手,不肯松开,一会儿摸摸他的脸颊,一会儿看看他的头发,像是要把这三十年的空白都填补回来。黄旭华陪着母亲坐在榕树下,说着些家长里短,村里谁家添了娃,谁家盖了新房,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两人却聊了很久。关于核潜艇,关于深潜试验,他一个字都没提,他怕母亲知道那些危险,会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这就是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选择,把国家的重任扛在肩上,把对家人的亏欠藏在心底。我们总说岁月静好,却忘了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黄旭华们隐姓埋名的三十年,换来的是中国核潜艇事业的突破,换来的是国家海防的坚不可摧。这份牺牲,不是一句简单的“奉献”就能概括的,那是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思念和割舍换来的。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信息来源:央视新闻《国家记忆》栏目、《黄旭华传》、人民日报人物专访
深潜试验后黄旭华归家探母95岁母亲无言凝望藏半生牵挂1988年,“中国核潜
深潜试验后黄旭华归家探母95岁母亲无言凝望藏半生牵挂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自己的母亲,谁知95岁高龄的老母亲,望着多年未见的儿子,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一年黄旭华已经62岁,从1958年接下核潜艇研制任务开始,他已经和家人断了整整30年的公开联系。30年前他奉命进京时,只跟母亲说“要去外地工作,暂时不能常回家”,却没敢透露具体去向和工作内容。核潜艇研制是国家最高机密,参与项目的科研人员都要签订保密协议,不仅不能向家人透露工作,连通信地址都只能用代号,他写给家里的信,永远只说“一切安好,勿念”,却绝口不提自己在做什么,身在何处。1988年的南海深潜试验,是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关键一役。作为总设计师,黄旭华力排众议,亲自跟着核潜艇下潜到水下300米,这是当时核潜艇的极限深度,每下潜一米都伴随着巨大的水压风险。试验成功的那一刻,艇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黄旭华的眼眶红了,他知道这30年的隐姓埋名、呕心沥血,终于换来了国家海防的坚实屏障。试验结束后,上级特批他顺路回家探亲,这是他30年来第一次以真实身份出现在家人面前,手里攥着的除了试验成功的报告,还有给母亲带的南海特产,只是那袋特产的包装,早就在长途奔波中磨得发皱。推开老家的院门时,95岁的母亲正坐在院子里的老藤椅上晒太阳,手里还攥着他早年寄回家的旧照片。听到脚步声,母亲缓缓抬起头,目光落在他身上时,先是愣了愣,随即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了亮光。黄旭华放下东西,快步走到母亲面前,哽咽着喊了声“娘”,可母亲只是定定地看着他,嘴唇动了又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30年的时光,把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熬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母亲的记忆里,儿子还是离家时的模样,眼前的人既熟悉又陌生,千言万语都堵在了喉咙里。院子里的老槐树还是当年的样子,树下的石桌石凳也没换过,只是母亲的背更驼了,耳朵也听不太清了。黄旭华蹲在母亲面前,握着她干枯的手,把30年的经历慢慢讲给她听,从最初的图纸设计,到在荒岛上的艰苦攻关,再到这次深潜试验的成功,他刻意避开了那些危险和艰难的细节,只挑轻松的话说。母亲全程没插话,只是时不时点头,眼角的泪却顺着皱纹往下淌,滴在了他的手背上,温热的触感让黄旭华的心酸得发紧。他知道,母亲这些年的牵挂,都藏在了那一封封没写地址的回信里,藏在了每天傍晚望向村口的等待里。后来家人告诉他,母亲这些年总在念叨他,逢人就说“我儿子在外地干大事”,却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有好几次母亲生病,都念叨着要见他最后一面,可每次都因为他的保密工作,只能隔着书信寄托思念。这次见面,母亲虽然说不出话,却紧紧攥着他的手不肯松开,连吃饭时都要让他坐在自己身边,时不时给他夹菜,就像他小时候一样。临走时,母亲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她攒了多年的零花钱,硬要塞给他,嘴里终于挤出了几个字“照顾好自己”,那一刻,黄旭华再也忍不住,抱着母亲失声痛哭。这次探亲后,黄旭华的身份才逐渐公开,家人和乡亲们才知道,这个常年不回家的游子,竟然是为国家造核潜艇的大功臣。可对黄旭华来说,再多的荣誉都比不上母亲那无言的凝望,那里面藏着的,是一位母亲对儿子最深的牵挂,也是他30年隐姓埋名的最大亏欠。为国尽忠与为母尽孝的两难,是无数科研先驱的共同抉择。黄旭华的30年沉默,换来了国家海防的底气,而母亲的无言凝望,藏着中华民族最朴素也最伟大的家国情怀。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1988年黄旭华去南海做核潜艇深潜试验,顺道回了趟老家。他母亲已经95岁了,坐在
1988年黄旭华去南海做核潜艇深潜试验,顺道回了趟老家。他母亲已经95岁了,坐在院子里见到他愣了好半天,眼泪一直往下掉却说不出话。这三十年他没回过家,连父亲去世都没赶回来。当年黄旭华突然接到秘密任务就走了,说只去几天结果再没露面。母亲每年给他做两双布鞋,春夏穿的和秋冬穿的,鞋码还是他走时候的尺寸。后来积攒了三大箱子,邻居劝她别做了,她说等儿子回来还能穿。试验成功那天黄旭华想回来看看,坐三天火车到老家。母亲把新做的渔干塞他包里,他发现母亲腿有伤疤也没说。临走前母亲往布鞋里缝了个平安符,他穿着老式布鞋去领了共和国勋章。
988年,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母亲,谁知95岁高龄的老母亲
988年,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母亲,谁知95岁高龄的老母亲,望着30年未见的儿子,竟然激动地说不出一句话来。大家可能不知道,黄旭华这30年“凭空消失”,可不是故意躲着家人。1958年国家启动第一代核潜艇研制,他作为核心技术人员接下任务,第一句话听到的就是“保密终身,不能向家人透露工作内容,连工作地点都不能说”。从那以后,他就跟老家断了“实联系”。之前还能常回家看看,后来只能偶尔写封短信,信里只敢说“在外地搞建设”,连具体在哪、做什么都绝口不提。母亲起初还盼着他回信,后来信越来越少,托亲戚朋友四处打听,都没找到他的下落,甚至偷偷跟邻居念叨“是不是孩子在外头出了啥意外,或是忘了娘了”。其实黄旭华哪能忘?每次夜深人静,他看着口袋里母亲的老照片,都想写封信多说几句,可一想到保密纪律,又只能把话咽回去。当时我国受美苏核潜艇技术严密封锁,连张完整的核潜艇图纸都没有,研发全靠“摸石头过河”,他白天泡在实验室算数据,晚上住在简陋的工棚里盯进度,根本没精力顾小家,更没勇气跟家人解释“为啥不回家”。直到1987年,国家对核潜艇研制的保密政策稍有松动,《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我国核潜艇研制的文章,里面悄悄提了“黄旭华”这个名字,还说了句“隐姓埋名三十载”。母亲看到报纸时,拿着放大镜反复看了好几遍,又让家人念了一遍,才颤着声音说“这就是我儿啊,他没忘家,是在做大事”。1988年的深潜试验,更是赌上了他的命。当时我国核潜艇从没下潜到设计深度,国外曾有核潜艇深潜时解体的先例,不少科研人员心里没底。作为总设计师,黄旭华没让别人去冒险,自己主动穿上潜水服,跟着潜艇下潜到数百米深海,全程盯着仪表盘,直到潜艇成功上浮,他才松了口气——这时候他第一个念头,就是“终于能回家看看娘了”。所以试验一结束,他没跟队伍去庆功,揣着简单的行李就往老家赶。推开门看到母亲的那一刻,他喊了声“娘”,母亲就盯着他看,从头发看到脚,手里攥着他的胳膊,指节都泛白了,半天说不出一个字,眼泪却顺着眼角往下淌。黄旭华也红了眼,蹲在母亲跟前,把这30年的事儿慢慢说,母亲没怪他,只拍着他的手说“娘不怪你,为国家做事,值”。有人说黄旭华“不孝”,30年不陪母亲,可谁知道,他的“不孝”,是让更多家庭能安稳过日子的“大孝”。当时像他这样隐姓埋名的科研人员还有很多,他们把对家人的牵挂,都藏在了国家的发展里。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黄旭华院士家乡小学获授“国字号”招牌
活动指出,新寮小学是黄旭华院士家乡的学校,又恰逢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月,此次新寮小学获授“国字号”招牌,意义深远,必将在孩子们心中播撒爱国防、建国防的种子,激励孩子们茁壮成长,成为国家栋梁。活动强调,强国伟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