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的岭南,总氤氲着一种时序失序的恍惚。
行在横琴的步道上,一抬头,便撞见了一场不合时宜的盛放。粉的,洇成云絮;红的,烧至天边。这般的轰轰烈烈,却都簇拥在铁灰色的光秃枝干上,像一场没有前奏的高歌,灿烂得近乎悲壮。有人怀疑,这是木棉的“第二个花期”,是大湾区一场小小的私心挽留,让春天打了个盹,漏下些缠绵的暖意。
我怔怔地望着,心里却模糊地浮起一个影子,那是在诗文里见过,三四月份开花的“英雄树”。眼前这般景物,难道是偶遇了它?这疑惑,如刺在心,让我不能释怀。
我本来也算一个“异类”,从孕育了二十四节气的中原,迁到这似乎没有冬季的岭南,总觉自己是个冒失的闯入者,看什么都隔着一层温润的水汽,不甚分明。于是常以“异广东人”自嘲,戏谑里带着一点认命般的疏离。不想,这“异”字,竟先在此处与花相逢了。据友人说,这是“异木棉”。撞名的一刹那,我仿佛被别人点破了心事,竟有一丝小小的窘迫,又有些许莫名的亲切。仿佛这树木与我,同是这方水土的客,或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归人。

既是“异类”,便起了寻根究底的念头。经多方求教,始知,岭南的天地间,竟隐藏着这样一场年复一年的错过。那被称作“英雄树”的,是木棉,“浓须大面”,花朵硕大如盏,红得沉郁坚决,不掺一丝杂质,盛放时昂首向天,花谢时“啪”的一声,整朵坠地,不肯萎顿枝头,确有一副掷地有声的刚烈。待“烽火树”的炽热,在三四月份的春风里燃尽,枝头抽出茸茸新绿,天地便换了主角。秋凉一起,那被唤作“美人树”的异木棉,才袅袅婷婷地,敷着满脸的薄粉,缓缓登场。一个落幕,一个登台,清清白白,从无交集,像是宇宙间两条设定好的平行线,各自运行着绚烂的流年,却永不交汇。
这种“错峰出镜”的现象,令我无端地耿耿于怀。仿佛一出没有对手戏的传奇,英雄的铠甲还未冷却,美人的佩环已响在空谷。不知道他们可曾听过彼此的传说?可曾在某个晨昏,通过风、通过鸟、通过泥土深处根须的颤动,传递过一丝半缕难以言喻的讯息?或许,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痴念。草木的世界,自有其严苛而浪漫的自然法则。它们的时序,是刻在基因里的日月星辰,是关乎授粉、关乎存续、关乎物种繁衍的大计。人间的离愁别绪、“当时轻别意中人”的绮思,在大自然的法则面前,大抵是徒然的。我的揣度,不过是把人类情感的油彩,泼洒在它们无言的物候画布上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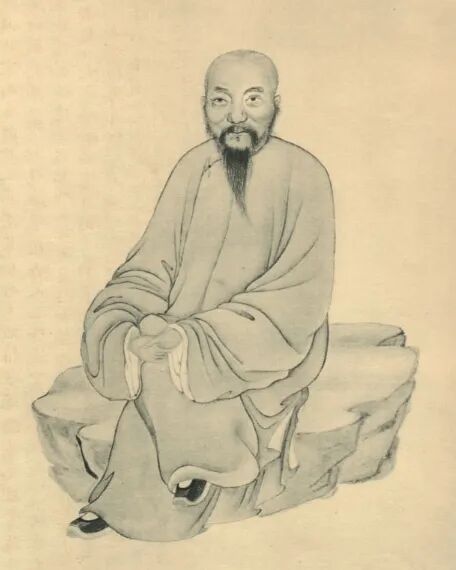
陈恭尹像
然而,这“英雄”与“美人”的冠名,虽别有意趣,但终究是人为赋予。木棉得了“英雄”的名号,是因了那顶天立地的躯干,因了那赤诚如血的花朵,更因了明末岭南志士陈恭尹那一句“浓须大面好英雄”的定评。国破家亡的遗民,见那红棉如烽火,如战旗,便将胸中一股不甘沉沦的壮气,全然寄托了上去。那花,从此便不仅是花,更成了气节的象征,成了岭南风骨里一根倔强的脊梁。木棉花可食,絮可织,皮可药,似乎与苍生冷暖息息相关。而丘逢甲“绝无衣被苍生用,空负遮天作异红”之叹,则为这英雄气添上了一笔亘古苍凉,抱负与际遇的错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何尝不是一种人生“错峰”?

至于异木棉,她的“美人”称谓里,似乎天然带些轻盈的,乃至唯美的意味。那粉黛的颜色,团团簇簇,如云如雾,确有一种惹人怜爱的娇柔。可她偏偏浑身是刺。这刺,幼苗时尤为尖锐,是保护自己稚嫩躯体的甲胄。待岁月磨砺,树干厚实了,足以抵御外物侵袭,那一身锋芒便悄然褪去,功成身退。我审视她一身渐褪的刺,如同检视自己日渐圆融,却未失棱角的脾性,她拂过我的额发,亦如这片水土以温润重塑我的感官。这哪里是仅供赏玩的花朵?分明是一位懂得藏锋守拙、外柔内刚的智者。她的美,是历经防御、挣扎、自保之后,从容而展的一树风华。世人只见她盛放的“黛眉”,谁又曾细辨她成长中那些凛然的“分明”?英雄以决绝的坠地成全气节,美人则以优雅的盛放演绎生存智慧。
那些异木棉的花,粉白中透着一抹极淡的紫,朦朦胧胧,边缘融化在岭南潮湿的空气里,确如女子未曾精心勾勒的眉黛,天然自带一段风韵。这“不分明”,是形态,怕也是身世与性情的注脚。她原产南美,漂洋过海而来,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开了花,成就了岭南冬日难得一见的盛景。她的来历“异”,她的花期也“异”,连她那一身自卫的刺,在温和的岭南也似显多余,且凭空多了一种“异”的痕迹。可正是这诸般的“异”,构成了她独特的存在,一种既融入,又迷人的朦胧。像我,像许多迁徙流转的“异乡人”,眉梢眼角,总带着故土与新壤交织的温润与疏离,眉目神情里,总是杂糅着两处水土、两种气候交错的“不分明”。那不是模糊,而是一种复杂的、层次交叠的清晰。
一阵沁凉的海风吹来,满树粉黛如波涛微吟,飒飒作响,像极了美人的轻声叹息。我徜徉于这绯红的梦境,前不见灼灼英雄红,后不闻萧萧秋木声,唯有这冬日的盛大花事,将我从四面八方温柔围合。左也是花,右也是花,来路与去路,皆隐入这片如梦似幻的粉雾之中。

就在这一瞬,我与花蓦然成了彼此的镜像。不知是我在品评这“异乡”的美人,还是我这“异客”,成了她眼中一道值得玩味的风景。我那耿耿于怀的执念,忽然在这无言的对望中倏然冰释。何必执着于英雄与美人的相见?他们各自占定一段光阴,将生命绽放到极致,成就自身,亦圆满时序。这看似无奈的“错峰”,或许正是天地间最精妙的“对位”——让每一份灿烂都有不可替代的坐标,让宇宙的喧嚣蕴藏一种深邃的宁静。
就像此刻,我立于南海之滨,以“异”客之身,观“异”木之华,心中流淌的却是跨越千年的、关于“木棉”的诗句。时空的层理在此交错、叠合,又生出新的意蕴。孰主孰客?孰古孰今?那界限已然被悄然融解。只觉那花影、诗魂与流转不息的感怀,穿透所有季节的错位与物种的藩篱,暖暖地汇成一团粉雾,将我轻轻包裹。
岭南见我,料应如是;我见岭南,恐亦如是。这眉目交融处的“不分明”,并非含糊,而是历经辨识后的包容与深情。
作者简介

范利青,男,河南淅川人,人力资源管理师、工程师,爱好文学,记录生活本真,收藏点滴美好,曾在《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网》《西安日报》《三角洲》《人民作家》《大河文学》《南粤作家》《深圳文学》《儒林文院》《顶端新闻》《环境生态学》等不同媒体期刊发表散文、诗歌、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