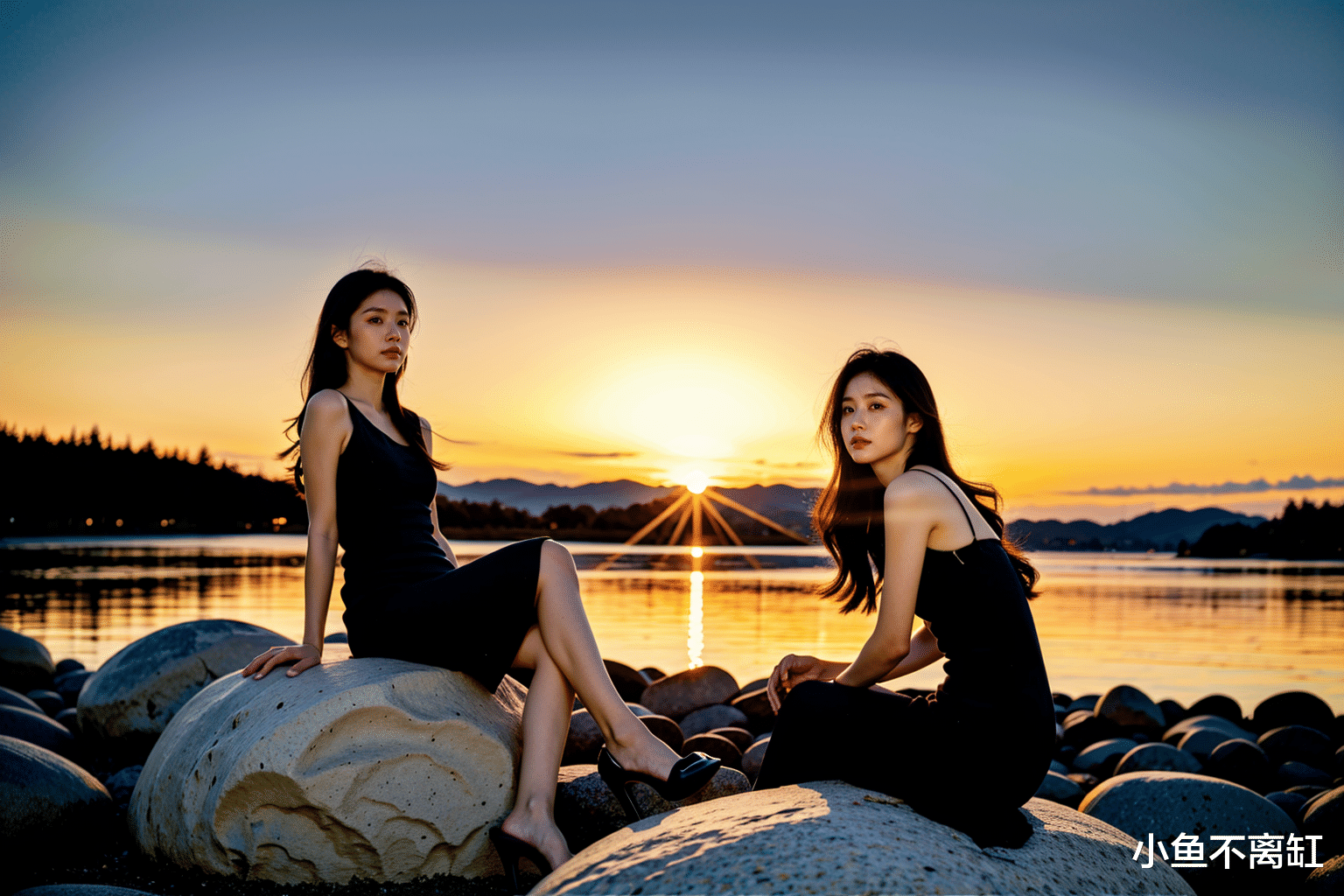
姐姐嫁给陈立那年我 23 岁,搬进他们 130 平的婚房时,我特意选了朝北的小房间。姐夫说朝南的主卧有飘窗,适合姐姐备课,却在我搬进去当晚,把我电脑里所有露肩的设计稿都改成了高领。"当老师家属要注意形象。" 他笑着替我合上电脑,指尖划过我后颈时,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分不清是感动还是不适。

去年深秋的雨夜,我在书房改方案。姐夫应酬回来,领带松垮地挂在脖子上,带着威士忌的气味。他忽然蹲下来,指尖摩挲我手腕上的红痕:"雨雨手冻得发紫了。" 我抬头撞见他镜片后的目光,像冬夜里的路灯,明明灭灭的烫。鬼使神差地,我说出藏了三年的话:"姐夫,我喜欢你。"

从那天起,他开始给我带礼物。藏在我帆布包里的香水,是姐姐梳妆台上同款;夹在我画稿里的珍珠耳钉,转天就出现在姐姐耳垂上。周末家庭聚餐时,他会突然按住我夹菜的手:"雨雨多吃点鱼,看这手腕细得像筷子。" 姐姐的勺子 "当啷" 掉进汤碗,眼尾的痣跟着抖:"阿立,你最近对妹妹太上心了。"
平安夜那晚彻底失控。我加班到十点,推开门看见客厅点着红蜡烛,姐姐坐在地毯上哭,脚边散落着撕碎的照片 —— 是上周姐夫带我去看展时,被他偷偷拍的侧影。"你俩是不是有事?" 姐姐冲过来扯我的头发,发丝缠在她新买的珍珠手链上,"他连我们结婚周年都忘了,却记得给你买画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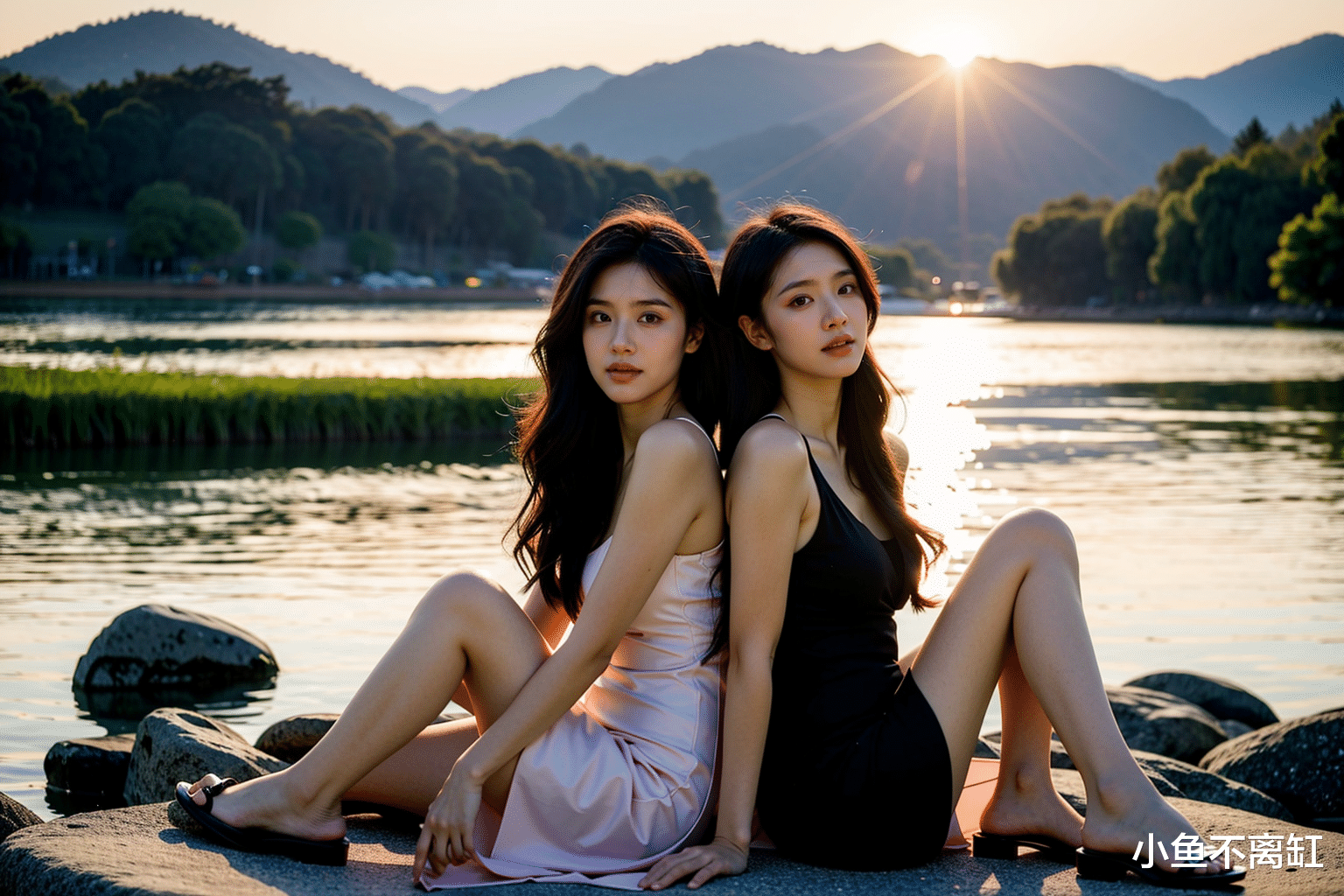
更可怕的是接下来的半个月。姐夫开始在我们洗澡时故意推门,说 "找充电器";深夜敲我房门,说 "梦见晴晴哭,来看看"。有次姐姐出差,他居然穿着睡衣钻进我被窝,滚烫的呼吸喷在我颈侧:"雨雨闻起来像晴晴,又不像晴晴。" 我浑身僵硬,听见他低笑:"别怕,我们是一家人,永远都要拴在一起。"
除夕那天爆发了。姐姐在我衣柜里发现半瓶和她同款的妊娠霜,其实是我随手拿错的护手霜。她尖叫着把我推到衣柜上,木质柜门硌得我后背生疼:"你连孩子都怀上了?!" 姐夫冲进来时,我看见他眼里闪过一丝兴奋,却故意扯开领带:"晴晴你冷静点,是我不好,我两个都爱,以后我们一起生活......"

我这才想起,父母去世后,姐夫总说 "女孩家不要抛头露面",却悄悄撕毁过我的校招 offer;姐姐辞去工作时,他说 "我养你",却把她的医保卡密码设成自己生日。此刻他终于褪去温和面具,额角青筋暴起:"你们以为能离开我?这房子、你们的工作、甚至你妈留的玉佩......"
"都在这。" 姐姐打断他,从口袋里掏出 U 盘,"你帮人做假账的证据,我早就备份了。" 原来她辞职后一直在学审计,那些看似浇花的时间,全用来研究他的文件柜。姐夫的脸瞬间惨白,像被抽走所有血色的纸人。


他忽然扑过来,抓住我手腕拼命掰,那枚银戒划破我的皮肤,血珠滴在他衬衫上:"你们不能走,我不能没有你们......" 姐姐抄起花瓶砸在他背上,清脆的碎裂声里,我看见布偶猫从阳台跳走,就像我们终于挣脱的、长达六年的枷锁。

有时候会想,若当初没说那句表白,是不是还会在他编织的金丝笼里当一辈子提线木偶?但看见姐姐重新扎起利落的马尾,看见自己电脑里终于能存露肩的设计稿,才明白真正的喜欢不该是锁链,而是让彼此在阳光下自由舒展的土壤。至于那个说 "喜欢我们俩" 的男人,就让他永远困在自己扭曲的占有欲里吧,就像他办公室那幅永远闭合的百叶窗,永远见不得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