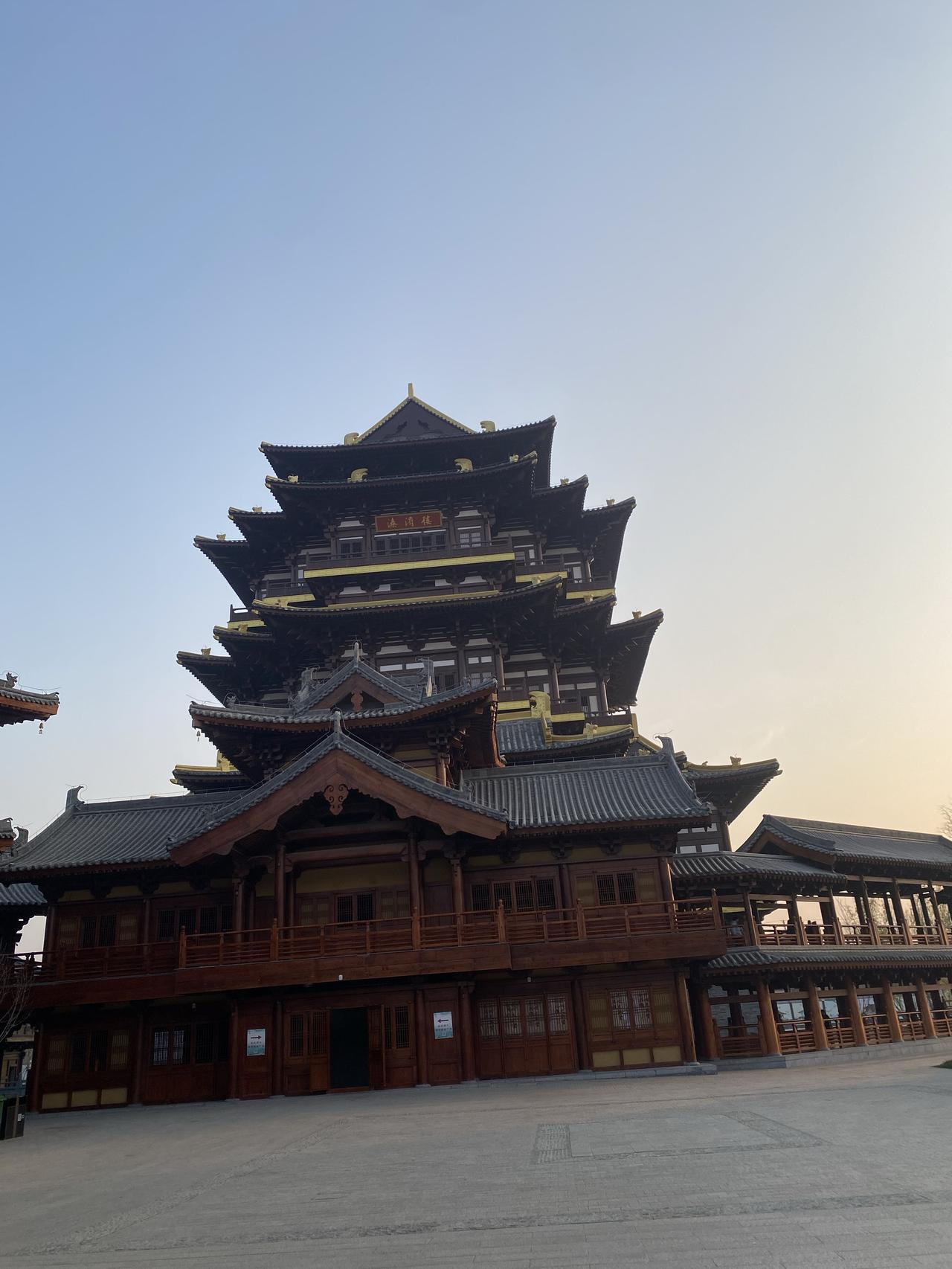“啪——”
老公陆明轩在婆婆的55岁生日宴上突然对着我甩了一巴掌。
“你就不能先给我妈盛碗汤?养你这么多年有什么用!”
陆明轩指着我破口大骂。
我捂着脸还没说话,婆婆又在一旁哭诉:
“我命苦啊,娶个祖宗回来供着!”
小姑子也举着手机在一旁直播:“家人们看,这就是我那个不孝顺的嫂子!”
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笑话,我却笑了,慢慢放下手上的筷子,一字一句地说:
“离婚吧,你净身出户,这日子不过了。”
听到这话,他们却慌了……
01
为了筹备婆婆陈秀珍的五十五岁生日宴,我从三天前就开始拟定菜单和采购清单。
当天清晨六点我就赶往杭州最大的生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那只帝王蟹就花掉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陆明轩在电话里信誓旦旦地说这次一定要让他妈对我刮目相看,可我清楚这不过是又一次自我安慰的幻象。
宴席设在西湖边那家需要提前三个月预定的私房菜馆,暖黄色的灯光洒在红木圆桌上,映照着十二道我亲手制作的菜肴。
空气里飘荡着佛跳墙的浓郁香气和婆婆身上那款过于甜腻的香水味道,这两种气味混合在一起让人有些头晕。
陆明轩的妹妹陆婷婷正举着手机直播这场家庭盛宴,镜头刻意掠过每一道菜却始终没有对准在厨房忙碌了整整六个小时的我。
当最后一道龙井虾仁端上桌时,我的手指已经被蒸汽烫出了两个水泡,但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
陆明轩在桌下轻轻踢了踢我的脚,压低声音说:“晴晴,快给妈盛碗汤,今天她最大。”
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在场的七大姑八大姨都默契地停下了筷子,十几道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
那些眼神里有审视有期待还有陆婷婷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我甚至能听到她对着直播镜头轻声解说的声音。
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伸手去拿婆婆面前的青瓷汤碗,脑子里却突然闪过上个月她当着所有亲戚面说我“不下蛋的母鸡”的场景。
就在我的指尖即将碰到碗沿的瞬间,陆明轩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明显的不耐烦:“苏晴!你是聋了吗?我让你先给我妈盛汤!”
整个包厢顿时安静得可怕,只有火锅汤底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婆婆陈秀珍这时慢悠悠地开口,声音拉得又细又长:“算了算了,明轩你别为难小晴,她从小娇生惯养的哪会伺候人,我能喝上这口汤就知足啦。”
她嘴上说着体谅的话,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我,那种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不称职的佣人。
陆婷婷立刻接话,声音尖锐得能刺破耳膜:“哥,你就是太惯着嫂子了,妈养你这么大容易吗?过生日连碗汤都要等这么久,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家没规矩呢!”
我握着汤勺的手指关节开始发白,手背上的烫伤隐隐作痛。
这些年来类似的场景上演过太多次,每次我都选择忍气吞声,以为退让能换来家庭的和谐。
可这次不知为什么,我突然不想再配合这场荒诞的表演了,那些累积的委屈像潮水般涌上心头。
我放下汤勺,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明轩,我记得你爸去年生日时你说过,咱们家不兴那些虚礼,怎么今年规矩就变了?”
这句话像是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陆明轩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沉了下来。
他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之前,他的手掌已经狠狠甩在了我的左脸上。
“啪”的一声脆响在包厢里回荡,我甚至能感觉到掌风带起了我额前的碎发。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脸颊上火辣辣的痛感迅速蔓延,嘴角尝到了腥甜的味道。
我缓缓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和我同床共枕了四年的男人,他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变形,眼睛里没有丝毫愧疚,只有被挑战权威后的暴怒。
“给你脸不要脸是吧?我妈的话你也敢顶嘴!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他的唾沫星子喷在我的脸上,和脸颊的灼痛感混合在一起。
整个包厢鸦雀无声,连刚才还在煽风点火的陈秀珍和陆婷婷都惊呆了。
公公皱了皱眉,却只是低头抿了一口酒,选择了沉默的纵容。
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清醒了,那种清醒来得如此突然又如此彻底。
过去四年里所有的隐忍和妥协,所有深夜独自吞咽的泪水,所有为了维持这个家而放弃的自我,在这一刻都失去了意义。
我慢慢地,极其缓慢地,拿起餐巾擦了擦嘴角,白色的棉布上留下一抹刺眼的鲜红。
然后我站起身,在所有人错愕的目光中,走到包厢的落地窗前,对着西湖的夜景深深吸了一口气。
转过身时,我的脸上甚至带着一丝微笑,看着陆明轩一字一句地说:“这一巴掌,打断了我们之间所有的情分。”
我的声音平静得出奇,没有颤抖没有哽咽,就像在陈述今天天气很好这样简单的事实。
陆明轩愣住了,他大概以为我会哭会闹会求饶,就像从前每一次争吵后那样。
我从包里拿出化妆镜,对着镜子看了看左脸,五个清晰的指印已经肿了起来,在包厢暖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狼狈。
但我没有哭,反而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然后走到主位前,对着陈秀珍和公公各鞠了一躬。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这四年的‘照顾’,祝阿姨生日快乐。”我的腰弯得很低,姿态恭敬得无可挑剔,说出来的话却让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至于你们的儿子,我原物奉还。”
说完,我拎起挂在椅背上的羊皮手包,踩着七厘米的高跟鞋向包厢门口走去,鞋跟敲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苏晴!你今天敢走出这个门,就永远别想回来!”陆明轩的怒吼在身后炸开,伴随着椅子被踢倒的巨响。
我没有回头,甚至没有放慢脚步。
陈秀珍尖利的哭嚎声追了出来:“造孽啊!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娶了这么个媳妇!过生日给我添堵,这是要气死我啊!”
陆婷婷也在帮腔:“哥,你别追!让她走!走了正好给菲菲姐腾位置!”
听到“菲菲”这个名字时,我的脚步微微顿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节奏。
原来如此,原来早有准备,原来这场生日宴不过是为换人做铺垫的戏台。
走到电梯口时,身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陆明轩追了出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他的力道大得惊人,手腕处立刻传来了刺痛感,但我没有挣扎,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放手。”我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
“苏晴,你现在回去跟我妈道歉,今晚的事我可以当没发生过。”他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语气里混杂着威胁和最后通牒。
我轻轻抽出自己的手,从包里拿出一张湿巾,慢条斯理地擦着他刚才抓过的地方,仿佛那里沾了什么脏东西。
这个动作彻底激怒了他,他扬起手想再给我一巴掌,但在半空中停住了,因为电梯门在这时打开了。
我走进电梯,在门即将合上的瞬间,对着外面那张扭曲的脸轻声说:“明天上午九点,带上结婚证,民政局见。”
电梯门缓缓关闭,镜面里映出我红肿的脸和异常冷静的眼睛。
02
我没有回那个被称为“家”的地方,而是直接去了我在钱塘江边租的工作室。
这个三十平米的空间是两年前我用私房钱悄悄租下的,陆明轩一直以为我只是在这里做兼职设计,实际上它是我为自己留的最后退路。
打开灯,满墙的设计图纸和样布料在冷白色灯光下显得格外亲切,这里没有公婆的挑剔,没有丈夫的指责,只有属于我自己的梦想和汗水。
我反锁了门,第一件事不是处理脸上的伤,而是打开隐藏在书柜后面的保险箱。
转动密码锁时,我的手指在微微颤抖,但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终于要打开这个准备了太久的潘多拉魔盒。
保险箱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样东西:婚前购房的转账记录复印件,我父母赠予的嫁妆银行流水单,陆明轩公司财务报表的备份U盘,还有一本厚厚的剪报。
那本剪报里贴着过去四年陆明轩每一次对我言语暴力的记录,时间、地点、原话,有些甚至录了音转成了文字。
我坐在地板上,一页一页地翻看,那些被刻意遗忘的伤害此刻全都鲜活起来。
三年前我流产住院时,他在病房里说“别人都能保住怎么就你不行”;两年前我父亲做手术需要钱,他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一年前我升职需要加班,他说“女人事业心那么强干什么”......
手机在这时疯狂震动起来,屏幕上“老公”两个字在不断闪烁。
我看着那个曾经让我心动的备注,现在只觉得讽刺至极。
我没有接,而是任由它响到自动挂断,然后熟练地打开通讯录,找到那个名字,点击,加入黑名单。
接着是陈秀珍,陆婷婷,以及陆家所有亲戚的联系方式。
做完这一切,我给闺蜜林薇发了条微信:“薇薇,收留我几天,我离婚了。”
消息刚发出去,电话就打了过来,林薇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焦急:“晴晴你说什么?离婚?你现在在哪?安全吗?”
“我在工作室,很安全。”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明天细说,今晚我想一个人静静。”
挂断电话后,我给自己倒了杯红酒,站在落地窗前看着钱塘江的夜景。
江对岸就是我和陆明轩的婚房,那个我投入了所有积蓄和情感的地方,现在想来不过是个华丽的牢笼。
凌晨两点,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我知道是他。
我按下录音键,然后接通电话,没有说话。
“苏晴,你闹够了没有?”陆明轩的声音听起来疲惫又烦躁,“大半夜不回家,你知不知道妈被你气得血压都高了?”
我轻轻晃着红酒杯,看着深红色的液体在杯壁上留下痕迹:“所以呢?”
“所以你现在马上回来,给妈道个歉,这事就算过去了。”他的语气理所当然,仿佛我只是个闹脾气的小孩子,“菲菲都在家里帮忙照顾妈一晚上了,你看看人家多懂事!”
听到“菲菲”再次出现,我忍不住笑出了声:“林菲菲在你家照顾你妈?陆明轩,你们一家子演这出戏累不累?”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再开口时,他的语气变得强硬:“你少阴阳怪气,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回来,那套房子你一分钱也别想拿到!”
“房子?”我抿了一口红酒,酒精的温热从喉咙滑到胃里,“滨江那套首付二百八十万的房子?其中二百二十万是我爸妈出的,需要我现在把转账记录发给你回忆一下吗?”
“你......”他显然没料到我会提起这个。
我继续慢悠悠地说:“还有你公司那个拿了设计大奖的‘水墨江南’项目,它的核心设计理念和初稿,好像是在我的笔记本上诞生的吧?”
“对了,你书房第二个抽屉最下面,是不是放着三份不一样的财务报表?需要我提醒你,其中一份的备份就在我手里吗?”
电话那头传来粗重的呼吸声,接着是玻璃碎裂的巨响,显然他砸了什么东西。
“苏晴!你居然敢调查我!你他妈早就计划好了是不是!”他的咆哮通过听筒传过来,刺得我耳膜发疼。
“计划?”我放下酒杯,声音冷了下来,“陆明轩,从你第一次动手推我开始,从你妈第一次骂我‘不会下蛋’开始,从你妹妹第一次偷用我的信用卡开始,我就该‘计划’了。”
“我留到现在,不过是想看看,你们这家人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顿了顿,“现在看来,根本没有底线。”
他还在电话那头骂骂咧咧,但我已经不想再听了。
挂断电话前,我给了他最后一句忠告:“明天九点,民政局,如果你还想保住公司的话。”
通话结束,我将长达二十分钟的录音保存,命名为“生日宴的礼物”。
窗外,钱塘江上的游轮缓缓驶过,船灯在江面上拉出长长的光带。
我躺在工作室的沙发上,脸上敷着冰袋,第一次感到四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
03
第二天早上八点,林薇就带着早餐冲进了我的工作室。
她看到我脸上的伤时,眼眶瞬间就红了,想说什么却被我摆手制止。
“我没事,真的。”我把豆浆插上吸管递给她,“比起这个,陪我去见个人更重要。”
我要见的是我的大学导师周教授,他现在是杭州有名的法学专家,也是多家企业的法律顾问。
当年我结婚时,他是唯一明确表示反对的人,说陆明轩眼神不正,家风也有问题。
我现在终于明白,有些人的阅历真的能一眼看透本质。
周教授的办公室在浙大玉泉校区,窗外是满墙的爬山虎,秋日的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进来,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镀了一层金边。
他看着我脸上的伤,长长叹了口气,什么也没问,直接递给我一份名单。
“这几个都是我最好的学生,现在都是杭州顶尖的律师。”他推了推老花镜,“打离婚官司,特别是涉及财产分割和家庭暴力的,我建议你找沈墨。”
他在沈墨的名字上画了个圈:“这孩子是我带过最冷静也最果断的学生,最重要的是,他有正义感。”
我握着那份名单,喉咙有些发紧:“周老师,当年我应该听您的。”
“现在也不晚。”他起身给我倒了杯茶,“三十岁离婚,好过四十岁、五十岁还在火坑里挣扎。苏晴,你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不该被那样的家庭埋没。”
从浙大出来,我直接拨通了沈墨的电话。
他的声音通过听筒传来,沉稳而清晰:“你好,我是沈墨。”
我们约在南山路的一家茶馆见面,那里安静隐蔽,适合谈事情。
沈墨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十分钟,我进门时他已经选好了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一台轻薄笔记本电脑。
他看起来三十出头,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深灰色西裤,金丝边眼镜后的眼神锐利却不失温和。
看到我脸上的伤时,他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专业的神态。
“苏女士,请坐。”他起身为我拉开椅子,“周教授已经简单跟我说了您的情况,不过我还是想听您亲自说说诉求。”
我把准备好的文件袋推到他面前,里面是房产证明、转账记录、U盘,还有昨晚的录音文件。
“我要离婚,越快越好。”我的手指在文件袋上轻轻敲了敲,“我要拿回属于我的每一分钱,包括我父母出的首付,我投进他公司的钱,还有这些年的精神损失。”
沈墨打开文件袋,一份份仔细查看,看到U盘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这里面的东西,您确认过真实性吗?”
“每一份数据都有原始文件可以核对。”我迎上他的目光,“我不是在诬陷,只是在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他点点头,将U盘插入电脑,快速浏览着里面的内容。
随着页面滚动,他的表情越来越严肃,最后甚至倒吸了一口凉气。
“如果这些证据属实,陆明轩先生涉嫌的就不只是转移婚内财产了。”他推了推眼镜,语气凝重,“虚假财务报表,偷税漏税,这些已经触及刑法。”
“我知道。”我平静地说,“所以我才来找您,我需要一个既懂婚姻法,又懂经济法的律师。”
沈墨合上电脑,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苏女士,根据您目前提供的材料,这个案子比一般的离婚诉讼复杂得多。”他的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很有分量,“我们需要多线并行。”
“第一,今天就去医院做伤情鉴定,然后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是他家暴的直接证据。”
“第二,以家暴和感情破裂为由提起离婚诉讼,同时申请财产保全,防止他转移资产。”
“第三,”他敲了敲装着U盘的文件夹,“这份材料,我们先不用。等他的公司出现危机时,自然会有人找上门。”
我有些不解:“不直接用这份证据吗?”
沈墨摇摇头,露出了今天第一个笑容,那笑容里带着律师特有的精明:“最好的武器,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亮出来。现在亮牌,只会让他有准备时间。”
他打开电脑,开始起草文件,修长的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
“我会先以匿名方式,向税务局和工商局举报他公司账目异常,同时联系几个他公司的竞争对手。”沈墨头也不抬地说,“不出三天,他就会焦头烂额。”
我看着窗外南山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突然想起四年前,我也是在这条街上答应了陆明轩的求婚。
那时他说会一辈子对我好,会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现在想来,世界上最讽刺的莫过于誓言,因为它总是在被违背时才显得格外真诚。
“沈律师,费用方面......”我收回思绪,回到现实问题。
沈墨停下打字,认真地看着我:“周教授的学生,第一个案子免费。而且,”他顿了顿,“这样的案子,赢了就是最好的名片。”
离开茶馆时已经是中午,阳光有些刺眼。
我站在路边等车,手机在这时震动起来,是陆明轩发来的短信:“苏晴,我们谈谈,妈说只要你回来,之前的事一笔勾销。”
我看着那条短信,突然想起沈墨刚才说的话:“谈判的前提是双方实力对等,您现在需要的是积累筹码,而不是急着上桌。”
我删掉了短信,抬头看向天空。
杭州秋天的天空总是特别高特别蓝,就像我今天的心情,虽然脸上还带着伤,心里却无比敞亮。
04
陆明轩找不到我,开始换着花样上演苦情戏。
先是给我父母打电话,声泪俱下地忏悔,说我只是一时冲动,他愿意改过自新。
我爸妈虽然心疼我,但这次态度异常坚决,直接告诉他:“晴晴的决定就是我们的决定。”
软的不行,他就来硬的。
第三天下午,他带着陈秀珍和陆婷婷,直接堵在了我父母家楼下。
那是城西一个老小区,邻里都是几十年的老相识,谁家有点什么事第二天就能传遍整个社区。
我妈打电话给我时,声音都在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