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序章:在“上帝”与“垃圾”之间——梦的千年悬案
让我们从一个每个人都无比熟悉,却又因此无比神秘的经验开始:做梦。
夜幕降临,当我们卸下白日里那副由理性、逻辑与社会规范铸成的坚硬盔甲,沉入那片名为“睡眠”的寂静海洋时,另一个“我”,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心灵剧作家”,便会悄然登场。它在我们意识最深处的舞台上,以我们自己为主角,上演一出出光怪陆离、彻底挣脱了现实引力的戏剧。在这些戏剧里,我们时而如雄鹰般翱翔天际,时而如断线风筝般向深渊坠落;早已在时光中逝去的亲人,会带着昔日的温度与微笑向我们走来,而素未谋面的陌生脸孔,却可能带来浸透骨髓的莫名恐惧;我们会在最荒谬不经的场景里,体验到最真实无妄的心悸、狂喜,抑或是无法言说的彻骨悲伤。
天亮时分,大幕骤然落下,这位神秘的剧作家不告而别,悄然隐去,只留给我们一些支离破碎、常常在几分钟内就于记忆中烟消云散的“剧本残页”。
这个纠缠了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幽灵——梦,它到底是什么?
自从人类的意识在地平线上升起,这个问题,就如同一个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威严地盘踞在文明的入口,向每一个试图探寻心灵奥秘的勇敢旅人发出诘问。对于这个谜题,几千年来,人类的心智给出了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同样根深蒂固的答案。而这两种答案,恰好将梦的地位,推向了“神圣”与“无物”的两个遥远极端。
第一个答案,来自神坛之上,来自人类文明那充满敬畏与想象的童年。在这个答案里,梦,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圣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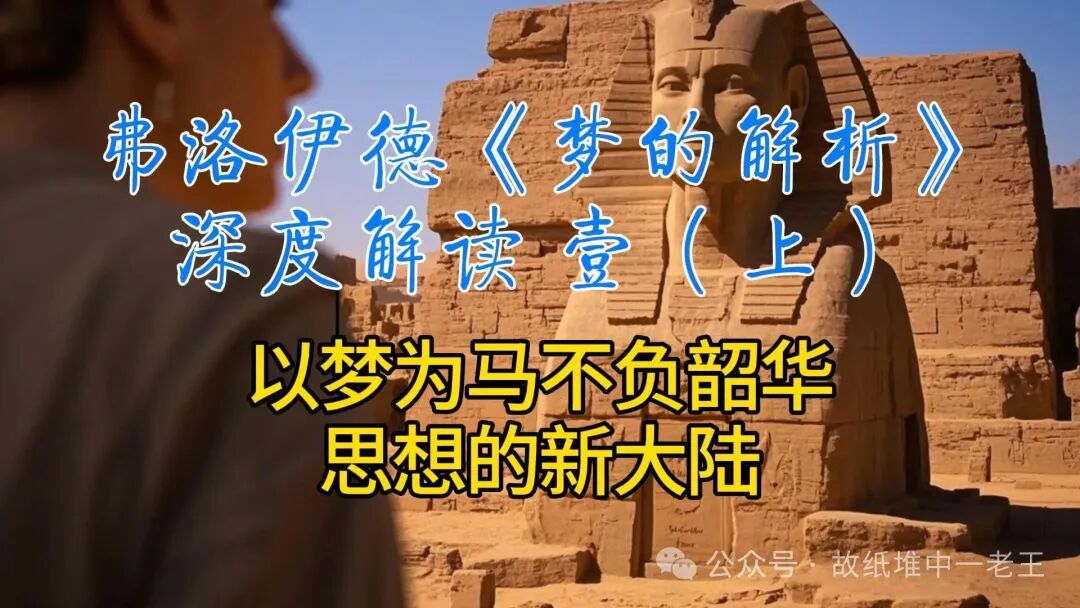
翻开任何一部古老的史诗或宗教典籍,我们都能看到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仿佛是命运的低语,是神祇投向人间的隐秘目光。在古埃及的莎草纸上,梦是太阳神“拉”派遣的信使,是通往幽深冥界的入口,祭司们甚至呕心沥血地编写了厚厚的《解梦书》,试图将梦中的每一个意象,都像破译密码本一样,精准地对应到现实世界的吉凶祸福。在古代巴比伦不朽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英雄吉尔伽美什正是通过解读自己那充满了野牛与巨斧的狂野梦境,才预见了他与恩奇都那场惊天动地的伟大友谊。
即便是在古希腊,这个我们至今仍奉为“理性摇篮”的伟大文明里,对梦的敬畏同样无处不在。从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在梦中与挚友帕特罗克洛斯之魂的悲伤相会,到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里,波斯王薛西斯因一个反复出现的梦境鬼影而决意远征希腊。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里,无数的君王与平民,都曾虔诚地躺在圣殿冰冷的石板上,向上帝祈求一个能够指点迷津的“神谕之梦”。
而在《圣经》的世界里,梦,更是上帝与他拣选的子民之间最直接、最私密的沟通渠道。雅各在旷野的梦中见到那架连接天地的“天梯”,从而获得了上帝的祝福;约瑟夫,这位堪称精神分析“古代鼻祖”的天才,更是凭借其为法老解读“七只肥牛与七只瘦牛”之梦的非凡能力,从一个身陷囹圄的阶下囚,一跃成为权倾朝野的埃及宰相,以神启般的智慧拯救了整个国家免于饥荒的厄运。
在中国,这片同样古老而深邃的土地上,梦的神秘色彩也从未褪色。我们有“周公解梦”的古老传统,将纷繁的梦境与现实的运势紧密相连;有“庄周梦蝶”的哲学沉思,让我们在“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的终极迷惘中,追问着存在与虚幻的本质;更有“黄粱一梦”、“南柯一梦”的世事感叹,用梦的泡影警示着人生功名的虚幻与无常。
在这种贯穿了人类文明几千年的世界观里,梦,不但有意义,而且是一种远比现实更重大的意义。它是一座秘密的桥梁,连接着人与神、凡人与命运、可见世界与那广袤的不可见世界。解梦,也因此是一门需要特殊天赋、虔诚信仰和神圣灵感的“天启的艺术”。
第二个答案,则截然相反,它来自实验室之内,来自人类文明告别童年后,那个自信、叛逆而又略带傲慢的“科学青春期”。
随着文艺复兴的号角吹响,特别是到了19世纪,伴随着神经生理学、实验心理学的强势兴起,人类的理性,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决绝,向一切盘踞在未知领域的“神秘主义”发起了总攻。梦,这个在人类心灵中栖居了数千年的最后一个“幽灵”,自然成了被“科学”的探照灯,第一个要彻底驱散的对象。
科学家们用冰冷的目光、精密的显微镜和测量神经反应的电极,试图将这个神秘飘忽的“幽灵”,还原为一堆可以被测量、被计算、被预测的物理和化学现象。他们用一种近乎轻蔑的口吻,给出了一个与“神启”针锋相对的答案:梦,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神经垃圾”。
弗洛伊德在他《梦的解析》的第一章里,就极其详尽地、百科全书般地,为我们梳理了当时科学界对梦的种种“降维打击”。这些理论,虽然五花八门,细节各异,但其冰冷的内核,都是在试图从根本上证明梦的“无意义性”。
一种理论说,梦是“外部物理刺激”的歪曲反映。法国学者莫里(Maury)做了一系列有趣的实验:他让人在自己睡着时,用羽毛轻搔他的嘴唇和鼻子,结果他梦见自己正在经受一场可怕的酷刑,一块滚烫的沥青面具被从他脸上活生生撕下来。结论是:梦,不过是你的大脑,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对你身体感受到的那点“痒”,进行了一次“夸张而又荒谬的即兴加工”而已。闹钟响了,你可能会梦见庄严的教堂钟声;被子没盖好觉得冷,你可能会梦见自己在冰封的南极探险。
另一种理论说,梦是“内部生理刺激”的产物。你的心脏因某种原因跳动过速,可能会梦见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你的肺部呼吸不畅,可能会梦见被人死死掐住脖子或是在深水下窒息;你的胃部消化不良,可能会梦见正在被迫吃一顿难以下咽的、令人作呕的大餐。梦,无非就是你身体内部各种“器官语言”的一场混乱不堪的“同声传译”。

最主流、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则认为梦是“大脑细胞的随机活动”。德国精神病学家宾茨(Binz)等人认为,睡眠,是大脑皮层的一种“局部贫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大脑的高级中枢失去了统一指挥,那些不安分的细胞便开始进行一些不受控制的、毫无关联的“随机放电”。这些随机兴奋的细胞,就像一群喝醉了酒、冲上舞台的群众演员,随意地组合出各种记忆的碎片、情绪的残渣和感官的幻影,上演一出出毫无逻辑、也毫无目的的“神经狂欢”。
因此,梦,就是一场“精神的无政府状态”。它的内容,与你白天的思想、你的性格、你的欲望,都没有任何必然的因果联系。它就像老式电视机在没有信号时,屏幕上疯狂闪烁的“雪花点”一样,纯粹是机器本身在特定状态下的一种“噪音”。
在这种冰冷的世界观里,梦的心理价值“恰好等于零”。试图去“解析”它,就如同试图去分析肠胃的咕噜声里是否蕴含着人生的哲理,或者妄图从电视雪花点中解读出明天的天气预报一样,是荒谬的、徒劳的、反科学的。
在弗洛伊德动笔写《梦的解析》之前,梦,就如此尴尬地,被撕裂地悬浮在“上帝”与“垃圾”这两极之间。它要么被高高地捧上无法验证、不可触摸的神秘主义神坛;要么被无情地踩入可以测量、但却毫无意义的生理学还原论的泥土。
它唯独,不被当作一种严肃的、具有其独特的内在规律和重大心理学意义的“心理现象”来对待。
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位深受19世纪科学实证主义精神熏陶,毕生都渴望为心理学赢得与物理学、化学同等科学尊严的维也纳神经科医生,他要在这本书中,完成一项前无古人、也因此极具野心的壮举。
他要像一位“思想的破冰船”的船长,以理性的锋刃为船头,同时撞开“神秘主义”和“生理学还原论”这两座看似坚不可摧的巨大冰山。他既要将梦从“神”的手中庄严地夺回,又要将它从“垃圾桶”里郑重地拾起。
他要向全世界宣告一个石破天惊的、全新的第三种答案:
梦,既不是来自上帝的神圣启示,也不是毫无意义的神经垃圾。它,是我们内心世界里,那个最深邃、最隐秘、最真实的“潜意识”的“伪装了的表达”!它有意义,而且是一种可以被科学方法所破译的、极其重要的心理学意义!
“梦的解析,是通往潜意识活动知识的王者之路(The Royal Road to a Knowledge of the Unconscious Activities of the Mind)。”
这句写在《梦的解析》第五章,却早已成为全书精神图腾的名言,就是弗洛伊德为他即将开启的这场伟大心灵探险,所立下的“出征宣言”。它充满了冷静的自信,甚至是一种近乎狂妄的科学野心。
那么,今天的核心悬念就此诞生:弗洛伊德,这位在当时维也纳医学界还饱受争议的医生,他到底是哪来的底气和自信,敢于以一人之力,挑战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和当时如日中天的科学权威?他所说的那个可以“科学解梦”的“万能钥匙”,那个足以开启幽暗潜意识大门的“王者之路”,到底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在他自己的手中,被一次偶然又必然的契机所发现的?
今天,我们将深入《梦的解析》的第一、二章,回到弗洛伊德思想的“寒武纪大爆发”现场,去看他是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废墟中,披荆斩棘,并最终从一个歇斯底里症女病人的梦中,获得了那束如同神启般,照亮整个潜意识深渊的第一道光的。
02
在思想的废墟上——弗洛伊德对“前人”的终极清算
在第一章《论梦的科学文献》中,弗洛伊德做了一件极其耐心、极其细致,也因此显得极其“残忍”的工作。这一章,长达近百页,几乎占据了全书相当大的篇幅。他像一位严谨到近乎“强迫症”的图书管理员,将1900年以前,人类心智所能触及的、所有关于梦的研究文献,从梦与睡眠的关系、梦的材料来源、梦的伦理感到梦的各种理论, meticulously地分门别类,然后冷静地摆放在我们的面前,像是在展示一间陈列着无数失败发明的博物馆。
这个过程,对于不熟悉学术史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感到有些枯燥和冗长。但请相信我,这绝不是一次无聊的“掉书袋”。弗洛伊德这么做,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意图:他要通过对“前人”所有尝试的系统性梳理和无情批判,来反向证明,他即将开辟的那条“新路”,是多么的必要、多么的与众不同,又是多么的具有革命性。
他就像一位即将登场的绝世剑客,在亮出自己的剑法之前,先将江湖上所有门派的剑法——无论是名门正派还是旁门左道——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一拆解、分析,并精准地点出其所有破绽和局限。他要让所有观众们清晰地看到,旧有的“武学”已经走入了无法前进的死胡同。然后,在他自己的那石破天惊的一招亮出的瞬间,才能营造出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颠覆性的震撼效果。
对“神秘主义”的礼貌性告别:密码本 vs. 方法论
对于那些将梦视为“超自然启示”的古代观念和民间传说,弗洛伊德的态度,是一种“尊重的疏远”。他没有简单粗暴地将其斥为迷信,而是以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的敏锐,指出这些古老的解梦术,其实可以清晰地分为两大流派:
第一派,是“整体象征法”(Symbolic Method)。 这种方法,是将整个梦境,作为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寓言故事来理解。比如,法老梦见的“七只肥牛被七只瘦牛吃掉”,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象征着“七个丰年之后,紧接着将有七个荒年”。这种方法,更依赖于解梦者自身的“灵感”、“智慧”与“洞察力”,是一种高度个人化、无法复制的艺术。
第二派,是“密码法”(Decoding Method)。 这种方法,在民间更为流行,也更为机械。它认为,梦是由一堆可以独立拆解的元素组成的,而每一个元素,都可以像查字典一样,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的、象征性的含义。比如,我们熟悉的“周公解梦”就是典型的例子:梦见棺材代表要升官发财,梦见蛇代表好运将至,梦见掉牙则代表亲人可能会有不幸。解梦的过程,就像是把一封用密码写成的电报,对照着一本固定的“密码本”,逐字逐句地、毫无创造性地翻译出来。
弗洛伊德承认,这两种方法,特别是后者,深刻地塑造了普罗大众对梦的看法,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作为一个立志要将心理学建立在坚实科学基础之上的学者,他明确地指出,这种“密码法”式的解梦,无论多么流行,都是不科学的,因为它犯了两个致命的逻辑错误:
忽略了个体差异: 它傲慢地完全忽略了做梦者本人的个体差异、个人生活史和独特的情感联结。同一个“蛇”的意象,对于一个从小在乡下长大、经常与蛇嬉戏打交道的孩子,和一个在城市动物园里第一次隔着厚厚的玻璃见到蛇、并感到毛骨悚然的孩子,其内心的心理意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可能代表着旺盛的生命力或潜藏的危险,后者则可能纯粹是恐惧情绪的直接再现。一本适用于所有人的“通用密码本”,其存在本身就是反心理学的。
方法论的缺失: 它只给出了“答案”,却没有给出推导出答案的“过程”。它告诉你梦见蛇代表好运,但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会建立起这样的连接。这是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神秘主义独断结论,它要求的是信徒,而不是探索者。
所以,弗洛伊德在开篇,就礼貌地、但也是异常坚决地,将“神秘主义”这尊古老而华美的神像,请出了他即将构建的科学殿堂。他要寻找的,不是一本适用于所有人的“解梦密码本”,而是一种能够深入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复杂的个体内心世界的“解梦方法论”。
对“生理学还原论”的猛烈炮轰:当科学家成为“傲慢的化学家”
如果说,对神秘主义的批判还算温和,带着一丝对古人智慧的敬意,那么,弗洛伊德对当时主流的“科学界”关于梦的解释,则发动了一场毫不留情的、火力全开的猛烈炮轰。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所谓的“科学”解释,比神秘主义更危险,因为它打着“科学”的旗号,实际上却是在扼杀对梦进行真正心理学探索的一切可能性。
他将当时科学界对梦的解释,冷静地归纳为几大类,并用他那标志性的、略带反讽的犀利笔触,逐一指出了它们的“致命缺陷”:
“外部刺激论”与“内部刺激论”:只见“扳机”,不见“子弹”弗洛伊德坦率地承认,大量的实验已经雄辩地证明,睡眠中的生理刺激,确实可以“触发”梦境的产生。他详细列举了当时学者们的各种实验:闹钟声可以引发关于钟声的梦,肢体的压迫可以引发关于瘫痪的梦,等等。但是,他紧接着就如同最优秀的检察官一样,提出了那个致命的追问:这些刺激,顶多解释了梦的“某些素材来源”和“触发机制”,就像是扣动了手枪的“扳机”。但它们完全没有,也无法解释,那颗真正射出的“子弹”——即梦境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从哪座军火库里取出来的?“这些刺激的作用,仅仅是为潜意识提供了一个可以附着和表达的机会。”(大意)为何同一个闹钟声,你会梦见欢快的教堂婚礼钟声,而我却会梦见悲伤的葬礼丧钟,另一个饱受考试压力的人,则会梦见宣告考试开始的催命铃声? 那个将“刺激”这个微不足道的“原材料”,加工成一个充满了个人情感色彩、个人记忆和个人冲突的、结构复杂的“梦境剧本”的“心灵编剧”,到底是谁?它的“创作原则”、“戏剧偏好”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又是什么?所有这些生理学理论,都在这个最关键的、真正属于心理学的问题面前,保持了尴尬的沉默。
“大脑随机放电论”:对“意义”本身的彻底谋杀这是弗洛伊德批判的火力集中点,因为这个理论,以科学之名,直接从根源上否定了“解梦”的一切可能性。这个理论认为,梦是“一种躯体过程,而且……毫无意义”。它就像大脑在睡眠时,进行的一次“神经系统大扫除”,将白天积累的无用信息碎片,随机地、混乱地、毫无目的地激活,然后清除出去。弗洛伊德在这里,展现了他作为思想革命家的伟大之处。他没有愚蠢地陷入与生理学家们关于“到底是哪个脑区在放电”的技术性争论。他牢牢地抓住了一个所有人都无法否认的、最核心的“临床心理事实”:梦,是有情感的;梦,是有模式的;梦,是与我们白天的生活和内心的冲突,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割裂的联系的。
情感的强度: 如果梦真的是完全随机和无意义的“神经噪音”,那我们为何会在梦中,体验到比白天清醒时更强烈、更纯粹、更真实的狂喜、恐惧或悲伤?为何我们会从一个噩梦中猛然惊醒,心跳加速,冷汗直流,好几个小时都无法从那份恐怖中平复?“神经噪音”本身,是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
内容的模式: 为何某些特定的主题(比如考试、追逐、飞行、掉牙),某些特定的场景(比如童年的老房子),某些特定的荒谬组合,会反复地、纠缠不休地出现在同一个人的梦里?完全的“随机”,是不会如此固执地产生“模式”的。
与清醒生活的关联: 为何我们梦的内容,总是那么显而易见地,是由我们“白天的残余”(Day's Residues)——那些我们白天里思考过、但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些我们体验过、但没有充分消化的情绪,那些我们渴望过、但被压抑的念头——所构成的?
弗洛伊德在这里,打了一个极其精彩、也极其尖刻的比喻。他说,那些生理学还原论者,就像一群只 meticulously地研究了画布的材质、画框的木料和颜料的化学成分,然后就以科学权威的姿态宣称,梵高的《星空》“不过是一堆碳氢化合物的随机组合,毫无艺术价值和个人意义”的化学家一样,是傲慢而又盲目的。他们用显微镜看到了“物质”,却因此彻底谋杀了“意义”。
通过这场彻底的、不留情面的“学术清算”,弗洛伊德为自己清出了一片广阔的、无人涉足的“无人区”。他像一位王者,独自站在一片思想的废墟之上,向世人雄辩地证明了,在“神秘主义”的过度诠释,和“生理学”的过度简化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等待被探索的科学新大陆——梦的心理学。
而他,已经找到了那张通往新大陆的、独一无二的“航海图”。这张图,不是在图书馆的故纸堆里找到的,而是在他自己的诊室里,在他与那些被歇斯底里症所折磨的病人的痛苦对话中,偶然又必然地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