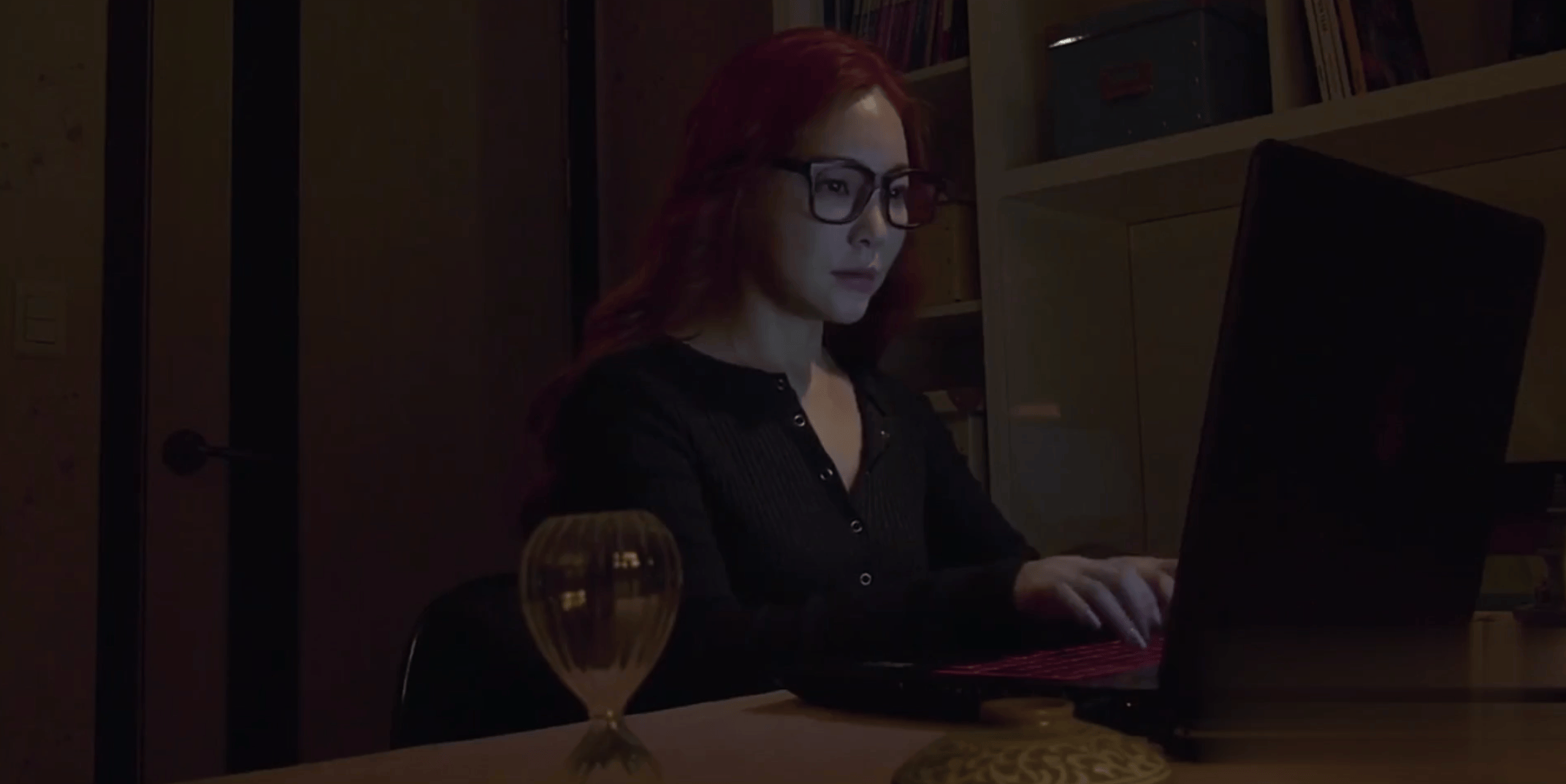
厨房里传来规律的切菜声,像这个雨季的计时器。
我缩在客厅沙发上,第一百次刷新求职网站的回复页面。“很遗憾”三个字以不同字体、不同排版方式出现在屏幕上,整齐得残酷。窗外,首尔的梅雨已经持续了十七天,天空灰得像是永远不会再蓝。
阿姨背对着我,在腌制这个月的第三批泡菜。她矮小的身子微微前倾,肩膀随着揉搓的动作有节奏地耸动。空气里弥漫着辣椒粉、鱼露和捣碎的大蒜混合的辛辣气息——这味道顽固地渗透进墙壁、窗帘和每件衣服纤维里,成为这个“家”无法剥离的底色。
阳台上,我昨天面试被大雨浇透的廉价西装,和她那件洗得发白、袖口已经起球的旧毛衣并排挂着。水珠从毛衣下摆滴落,在水泥地上积起一小滩水,啪嗒,啪嗒,啪嗒。节奏单调得让人心慌。

我们这样“同居”已经八个月了。
父母车祸去世那年我十五岁,阿姨四十三。她是我母亲唯一的妹妹,未婚,在小型服装厂做了三十年质检员。葬礼上她握着我的手,手掌粗糙得像砂纸:“以后跟我过。”不是商量,是陈述句。后来我才明白,那五个字是她用尽全部勇气许下的承诺。
十年后,我大学毕业却撞上就业冰河期,存款耗尽,信用卡债台高筑。电话里我支支吾吾说了不到三句,她在那边沉默了几秒:“回来住吧。泡菜管够。”
于是我又回到了这个三十六平米的老旧公寓。玄关还是窄得转身都困难,卫生间的水龙头依旧漏水,阳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竟然还在。时间在这里仿佛凝固了,除了阿姨头上多出的白发,和眼角加深的皱纹。
我们之间横亘着太多东西:二十岁的年龄差,父母早逝留下的巨大空洞,我青春期时那些伤人的叛逆言语,以及所有未曾说出口的感激与愧疚。对话总是简短而务实:
“晚饭七点。”
“好。”
“下雨了,带伞。”
“嗯。”
只有阳台上并排晾着的衣物,在通风时偶尔纠缠在一起——我的衬衫袖子轻轻搭在她的围裙带上,像某种笨拙的、无声的依偎。这是我们最接近拥抱的时刻。
上周三凌晨,我腹痛如绞。多年的饮食不规律终于报复性发作。我蜷缩在浴室地上,冷汗浸透睡衣。朦胧中听见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阿姨焦急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能站起来吗?”
去急诊室的出租车上,我靠在她瘦削的肩膀上。她身上有淡淡的樟脑丸和肥皂的味道——和记忆里母亲的味道完全不同,却莫名让人安心。输液时我昏昏沉沉,感觉有粗糙但温暖的手一遍遍抚过我的额头,像在安抚受惊的孩子。
第二天清晨醒来,厨房飘来小米粥的香气。阿姨站在灶台前,背影在晨光中显得有些单薄。桌上放着一盒胃药,说明书上用圆珠笔仔细标注了服用时间。

“面试可以再找。”她把粥推到我面前,眼睛却看着窗外,“身体垮了就什么都没了。”
粥很烫,热气模糊了我的眼镜。我埋下头大口大口地吃,眼泪毫无预兆地掉进碗里。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她从未说过“爱”,却把爱我这件事,做成了这十年里的每一顿饭、每一盏留到深夜的灯、每一次无声的担忧。就像阳台上那件旧毛衣,毫不起眼,却能在首尔湿冷的雨季里,提供最实在的温暖。
昨天我偷偷翻看她藏在电视柜下面的相册。在一张褪色的照片里,年轻的阿姨穿着碎花裙子,站在梨花树下笑得很灿烂。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给姐姐。我会过得很好,别担心。”
原来她不仅是我的阿姨,也曾是某个人的妹妹,也曾有过自己的青春和梦想。她把这一切都折叠起来,收进那件旧毛衣的口袋里,然后用那双被泡菜腌入味的手,为我撑起了一个摇摇欲坠却从未倒塌的世界。
雨还在下。我走到阳台,把她的毛衣往里面挪了挪,避免被飘进来的雨丝打湿。我的西装旁边,不知何时多了两双洗干净的袜子——她的纯黑,我的深灰,并排挂着,像某种沉默的宣言。
厨房里,阿姨开始炖泡菜汤。辛辣的香气再次弥漫开来。
我走进去:“阿姨。”
她没回头:“嗯?”
“需要我帮忙吗?”
她顿了顿,递过来一把葱:“洗干净,切段。”
水很凉,葱的味道冲鼻。我站在她身边,第一次注意到她头顶的发旋,注意到她耳垂上那个小小的、几乎看不见的耳洞。我们并排站着,像阳台上那些并肩的衣物。
汤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响。窗外的雨声渐渐小了。这个三十六平米的空间里,两个都不太会表达的人,正在用各自的方式,笨拙地搭建一座桥——跨越年龄,跨越失去,跨越所有没说出口的千言万语。
也许爱从来不需要华丽的宣言。它可能就是一碗烫嘴的粥,是一件晾在阳台的旧毛衣,是在漫长雨季里,有人愿意和你一起,等待天晴。
泡菜汤的辛辣气息弥漫在空气中,很冲,很真实,像生活本身,也像所有埋藏在日常深处的、沉甸甸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