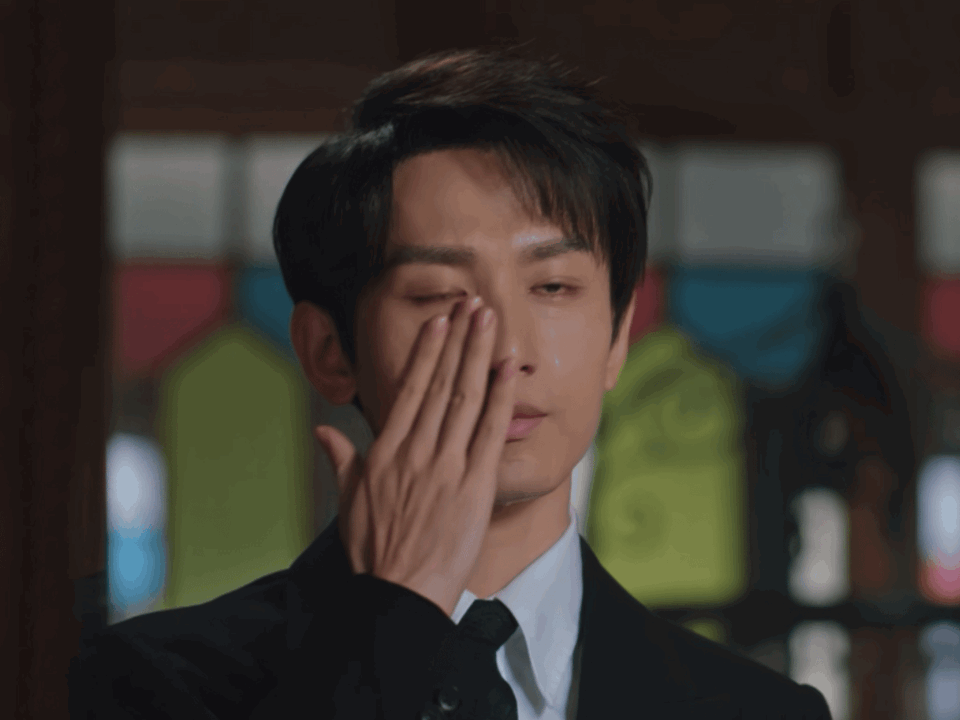我流落在外的第十年,亲生父母来接我回家了。
邻居都说我爹是在朝中当大官的,未婚夫也是人中翘楚。
黄婆给我装了许多果脯:
“幺幺要回家了,幺幺要过好日子啦。”
我也早早换上了新衣裳,欢欢喜喜等着。
可是回家之后,后院失火,兄长和未婚夫都选择了先救养女。
我被带火的横梁砸中了脑袋。
醒来后便听到兄长对未婚夫说:
“你是皎皎的未婚夫,于情于理,你都该去照顾她。之薇这里有我便可。”
“那个傻子?她也配。”后者高坐马上,冷嗤一声,“同我青梅竹马十年的是之薇,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当爷的未婚妻。”
1
“我才不是傻子。”
我推开门,愤愤地打断他们。
“我只是被打伤了脑袋,陈伯伯说我很快会好起来的,我不是傻子。”
说话的两人身形一僵,同时回头,对上我的视线。
面上都有些不自然。
谢清辞同兄长换了个眼神,屈指抵着唇轻咳一声,岔开话题:
“我去找郎中拿药。”
兄长也错开视线,音色冷润:“皎皎,你先歇息,我去买些糕点给你。”
我在火场时的恐惧,和此时的愤怒,谁也没当一回事儿。
我看着他们相继离开的背影,突然又想念黄婆了。
黄婆是过去十年里,对我最好的人。
可我不能就这样回去,黄婆还等着我接她去过好日子呢。
黄崖村的穷日子,我们都过怕了。
于是我捂着还在做疼的脑袋,推开阿爹的书房,对阿爹说:
“我想明白了,阿爹,我要嫁给谢璟。”
阿爹和阿娘对视一眼,似乎都有些诧异:
“你真想明白了?那谢璟可是个太监。”
我刚被接回家那天,阿爹给我搬了接风宴。
阿娘也抱着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几次差点要晕过去。
我照顾完阿娘便去陪阿爹说话。
十年不见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其实早就很模糊了,可我还是很想他们。
我想着同他们说些体己的话。
但是阿爹轻抚着我的发顶,迟疑地开口:
“皎皎,阿爹为你相看了个夫君,是在宫里当差的大太监,谢璟,你觉得怎么样?”
“他名声差是差了点,但对自己人是没得说的。”
“你嫁过去后,少说话多做事,他能保你衣食无忧一辈子。”
我眨了眨眼睛:“阿爹,你和阿娘不能护着我吗?”
为什么要将这般期望寄托在外人身上?
兄长和谢清辞都说谢璟不是好人,专权跋扈,喜怒无常。阿爹怎么会觉得,这样的人能护着我呢?
阿爹哽了下,讪讪地笑着扯开话题:
“阿爹阿娘自然能保你衣食无忧一辈子,但多一个人护着你,不是更好?”
我没接话。
离开前厅后,才听到阿娘和阿爹说:“谁说这孩子傻呢?脑子虽不灵光了,但心里都门儿清的。”
我明白,阿爹和阿娘有了更想护着的人。
原本要嫁给谢璟的人,是宋知薇,而不是我。
但我答应嫁给谢璟,不是因为阿爹阿娘。
我想要的,从头到尾都只有这一桩事——让黄婆过上好日子。
他们在接我回家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提过这件事。
但是兄长和谢清辞,阿爹和阿娘,好像都没当一回事,我只能去求谢璟。
于是面对阿爹的诧异,我坚定地点点头:
“想明白了,我嫁的就是谢璟!”
2
六岁那年,郴州大水,我被冲到了黄崖村,是黄婆捡了我。
但黄婆已然上了年岁,留下我后,日子便越发拮据。
村里的顽童惯会欺软怕硬的,隔三差五便偷屋顶的遮雨的茅草。我和黄婆只好便去追,但他们都是顽劣的性子,仗着黄婆和我追不上,便停下来用石头来砸。
我的脑袋就是那时候被砸的。
很疼,出了很多血,醒来便看见黄婆背着我悄悄抹眼泪:
“幺幺跟着我,受苦了,等你阿爹阿娘找到你就好了。”
这样的话,十年里黄婆说了很多遍。
我不想黄婆哭,也绞尽脑汁想着我的亲生父母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家中又有几口人。
可是我的脑袋坏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学东西也不灵光。
一直到前些时日,宋言川和谢清辞寻到了我。
一个自称是我的兄长,另一个自称是我的未婚夫。
他们说我叫宋皎皎,是丞相府唯一的千金。
临走前,黄婆还摸着我的头宽慰地笑:
“我们幺幺要回家了,幺幺要有兄长和未婚夫了,日后便有人保护你了。”
可睿智如黄婆,大概也没想到,我流落在外乞讨的时候,阿爹已经收养了一个与我有七分相似的姑娘。
我满心欢喜等着回家与至亲重逢,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推开,被放弃。
那场大火里,兄长踹门而入时,火舌已经爬上我的衣裳。
身上好多处都被烫得很疼,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直到他同我对上视线,然后朝我走来。
我绷紧了心弦,隐隐升起些期待。
可他没走两步,就被扛起房梁的谢清辞拉住:“先救之薇,她快吓哭了。”
可是我也很害怕啊,但浓烟呛得我说不出来话,我只能祈求地看他。
谢清辞不耐烦地催促:“都这个时候了,还管什么外人?”
兄长便转身向宋之薇走去。
房梁砸下来瞬间,我满脑子只有“外人”二字。
妹妹和未婚妻也是外人吗?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回来得似乎很不是时候。
兄长,谢清辞,和宋之薇,已经自成一个圈子,而我挤不进去。
思绪回笼,伤口还是很疼。
谢清辞说去找郎中给我拿药,可是现在天快黑了,郎中也没来。
我只好再次捂着脑袋,问了几个下人才找到郎中。
宋之薇也在。
说要给我请郎中的谢清辞和说要给我买糕点的兄长,此刻都一脸紧张地看着郎中。
听见郎中说“宋小姐只是些皮外伤,并无大碍”,他们才都如释重负。
宋之薇向他们撒着娇:
“我都说我没事啦,你们快去陪皎皎姐吧。”
谢清辞揉揉宋之薇的发顶,和方才提起我时冷淡不同,他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是抬头看见我的时候,愣了下。
兄长也看到了我,他起身挡在宋之薇面前。
那是一种下意识的防御姿势。
我想,他来接我的时候,应该也听说了我拿着棍子将同村的顽童打得满头血的事。
可我那么做,只是为了保护黄婆。
兄长却担心我伤害宋之薇。
“皎皎,你怎么下来了?”
显然,他们都忘了应允我的事。
我抿抿唇:
“我疼,来拿药。”
兄长和谢清辞的面上同时闪过慌乱和心虚,连忙示意郎中给我处理伤口。
伤口化了脓,白麻布沾连在皮肤上,上药的时候无异于要撕掉一层皮。
宋知薇看得直皱眉倒吸冷气,拽着谢清辞的手撒娇:
“哥,清辞,皎皎姐的伤口看起来很严重,她会不会很疼啊?”
兄长瞥了我一眼,伸手捂住她的眼:
“别看,别怕。”
谢清辞也避开我的眼神附和:
“没事儿,你看皎皎都没喊疼,肯定不疼的,别担心。”
3
可他又不是我,怎么会知道我不疼呢?
我其实很疼很疼,疼得很想哭。
可是黄婆不在,没人会安慰我,哭闹只有落在会心疼自己的人眼里,才有意义。
不一会儿,宋知薇撒娇说想吃半月楼的桃花酥,兄长拔脚就要去买,却被谢清辞拉住:
“你在这儿照顾之薇……和皎皎,我去买。”
谢清辞风风火火地离开,又风风火火地回来。
好像在完成一件相当重要的使命。
他举着手故意逗宋知薇:“想吃啊,来来来,自己拿,你能够到就都给你!”
宋知薇垫脚伸手蹦了两下,没碰到,便气呼呼地鼓着腮帮子:
“我不吃了还不行吗?”
“好了好了,祖宗,都给你行了吧?”谢清辞便弯腰将桃花酥往她怀里塞。
宋知薇偏偏不接,故意往兄长身后躲。
郎中在这时上完了药,嘱咐道:
“宋小姐伤得不轻,这几日尽量卧榻静养,避免走动。谢公子,宋公子,你们送小姐回去吧。”
方才还在安慰宋知薇吃糕点的兄长和谢清辞,都同时陷入了沉默。
谢清辞悄悄捅了捅兄长,兄长悄悄捅了捅谢清辞。
但是谁也没动。
最后还是兄长用力攘了谢清辞一把,“别忘了,皎皎当初是为了救谁才流落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