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上说,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我醒来后的第一道军令,却是烧光自家粮草,
去抢金人的粮仓。
部下以为我疯了,哭着求我别乱来。
可老子是霍去病,不是岳飞。
在我的字典里,没有撤退,只有把敌人的家,
变成我的牧场!
我要大宋的羊,变成大汉的狼。
01
我醒来时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身上盖着一张
又冷又硬的被子。
一个尖细又傲慢的嗓音扎进我耳朵里。
「岳少保,接旨吧。这可已经是第十二道金牌了,
陛下的耐心是有限的!」
金牌?
我撑着床坐起来,头疼得更厉害了。
眼前终于清楚了一点。
这是一个简陋的军帐,几个穿着盔甲的将军跪
在地上,哭得跟死了爹一样。
帐篷中间站着一个娘娘腔,穿着太监的衣服,
手里捧着个金灿灿的牌子。
两股完全不同的人生记忆在我脑子里猛撞。
一股记忆,是属于一个叫岳飞的男人。
他三十九岁,打了十年仗,马上就要打到金人
老家了。
一个叫赵构的皇帝,连着发了十二道金牌,让
他滚回去。
另一股记忆是我的。
我叫霍去病。
大汉的冠军侯。
我二十四岁就封狼居胥,把匈奴人打得哭爹喊
娘。
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撤退」这两个字。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个叫岳飞的怎么就不懂呢?
我感受着这具身体里积压的憋屈、悲愤,还有
那股子蠢得要死的忠心。
我笑了。
「哈哈……哈哈哈哈!」
整个帐篷里的人都懵了。
那几个哭着的将军,抬起头傻愣愣地看着我。
那个捧着金牌的钦差,脸上的傲慢也变成了错愕。
「岳帅,您,您这是怎么了?」
我掀开被子,站了起来。
这具身体很沉,到处都是伤,眼睛也花了,但还能用。
我走到那钦差面前,一把拿过他手里的金牌。
沉甸甸的,做得还挺精致。
我随手往地上一扔。
「咚」的一声,金牌掉进了泥地里。
钦差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指着我,嘴唇哆嗦着:「你,你敢……你敢扔掉金牌?岳飞,你这是要造反吗!」
我懒得跟他废话。
「锵」的一声,我拔出了挂在床头的沥泉枪。
不对,这玩意儿太长,在帐篷里施展不开。
我又拔出佩剑,对着旁边一张木头做的帅案,狠狠劈了下去。
「咔嚓!」
案角被我一剑砍断。
钦差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尿都快出来了。
我用剑指着他,笑得更开心了。
「好一个赵构,好一个十二道金牌!他这是怕我走得太慢了啊!」
钦差傻了:「岳帅……圣旨是让您班师回朝,是撤退……」
「胡说八道!」
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把他从地上拎了起来。
「连发十二道金牌,就是让我别管那些坛坛罐罐,扔掉所有辎重,全军轻装,直捣黄龙!陛下这是嫌我打得太慢,催我去金人老家过年呢!」
我把他扔到一边,他瘫在地上,已经说不出话了。
我转身看向那几个将军。
他们是张宪、牛皋,还有杨再兴。
都是岳飞手下最能打的。
此刻,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都起来,哭什么呢?死人了吗?」我吼道。
几个人被我一吼,吓得一哆嗦赶紧爬了起来。
「传我军令!」
我的声音不大,但整个大营好像都安静了。
「所有重型辎重,全部烧掉!只留三天口粮,一个时辰后,全军拔营!」
张宪第一个反应过来,他上前一步,急了:「元帅,不可啊!烧了粮草,我们吃什么?而且,我们是要回临安……」
「谁说要回临安?」
我冷冷地打断他,伸手一指北方。
那里,是金军的大营。
我的嘴角咧开一个笑容,露出一口白牙。
「谁说我们没粮了?」
「金兀术的粮仓,不就是给咱们准备的吗?」
02
我话一说完,整个军帐里安静得可怕。
过了好半天,还是张宪这个老成持重的家伙,第一个反应过来。
他往前走了一步,脸都急白了。
「元帅,万万不可啊!金兀术在朱仙镇有十万大军,咱们就这么点人,还是轻装,冲上去不就是送死吗?」
「是啊元帅!」牛皋那个大嗓门也嚷嚷起来,「咱们岳家军打仗,靠的是结阵!步步为营!这么冲,阵型都散了,还怎么打?」
我听得有点烦。
岳飞这套打法,太稳了,也太慢了。
稳到瞻前顾后,慢到机会都从指头缝里溜走了。
「结阵?步步为营?」
我冷笑一声,把手里的剑插回了剑鞘。
「等你们的阵结好了,金兀术的庆功酒都喝完三轮了!」
我走到他们面前,一个一个看过去。
「我问你们,咱们军中,最快的是什么?」
大家面面相觑,没人敢说话。
「是马!」
我替他们回答了。
「传我命令,把全军所有战马,一匹不留,全部集中起来!尤其是背嵬军那八百匹最好的,谁敢藏一匹,我砍了谁的脑袋!」
「元帅!」张宪这下是真急了,「骑兵只能用来骚扰两翼,大军决战还得靠步卒大阵啊!这是咱们十年打下来的规矩……」
「规矩?」
我打断他,声音不大,但帐篷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从今天起,我就是规矩!」
我指着帐外,北风呼啸。
「我只知道,我的马蹄踩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疆土!」
「现在,我的马蹄要踩进金兀术的大营里,那地方,就得姓宋!」
「听懂了吗?」
这次,没人再敢吭声了。
一个时辰后。
朱仙镇,金军大营。
里面灯火通明,跟过年一样。
金兀术以为我们已经开始拔营南撤了,正跟手下大将们喝酒吃肉,庆祝这次「不战而胜」呢。
而我,带着岳家军里凑出来的八百骑兵,像一群幽灵,潜伏在离他们大营不到三里的黑暗里。
这八百人,就是岳飞记忆里最宝贝的背嵬军。
兵是好兵,就是被岳飞用得太小心了。
我感受着胯下战马的鼻息,听着远处传来的隐约笑闹声。
我没做什么战前动员。
对这群饿狼来说,最好的动员,就是让他们闻到肉香。
我拿出长枪,遥遥指向那片灯火。
「杀。」
一个字。
八百骑,瞬间启动。
没有声音。
马蹄上都裹了布。
这是我以前玩剩下的招数。
当金军的哨兵发现我们的时候,我们离营门已经不到一百步了。
「轰!」
八百匹战马同时加速,大地都在发抖。
营门被我们瞬间撞碎。
我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
岳飞的枪法,太正了,一招一式,都是为了破甲、杀敌,很实用,但不够痛快。
我用不惯。
我手腕一抖,长枪在我手里不再是刺,而是抡。
「呼」的一声,长枪带着风声横扫出去。
挡在我前面的三个金兵,连人带盔甲,直接被我扫飞了出去。
这他妈才叫过瘾!
我们这八百人,根本没想过要摆什么阵型。
就是一个字,冲!
金军大营彻底炸了。
无数刚从女人肚皮上爬起来,或者刚从酒桌上站起来的金兵,裤子都没提好,就看到一群杀神从天而降。
他们根本分不清我们有多少人,只看到到处都是黑色的铁甲,到处都是飞溅的鲜血。
很多人甚至以为是自己人火并了,拔出刀就近就砍。
整个大营,乱成了一锅粥。
我不管那些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跑的小兵。
我的眼睛,死死盯着最中间,那顶最大最豪华的王帐!
擒贼先擒王。
我带着身后最精锐的几十骑,像一把锥子,直直地扎了过去。
一个穿着金甲、披头散发的家伙,提着刀从王帐里冲了出来。
他满脸通红,眼神里全是震惊和愤怒。
是金兀术。
他看着我,这个浑身浴血、坐在马上,身后是冲天火光的「岳飞」,嘴巴张了半天。
「岳飞?你……你不是撤兵了吗!」
我笑了。
露出一口被血映得发红的白牙。
「兀术,借你人头一用。」
「回头还你!」
03
金兀术没敢接我的话。
他连滚带爬地翻上一匹没主人的战马,头也不回地往北边跑。
那样子,活像一只被烧了屁股的兔子。
「想跑?」
我冷笑一声,双腿一夹马腹,就要追上去。
但跑了两步,我又停下了。
杀他,不急于一时。
我要的不是他一个人的脑袋。
我要的是他整个金国的胆,都给我碎掉!
「传令下去!」我对着身后已经杀红了眼的背嵬军大吼,「别管那些小鱼小虾,给我咬住金兀术那条大鱼,全军,追击!」
这一声令下,整个乱成一团的金军大营,瞬间被我们抛在了身后。
八百骑兵,加上后面陆续跟上来的轻装步兵,汇成一股黑色的洪流,朝着北方席卷而去。
这一追,就是三天三夜。
我们根本不休息。
饿了,就嚼几口怀里的干粮。
渴了,就喝马奶或者路边的溪水。
困了?
不存在的。
杀人,就是最好的提神药。
金军的后队,被我们像赶鸭子一样追着砍。
很多人跑着跑着,就把手里的兵器扔了,身上的盔甲也脱了。
他们只想跑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岳家军的老将们都看傻了。
牛皋那个大老粗,跑得气喘吁吁,追上我喊:
「元帅,不能再追了!弟兄们都到极限了,再跑下去,马都要累死了!」
张宪也一脸担忧:「是啊元帅,咱们孤军深入,粮草也快没了。金人要是设下埋伏,我们就全完了!」
我听着他们的话,只觉得好笑。
极限?
在我霍去病的字典里,只有敌人的极限,没有我的极限!
「当年我带着八百人,就敢去摸匈奴单于的老家!
现在我手下有你们这几万虎狼之师,这天下,
还有哪里是我去不得的?」
我的声音在旷野上回荡。
「你们以前打仗,太斯文了!」
「打下一座城,还要安抚百姓,还要修筑工事,
还要等朝廷的粮草!」
「等你们忙活完,敌人早就跑没影了!」
我用马鞭指着前面那些丢盔弃甲、亡命飞奔的金兵。
「现在,我教你们一种新的打法!
「什么叫以战养战!」
「我们不攻城,只抢他们的牛羊,烧他们的粮仓,杀他们的贵族!」
「让他们跑,让他们看着自己的家被我们烧成灰,让他们永远活在恐惧里!」
我的话像一把火,点燃了每个士兵心里的疯狂。
他们不再是那支纪律严明、爱护百姓的仁义之师。
他们是一群饿了几天的狼。
他们看着前方,眼神里不再有疲惫,只有嗜血的渴望。
终于,在第四天的黄昏。
我们追到了一条大河边。
河水滔滔,奔腾不息。
金兀术的残兵败将刚刚通过一座浮桥到了对岸。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浮桥给砍了。
站在河对岸,金兀术看着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嘲讽。
我们被拦住了。
牛皋看着断掉的浮桥和湍急的河水,一屁股坐在地上,绝望地捶着地面。
「完了,这下全完了,让他们跑了!」
所有人的脚步都停了下来。
追了几天几夜,最后还是功亏一篑。
那股刚提起来的士气,好像一下子就要散了。
所有人都看着我。
看我这个把他们带到绝境的「疯子」,下一步该怎么办。
是承认失败,掉头回去?
还是在这里等死?
我看着对岸金兀术那张得意的脸,看着他身后那些惊魂未定的金兵。
然后,我笑了。
我催马上前,来到河边。
冰冷的河水,打湿了我的战靴。
我回过头,看着我身后这几万精疲力尽的士兵。
「谁说我们过不去了?」
我用手里的长枪,指向河对岸。
「没桥?直接蹚水过去。」
「对岸有酒有肉,有女人有金子!不敢过去的,就留在这里喂王八!」
04
我的话把所有人都镇住了。
包括河对岸的金兀术。
他脸上的嘲讽凝固了,看着我的眼神第一次带上了恐惧。
他怕了。
他觉得我疯了,而且是个敢把疯话变成现实的疯子。
我没再多说一个字。
我双腿一夹,催动胯下的战马,第一个踏进了冰冷的黄河。
「哗啦!」
河水瞬间淹没了马腿,刺骨的寒意从脚底板一直窜到天灵盖。
但这感觉,很爽。
就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发热的脑子上,让我更清醒了。
我身后的士兵们看着我,犹豫了一下。
然后,杨再兴,那个岳飞记忆里最猛的将领,也跟着我下了水。
一个,两个,一百个……
越来越多的人,默默地跟着我,走进了这条死亡之河。
没人说话。
只有战马粗重的呼吸声,和河水冲刷盔甲的声音。
我们就像一群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水鬼,朝着对岸走去。
金兀术终于反应过来了。
他尖叫着,让手下放箭。
稀稀拉拉的箭雨落下来,软绵绵的,根本射不穿我们的盔甲。
他们也累了。
他们以为自己安全了,弓都拉不满了。
等我们冲上对岸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那些刚刚还在嘲笑我们的金兵,哭喊着,被我们砍倒在泥水里。
鲜血,很快就把岸边的河水染红了。
金兀术又跑了。
我没追。
因为我手下的士兵们,在砍倒最后一个敌人后,就再也站不住了。
他们一个个倒在地上,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
几天几夜的追击,加上刚才的强渡河流,已经榨干了他们最后一丝体力。
更要命的是,我们断粮了。
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两个字:绝望。
我下了马,走到一群瘫倒的士兵中间。
「都他妈给老子起来!」
没人动。
「想死吗?」
还是没人动。
我明白了。
跟这群饿着肚子的家伙讲道理,没用。
我翻身上马,对还站着的张宪和牛皋说:「带上几个人,跟我走。」
我们朝着北方跑了一段距离。
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好地方。
那是一片巨大的庄园,看起来像某个金国大官的私人猎场。
里面有马,有牛,还有肥壮的羊。
我二话不说,带人冲了进去。
看守庄园的几个奴才,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砍了脑袋。
半个时辰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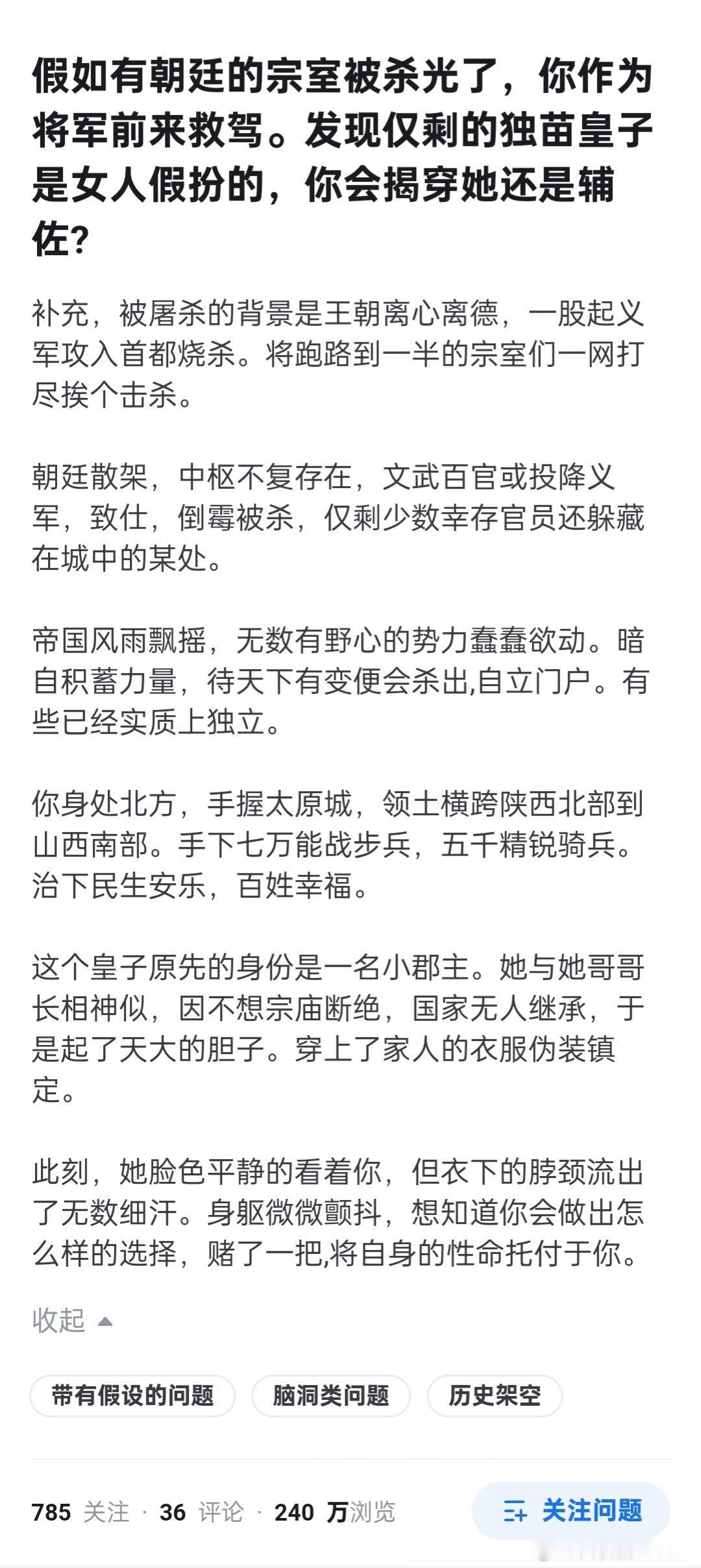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