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村里有一对恋人,小伙叫阿岩,姑娘叫阿禾。两人青梅竹马,海誓山盟,在村民眼中,二人成为夫妇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后来,山外来了一个年轻人,骑着白马,穿着绸缎,脸白白净净。 他在潭边见了阿禾,眼里放光。阿禾起初还躲闪,后来四目相对了。 阿岩去寻阿禾,总见她与那外乡人站在一处,笑声像脆铃。他站在自家低矮的土墙外,看那匹高头大马拴在阿禾家门前,看了很久。 花轿是吹吹打打抬出山的。那日,阿岩不见了。有人说他往更深的山里去了,那里有另一种活法。 再听见阿岩的消息时,他已成了“山里人”——这是对刀口舔血那类人的讳称。 一个秋夜,富家子带着阿禾从外家回来,马蹄在峡谷里敲出空洞的回响。火把忽然从岩后亮起,惊了马。事情发生得很快,几乎没什么响动。火把的光里,阿岩的脸像一块冷硬的岩。他手起刀落,富家子身首异处。阿禾被掳上马背,像掳一件货物,消失在墨黑的山影里。 匪窝在山坳的深处,木屋里充斥着土酒与汗的浊气。那一夜,阿岩喝了很多,醉得像一摊泥,倒在铺着兽皮的木板上,鼾声粗重。阿禾坐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看着油灯的火苗一下下跳。天快亮时,最暗的那一刻,她站起身,从阿岩腰间慢慢抽出那柄杀了她丈夫的刀。刀很沉,她双手握着,对着那起伏的胸膛,顿了顿,然后猛地摁下去。鼾声停了,变成一种漏气的、短促的嘶响,很快也归于沉寂。 她扔了刀,走到屋外,解下腰带,抛上去,打了个死结。 晨雾漫上来时,山林寂静如初,只有那树下,一个影子,微微地,晃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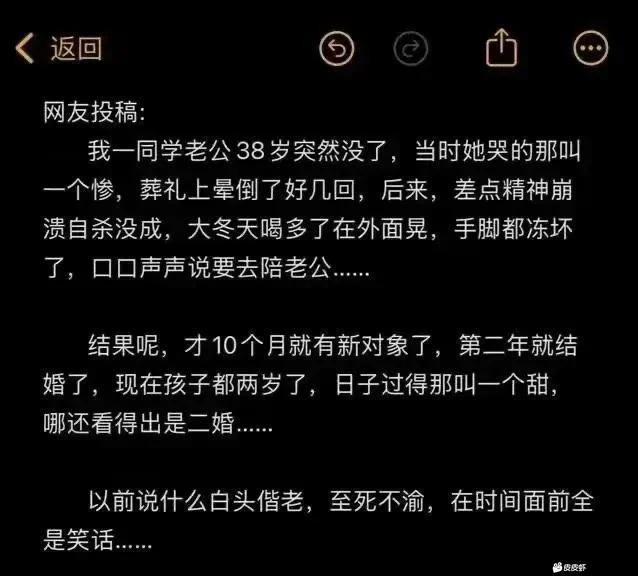

![好家伙,这就是一角一块的原因[笑着哭]](http://image.uczzd.cn/16928436450690562904.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