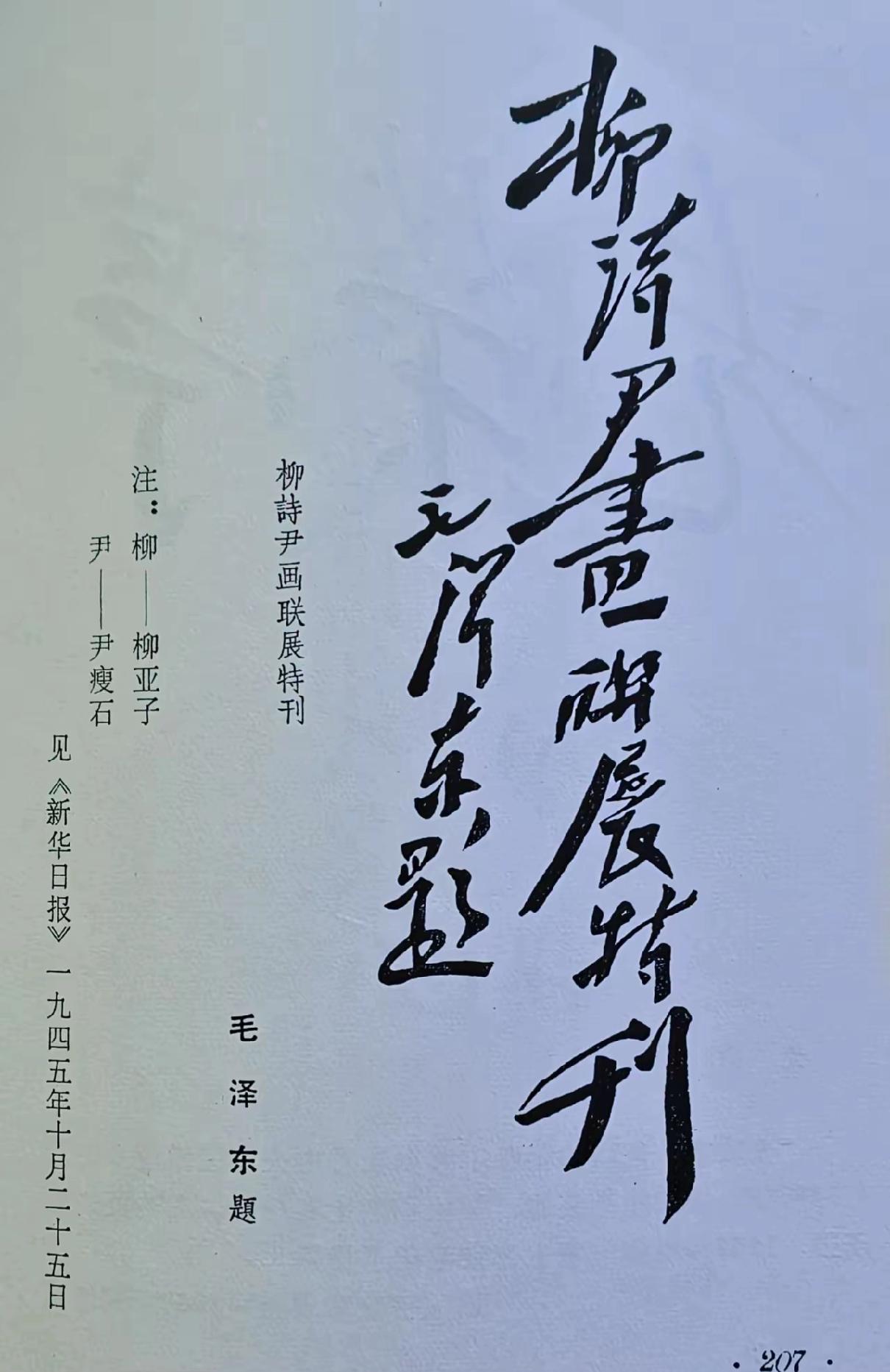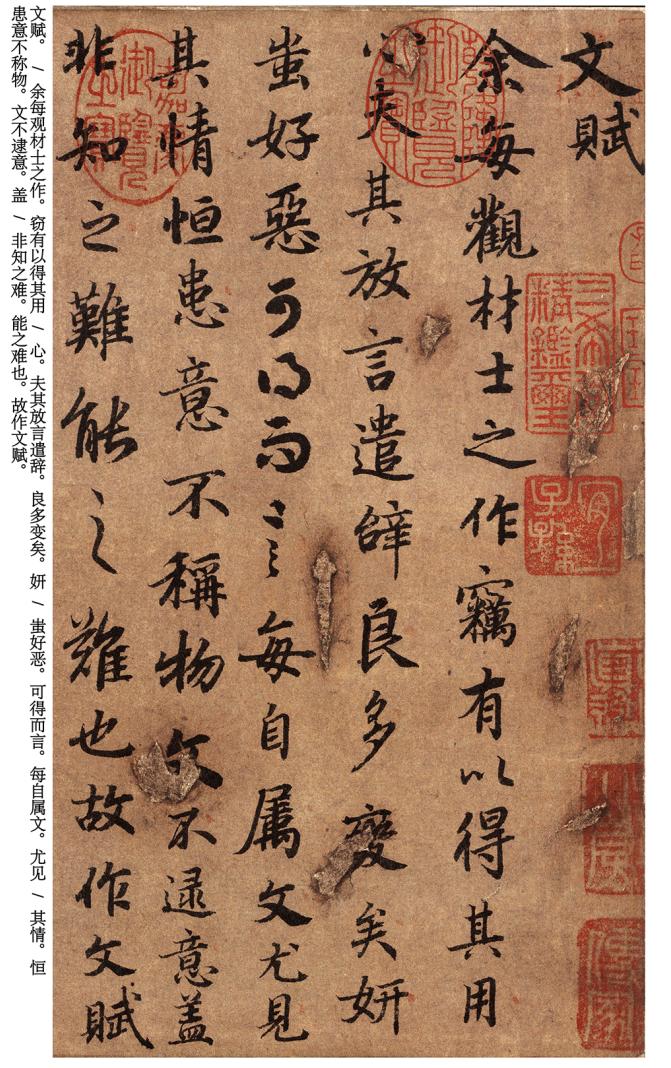1955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以后,林徽因认为碑文应该用楷体来写,但具体由谁来写犯了难,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说:“周总理的字苍劲雄伟,刚劲有力,有如颜碑,风格端庄凝重,可以问问周总理”。 真正的争论,从林徽因手里那张碑心石尺寸图开始。精密测算之后,碑身背面只能容纳3段文字,共114字,分别是29字、30字和55字,段落一段比一段长,气势一浪高过一浪。 她清楚,这样的结构如果用行草来写,远远仰望只会是一团线条,关键的“3年以来”“30年以来”“上溯到1840年”等时间节点,全会淹没在笔画里。 只有楷书这种横平竖直、结构严谨的字体,才能在十几米的高度上依然保证清晰,让每个字像站岗的战士一样稳稳立住。 她的判断并非凭空而来。明清时的大型碑刻,只要是记载大事长文,多用楷书,十三陵的神功圣德碑、曲阜孔庙的碑刻皆如此。几百年风霜过去,那些字依旧可以辨认,这就是最现实的理由。所以她咬定楷书不放。 问题随之落到另一个层面。字体定了,谁来写。有人提议干脆让毛泽东把背面也续写了,正面“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行草字已经惊艳四座,再写114个似乎顺理成章。 林徽因和梁思成却几乎同时觉得不妥。题字需要的是气魄,碑文更强调庄重清晰,若前后都用同一种行草,视觉上会头重脚轻,也违背了题款与正文分工不同的惯例。 这时,彭真提出了周恩来。 在当时的圈子里,周恩来的字是公认有根基的。少年时他按照家塾要求练颜体,又加魏碑练笔锋,久而久之形成颜体为骨、魏碑助劲的风貌,笔画里既有颜真卿那种浑厚稳重,也不乏魏碑干净利落的刀感。 林徽因本就是极重细部的人,她看过周恩来早年为南开题写的校牌,也注意到抗战时期那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心里明白,这样的字写在纸上是题匾,刻在石上就能撑起一段历史。 从会议室到中南海,提议通过后,真正的重量落在周恩来自己身上。忙碌的政务之外,他把碑文草稿摊在案头,从字形结构到通篇气韵一遍遍推敲。 先是拆开来练每个字,像“垂”“朽”这样的字,他要调竖画的挺拔、撇捺的开合,再合起来练整段排比气势,前后写了40多稿,废纸叠起来足有厚厚一摞。 秘书进屋送材料时,常看到他拿着两份稿子对照,甚至用尺子量笔画的倾斜角度,口中念叨,这碑是给英雄立的,一个细节也不能含糊。等他终于选定最满意的一幅,还亲自把手稿送到工地,向雕塑家刘开渠征求意见,态度是“不行就再写”。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过程,那114个字最后才能呈现出独特的力量。 通篇3组时间段的排比,从“3年以来”写到“30年以来”,再写到“由此上溯到1840年”,一段比一段沉,楷书的每一横都像压在历史断面的横梁,每一竖又像从硝烟中挺立起来的脊梁。 反复出现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笔势上也是一层紧接一层,既是为逝者立言,也是对后来人发出的召唤。 纪念碑坐向最后被整体旋转180度,正面行草大字朝向天安门,远远就能看到那8个镏金大字镇住长安街的气场,背面楷书碑文朝向广场,给所有走近的人一个缓缓阅读历史的机会。行草和楷书,一远一近,一主一辅,构成了这座“石书”的双重封面。 站在今天回望,当初那些主张“再找名家更保险”的声音早已被事实回应。别的名家或许写得更玄妙,却很难写出周恩来那一代人从鸦片战争阴影一路走来的切身感受。 正是他对人民英雄发自内心的敬意,对这段历史的亲历和理解,才能在字与字之间撑起真正的分量。 人民英雄纪念碑因此不只是一块石碑。正面8个行草字把“永垂不朽”写成了誓言,背面114个楷书字则把自1840年以来的民族苦难与抗争压进碑心。 林徽因坚持楷体,梁思成守住整体形制,彭真想到周恩来的字,周恩来又用40多遍书写去匹配这份托付,几条线叠在一起,最终让这组文字成为纪念碑真正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