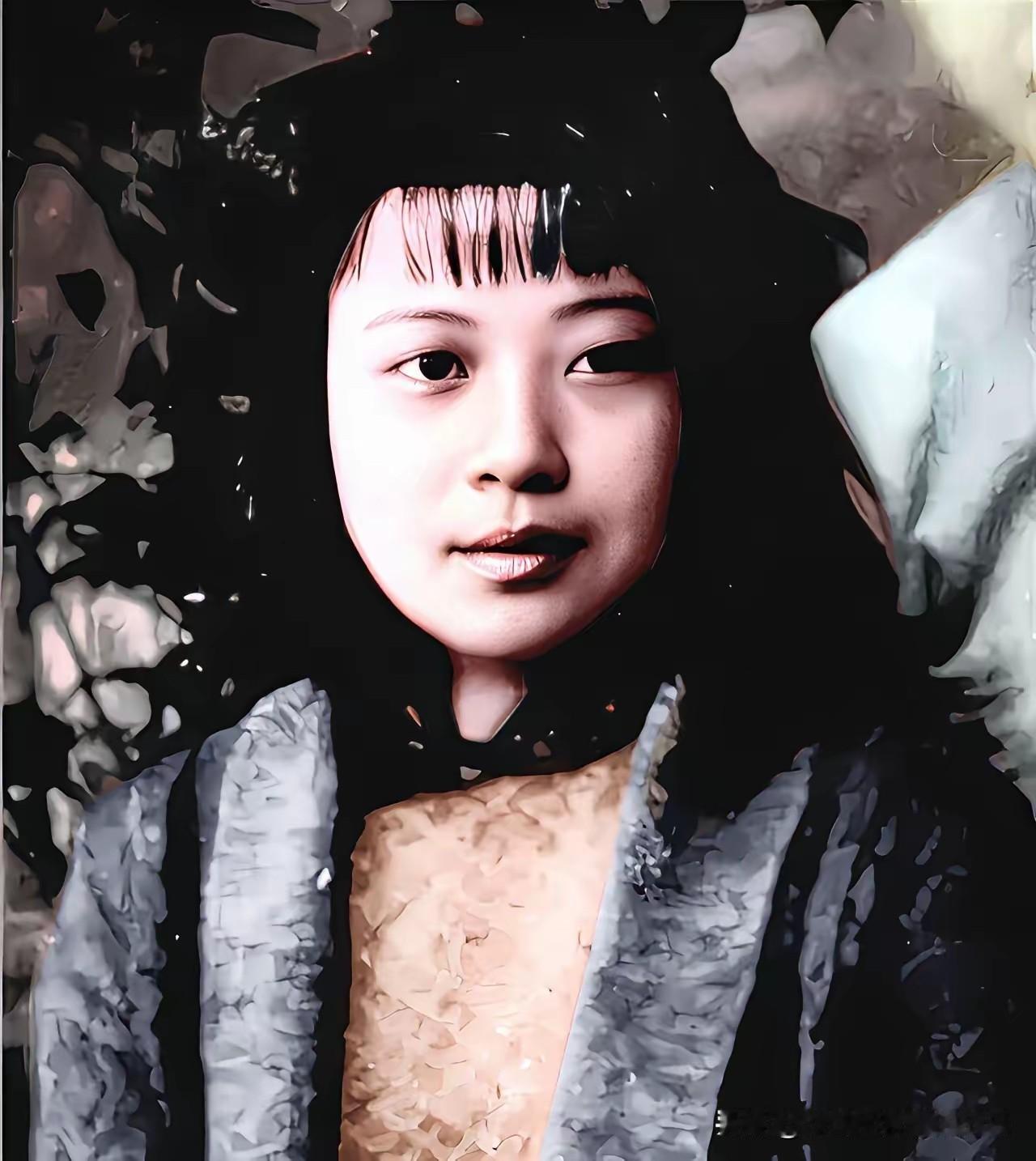1963年,陈广胜当了师长,听说老家那个拜过堂的媳妇秀兰还在,一个人拉扯着他走时还没出世的儿子,日子快过不下去了。 他就让警卫员回村带话,叫娘俩都来省城住。秀兰听完,眼皮都没抬,手里纳着鞋底说:“你告诉他,我不去,他也别回来。”警卫员愣在院子里,秀兰已经把门关上了。 警卫员攥着没递出去的路费,一路小跑回了省城。陈广胜正在办公室看地图,听完整句话,手里的钢笔“啪”地掉在桌上,墨水在地图上晕开一小片黑渍。他盯着那片污渍出神,想起1940年离家的那个清晨,秀兰站在村口老槐树下,红着眼圈塞给他一双新做的布鞋,说“我等你回来”。 这一等,就是二十三年。他在战场上九死一生,从士兵熬到师长,身边早没了当年的硝烟,却始终不敢忘了老家的牵挂,只是军务繁忙,竟没来得及回去看看。 秀兰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手里的针线扎破了手指,血珠渗在米白色的鞋底上,像一朵小小的红梅。她不是狠心,是不敢去。 当年陈广胜走后第三个月,她就发现怀了孕,村里的闲言碎语像针一样扎人,说陈广胜怕是早死在外面了,劝她改嫁。可她记得陈广胜临走时的眼神,那样坚定,她不信。 公公早逝,婆婆常年卧病,她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给人纳鞋底换粮食,硬是撑着把婆婆送走,把儿子拉扯到二十岁。 儿子陈念军放学回来,看到娘坐在地上,手指还在流血,赶紧找来布条包扎。“娘,是不是爹那边又来人了?”念军的声音带着少年人的清澈,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当大官的爹,却从没见过。 秀兰摸了摸儿子的头,叹了口气:“你爹让咱们去省城,娘没答应。”念军低下头,摆弄着衣角:“我知道娘为啥,你是怕去了给爹添麻烦,也怕我忘了咱老家的根。”秀兰眼眶一热,这孩子从小懂事,跟着她吃了不少苦,却从没抱怨过。 陈广胜没放弃,过了半个月,又让秘书带着粮食和钱去了村里。秀兰还是没开门,让邻居转告:“东西拿回去,广胜要是真有心,就别搅和我们娘俩的日子。” 秘书回去后,跟陈广胜说村里的情况:秀兰这些年不容易,念军在县中学读书,成绩拔尖,秀兰靠纳鞋底和种地供他,村里人选她当妇女主任,都说她是个硬气人。陈广胜听着,胸口像压了块石头,他知道秀兰的脾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其实秀兰心里清楚,陈广胜如今身份不同了,身边或许早就有了新的生活。她不想去省城看人脸色,更不想让儿子活在“师长儿子”的光环下,她要让儿子凭着自己的本事立足。 有一次念军发高烧,半夜里她背着儿子往镇上跑,走了十几里山路,鞋都磨破了,脚底板全是血泡。那一刻她也想过,如果陈广胜在身边就好了,可转念一想,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也就没必要再去依附谁。 陈广胜后来又托过几次人,都被秀兰婉拒了。直到1965年,念军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报到那天,秀兰送他到村口,只说了一句:“去了好好读书,别找你爹,咱娘俩的日子,咱自己过。”念军点点头,他知道娘的骄傲,也懂娘的深情。 那个年代的女人,大多有着这样的坚韧与自尊。她们守着承诺,扛着苦难,用单薄的肩膀撑起一个家,不求依附,不求回报。秀兰的拒绝,不是不爱,而是爱得太深沉,太骄傲。她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儿子,也守护着那段跨越二十多年的牵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