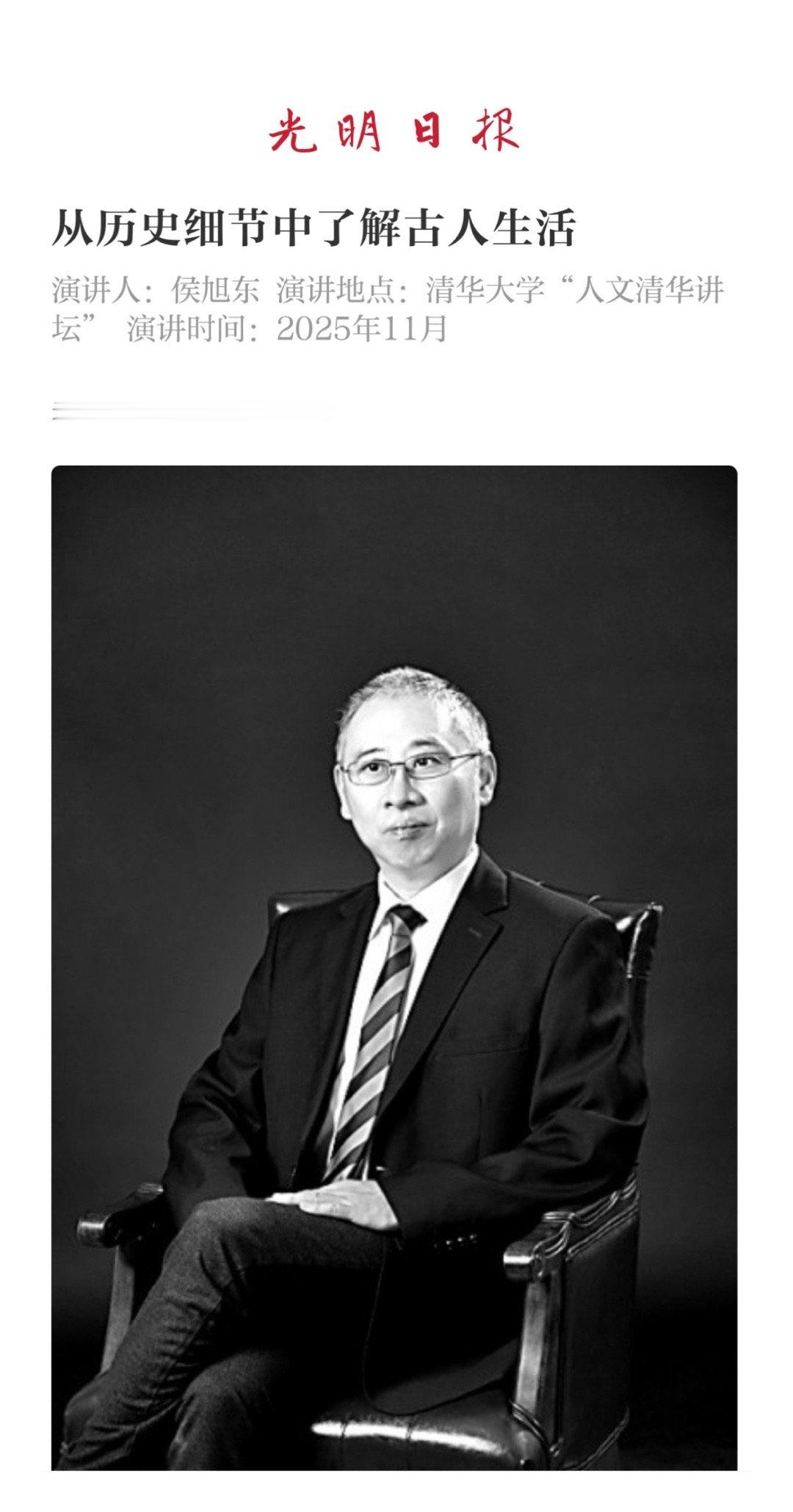【从历史细节中了解古人生活 ——侯旭东教授在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 的演讲】 (光明日报 2025-11-29 07:53 ) * 侯旭东 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秦汉三国文书简牍、早期中国国家形态与运行机制等。著有《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等,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 [ 在考古发现中探索古人饮食秘辛 ] 我们今天的讲座,要从西汉景帝说起。不过我们这次讲的并不是汉景帝在历史上的著名事迹,诸如“文景之治”、平定七国之乱等,而是汉景帝和老鼠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缘起就隐藏在汉景帝的阳陵里。现在我们所见的阳陵,中央是高高的封土,四周是田野。但这不是2000多年前汉景帝葬于此地时的样子,那时阳陵四周有许多建筑,地下也埋有大量随葬品。考古学家经几十年勘探研究,发现阳陵封土四周共有80多条外藏坑,从平面图来看每面约20多条。考古人员对阳陵东侧外藏坑部分做过发掘,出土的文物多收藏于附近的阳陵博物馆。其中13号、14号和16号外藏坑出土了不少动物骨骼。经过鉴定,其中有常见的牛、羊、兔、犬,以及猫、狐狸、豹子、四不像、鹿等,还有多种软体动物。其中特别的是出土了两块老鼠骨头,经鉴定认为是褐家鼠。 大家可能会问,外藏坑为何会埋藏如此多的动物骨骼?从丧葬观念来说,汉代人认为人死后在地下仍需吃喝、穿衣、出行,所以会在墓葬中埋入亡者的生前用品,外藏坑中的这些动物当初就是作为随葬食材放入的。而且不仅在地下,在地上皇帝的宗庙中,汉代人也会给已故祖先供应食物。目前推测汉代人一天吃2顿饭,但是汉代人给先帝所供食物的频次却不是这样,文献记载当时每天供应4顿饭,甚至比亡者生前还要多。 对于出土动物骨骼中的2块褐家鼠骨头,曾经有推测认为可能是外藏坑埋葬后,老鼠钻洞进入后死亡,历经上千年被考古人员挖出。当时动物考古学家对阳陵外藏坑动物骨骼进行鉴定后就判断,除后期侵入外藏坑的褐家鼠之外,其他骨骼都属于汉景帝的生前膳食随葬。 这个判断看似合理,但它是否正确?几年前我偶然看到这样的结论,随即产生了疑问——因为我联想到了河北满城汉墓的出土情况。满城汉墓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之墓。1968年解放军在满城当地施工时发现了山中墓葬,考古人员随后对墓葬进行了发掘。这两座墓均在山中开凿且规模很大,刘胜墓为1号墓,位于南侧;其妻窦绾墓为2号墓,位于北侧。满城汉墓出土了河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长信宫灯和金缕玉衣。 除了器物之外,满城汉墓中还有不少发现:1号墓的北耳室和2号墓的南耳室都有大量不同类型的陶容器,里面装有酒和各类动物骨骼。其中三个陶容器里有许多小骨头,考古人员经过鉴定后判定,1号墓的一个陶瓮(编号1:3502)以及2号墓的陶壶(编号2:2024)和陶罐(编号2:2205)中,有岩松鼠、社鼠、褐家鼠等多种老鼠骨骼,还有黄鼬(黄鼠狼)。这些老鼠数量达到几十甚至上百只,且有的容器(如陶壶)还有盖。这些老鼠显然不是后期侵入的。考古学者判断,陶罐、陶壶中的老鼠是当时作为食材放入耳室的,而耳室的功能相当于地下厨房,因此推断中山靖王刘胜和窦绾生前的食谱中包括老鼠,故下葬时将其作为食材随葬。 无独有偶,近年发现的河南新乡汉墓,其中5号汉墓也出土了不少老鼠骨骼,经鉴定为中华鼢鼠和东北鼢鼠。从生活习性来看,这两种鼢鼠具独居属性、不会聚集,但墓中却同时出土了不少骨骼。结合中山靖王墓以及南越王墓的情况,考古学家推断这些老鼠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食物,作为食材随葬。 中山靖王刘胜是汉景帝之子,他的食谱中存在老鼠,是否意味着汉景帝也有类似食谱?这种可能性很大,但父子也可能存在食俗差异,不能直接证明阳陵老鼠的用途。 因此我们再度把目光转回到阳陵。从阳陵外藏坑的构造来重新考察出土老鼠骨骼来自当时随葬还是事后侵入。考古学家提供的剖面图显示,下方两层为木结构外藏坑。上方有两层棚木,盖好后铺放垫土,垫土厚2.88米至3.38米,是汉代修建完外藏坑后铺设的,分若干层;棚木厚14厘米至32厘米,共两层。这样的构造意味着,外面的褐家鼠如果要侵入外藏坑中,需穿过约3米厚的垫土层,还要咬穿十几厘米厚的两层棚木。而根据动物学家的相关研究,褐家鼠的打洞深度一般为1米至1.5米,最深不过2米。由此来看,褐家鼠侵入阳陵外藏坑的概率极低。 至此,结合多方面考古发现,可以得出推论:阳陵外藏坑出土的2块褐家鼠骨骼所代表的个体,并非后期侵入,而是下葬时作为食材与其他动物一并放入的。由此我们认为,汉景帝生前有吃老鼠的食俗。 从历史研究角度来说,通过抽丝剥茧了解到汉景帝及其儿子儿媳等人(包括其他汉代人)都曾食用褐家鼠,这只是了解到汉代人的一种特殊饮食口味。不过,这个细节带给我们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理解与思考:最初考古发现阳陵老鼠骨骼,之所以首先判断老鼠并非随葬而是后来侵入,是因为今天的我们没有食用褐家鼠的习惯,大家知道食用这类老鼠有较大的健康危险,故而相关的考古推断也受到了这种现代认知的影响。最初的判断源自我们习惯性地用自身经验去推断2000年前的古人行为逻辑,这就是“以今度古”。我以为这个小故事更重要的意义,是唯有放弃成见才能有所发现、意识到“无知”才能获得新知,才能避免“以今度古”。 [ 简牍深处普通人留下的历史印记 ] 我们刚才说的是大人物的“常事”,在历史研究中,除了大人物的事迹之外,普通人留下的印记也值得重视。 不过,到哪里去寻找普通人的历史材料呢?研究晚近历史时相关材料很多,发现历史细节中的普通人身影相对容易。但是对于我研究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来说,要寻找对应时期的古代普通人材料就不容易了,我们需要借助20世纪以来的史料发现。 国内考古界有20世纪考古“四大发现”的说法,这源于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清华暑期学校的演讲,当时他提到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我今天要讲的是其中的汉晋简牍。 从1901年开始发现以来,汉晋简牍至今仍有新发现,是四大发现中的“常青树”。从数量上看,目前已发现30万枚汉晋简牍,未来可能还会增加。前几天浙江绍兴就出土了一些,以后其他地方或许还有新发现。 从地理上看,现在国内出土简牍的地点在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有分布:最南端在广东广州,西南地区云南有大量发现,北边在北京大葆台汉墓和通州副中心汉代潞城遗址的水井里均有出土,最东端是山东青岛黄岛的汉墓,最西端则在新疆,发现了很多批汉晋简牍。 从时间上看,简牍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最晚到公元4世纪的西晋与十六国时期,唐代简牍在新疆也有出土,前后跨越近千年。 从内容上看,简牍里既有《诗经》《尚书》《论语》《道德经》等古代典籍,也有秦汉时期的大量律令,数量更多的是行政文书。还有不少作为墓葬随葬品的简牍,这些简牍保留了众多古代小人物的历史印记,我们通过阅读简牍打捞他们的痕迹,发现他们生活的碎片,以便了解古代普通人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介绍汉代简牍中现身的两位小吏。 第一位叫师饶,我们通过墓葬出土的“名谒”获得了他的历史印记。在位于江苏东海县尹湾村的一座汉墓里,埋藏了很多木简和竹简,其中就出土了一枚名谒,相当于约2000年前的名片。名谒正面写着“进长安令”,表示这是要送给长安县令的;背面记录了送名谒者自己的职务和名字,左下角是他的姓氏和字。由此我们得知,他姓师名饶,字君兄,当时担任东海太守的功曹吏。东海郡位于今天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郡治在今天山东郯城县,师饶的家在今天江苏东海县,离郯城县不远。功曹吏主要负责管理人事,是非常重要的职务,属郡一级官员,是东海太守的亲信。 墓葬里除了名谒之外还出土了不少文书,其中一份叫《元延二年日记》,写在竹简上,大概有六七十枚,本身是西汉成帝元延二年的日历。师饶在这份日历的空白处记录了自己这一年的行踪,包括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住在哪里。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得知师饶在这一年因公出差80天,住的地方多为传舍和亭,其中住传舍的天数最多。这种情况,我们从很多类似资料里都有发现,当时的小吏经常出差,不仅去附近之地,还要去遥远的都城。比如刘邦起兵前就是秦吏,他曾从老家沛县出发去秦都咸阳。这正是秦汉时期郡县吏的常态。 师饶的日记多数只记录了出差日期和住宿地点,只有九月二十六日这一天记录了他的具体工作:“旦,逐贼,宿襄贲传舍。”这是说师饶这一天奉命去郯城县东北方向的襄贲县一带抓捕盗贼。当时,抓捕盗贼是地方官员的重要任务。按规定,如果盗贼出现三次以上未被抓到,地方官可能会因此被免职。师饶这次参与抓捕,当天却没能完成,随后他在襄贲县住了三四天才返回郡治郯城县,推测任务十分棘手。襄贲县距离郯城县不过25公里,这次任务却耗费多日,足见捕盗难度不小。现在我们在山东郯城县还能看到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县城城墙遗迹,当年师饶工作期间应该曾无数次出入这座城墙。 有日本学者根据师饶的日记,绘制过一张元延二年师饶郡外出差的行动地图:这一年他共外出六次,去过东北方向的琅琊国,也去过西南方向的楚国(楚国都城彭城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师饶曾经多次出差至彭城,且住宿天数亦多,最长一次住了将近20天,和楚王有很秘密的往来。遗憾的是,师饶在日记中并未记录他这期间具体做了什么,推测是在替郡守执行任务。按当时规定,郡守不能随便出辖境,所以他只能派亲信联络沟通,师饶就承担了这样的任务…… * 未完待续,原文稍长,两次分享,点击链接,一次收看:网页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