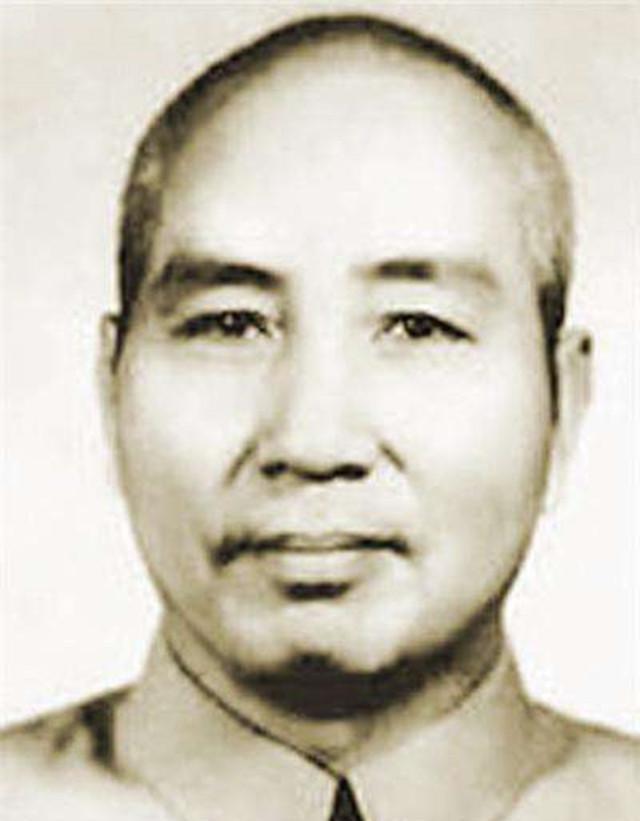1934年,地下党王同兴家里突然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臂缠毛巾、手提点心,这是说好的接头暗号。王同兴没起疑,中了特务的奸计。 敲门声在1934年的那个阴霾午后显得格外突兀,这不仅仅是打破了北京胡同里的宁静,更是直接撞进了地下党员王同兴那本就不安稳的睡梦中,作为一名掩护身份为书商、同时也被人戏称为“王胖子”的坚定战士,他对周遭的空气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 几天前同伴宋同发关于局势紧张的警告犹在耳畔,此刻门外那有节奏的叩击声,听起来像是一道催命符,又像是一场未知赌局的开场锣,门扉开启的瞬间,一场关于识别与反识别的暗战随即打响。 门外两名男子的装束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接头标准:手臂上缠着显眼的毛巾,手里提着礼节性的点心盒子,然而道具的完美无法掩盖“戏子”演技的拙劣,其中一个身形肥胖的来访者,刚跨过门槛,那一双眼珠子就在屋内四处乱转,目光黏在家具摆设上。 透出的不是同志相见的审慎,而是一股子令人作呕的贪婪,这种市侩气,与王同兴屋内堆满的进步书籍刊物格格不入,尽管对方嘴里说着“上级意思”、“有紧急情况”的切口,甚至搬出了陈仰贤的名字试图取信于人,但那种不仅没有风声预警。 反而甚至不允许主人思考的猴急模样,已经让王同兴那看似憨厚和煦的笑容背后,升起了一道冰冷的防线,即便心中疑云密布,王同兴手上的动作却没有丝毫迟滞,他深知在没有确凿证据前不能撕破脸。 一边热情地张罗着倒茶水,一边用身体语言掩饰着内心的盘算,他必须立刻要把这个异样的信号传递出去,找了个看似合理的借口溜出家门,王同兴直奔陈仰贤的住处,当他在角落里拉住那个袖口还沾满面粉、正在家里搓面团的汉子时。 那短短几句低语,瞬间让陈仰贤原本还在操持家务的轻松神情凝固成铁,两人不需要过多的 争执,眼神交汇间便定下了“将计就计”的策略,既然对方想演一出“瓮中捉鳖”,那他们不如就陪着演一场“金蝉脱壳”。 戏演到了高潮,特务们的耐心也消耗殆尽,在那两个冒牌货的推搡和催促下,王同兴、陈仰贤以及随后赶来的宋同发三人被塞进了一辆马车,向着所谓的目的地大名驶去,车轮滚滚,车厢内的空气沉闷得仿佛能拧出水来,阳光透过随着颠簸微微晃动的车窗帘缝隙。 在宋同发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就在他闭目养神、心中盘算对策的恍惚间,一道犹如实质的炙热目光穿透了车窗的阻隔,宋同发猛然睁眼,恰好看见窗外一匹快马疾驰而过,马上那身穿黑色大衣、戴着毡帽的身影是如此熟悉,正是真正的上级负责人王从吾。 这才是真正的接头,王从吾显然已经从王同兴那位焦急的老母亲口中得知了去向,一路抄近道狂奔而来,隔着马车晃动的窗口,王从吾并没有勒马停车,只是向着车内的同志打了一个噤声的急促手势,随后马鞭一扬,身影决绝地绕向前方路边的一处不起眼的茅草屋。 这无声的指令胜过千言万语,车内的三人瞬间读懂了其中的含义:那是一个坐标,也是一个信号,马车刚刚在茅草屋前停稳,那两个特务还沉浸在任务即将完成的喜悦中,幻想着将几人一网打尽。 殊不知,王同兴三人早已默契地交换了眼色,陈仰贤看似敷衍地回了一句“接手”三人动作整齐划一,在那电光火石的一瞬跳下马车,朝着王从吾指引的生路狂奔而去,等到负责押送的特务胖子反应过来冲进茅草屋时,留给他的只有四面漏风的空墙和一地狼藉。 夕阳下,那间空荡荡的茅草屋仿佛是对敌人最无声的嘲讽,意识到被彻底戏耍的特务气急败坏,将头上的帽子狠狠摔在地上,嘴里咒骂着那个永远抓不住的陈仰贤。 而在远处安全的角落,王同兴回望着那场未遂的阴谋,心中既对这群特务的愚蠢感到好笑,更对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无声配合感到由衷的激荡,在这条隐秘战线上决定生死的从来不是手臂上的那条毛巾,而是彼此灵魂深处从未动摇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