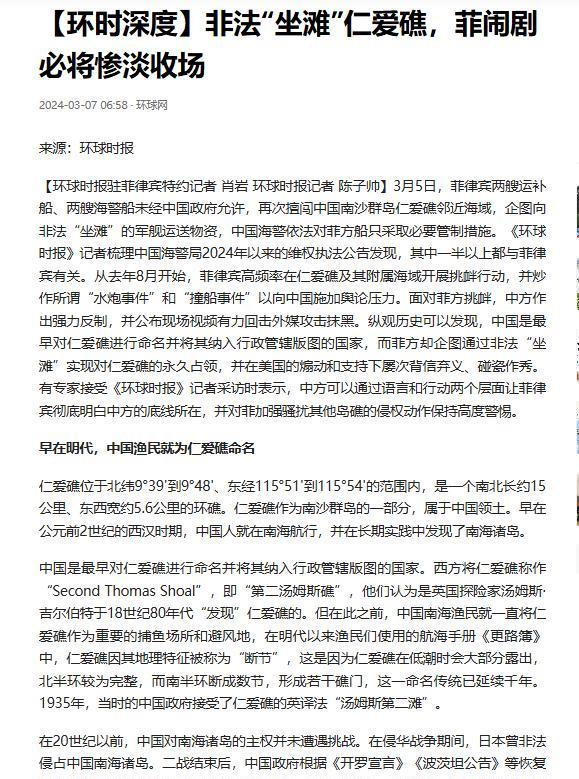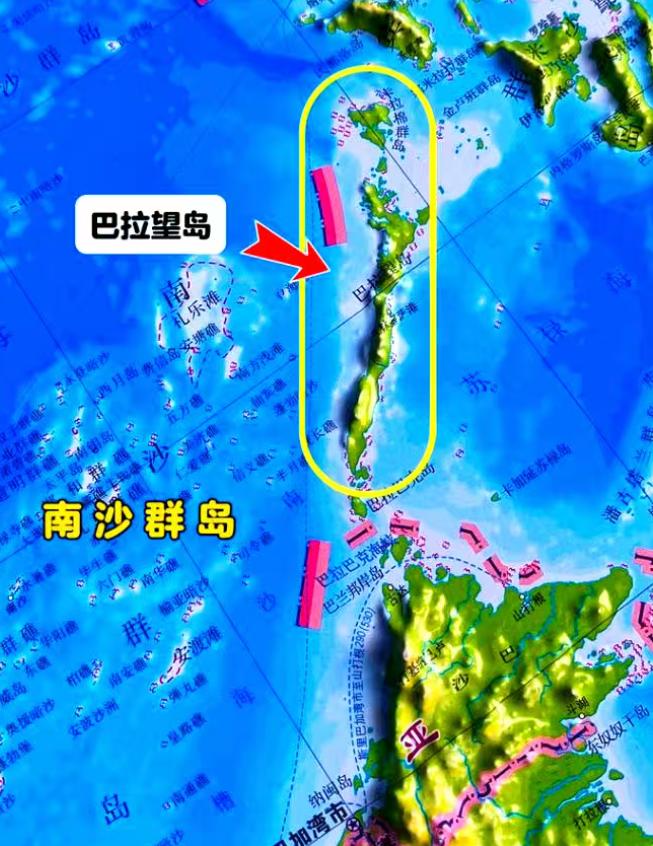菲律宾五万“无父娃”的寻亲路:照片里的爸爸,海那边的陌生人 马尼拉的贫民窟里,12岁的阿明攥着一张泛黄的合影,指尖反复摩挲着照片里年轻男子的脸。“妈妈说这是爸爸,他回韩国了,会来接我们。”可直到母亲病逝,他也没等到那句承诺。在菲律宾,像阿明这样的孩子有五万名,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Kopino”,特指韩国父亲与菲律宾母亲的非婚生子女,也成了“被遗弃”的隐秘代号。 这场横跨南海的情感缺席,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说起。当时,英语培训经历成了韩国就业的“硬通货”,费用低廉的菲律宾成了理想选择。一批批30至40岁的韩国男性涌入这里,在语言研修或短暂经商的日子里,与十几岁、二十多岁的当地女性产生交集。当爱情褪去或意外降临,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用最决绝的方式退场:收拾行囊返回韩国,拉黑联系方式,将怀孕的伴侣和尚未出世的孩子彻底从人生中删除 。 这些“跑路爸爸”的逃离手段,藏着令人心寒的算计。有人同居时刻意隐瞒护照号码和韩国手机号,让后续寻找无从下手;更有甚者,在菲律宾语言研修期间生子后,竟谎称自己来自朝鲜平壤,用一个荒诞的谎言切断所有追溯可能 。17岁就生下孩子的菲律宾母亲莉娜回忆,孩子生父离开时只留下一句“我会回来”,可转身就成了永远的失联者。她独自打三份工,仍凑不齐孩子的学费,“他或许在韩国有了新家庭,早忘了我们娘俩”。 最刺痛人心的,是生命在漠视中流逝的重量。韩国公益人具本昌永远记得那个哭泣的菲律宾母亲:她1岁多的韩菲混血女儿因没钱医治夭折,而孩子的韩国父亲离开时,只留下一张写着“韩国、18岁、你信吗?”的轻佻字条,字里行间全是挑衅与敷衍 。这个瞬间,让原本聚焦韩国国内抚养费问题的具本昌,将目光投向了菲律宾这片被遗忘的角落。 公开照片,成了这场跨国寻亲最后的破局之道。从2025年10月开始,具本昌在社交媒体上接连发布寻亲启事,附上混血儿与韩国生父的照片,直白标注“寻找2010年出生女儿的爸爸”“寻找2014年出生儿子的爸爸”,并掷地有声地宣告:“即使构成名誉损害也不会退缩” 。这不是冲动之举——在公开前,他的团队会彻底调查情况、听取双方陈述,甚至提前警告当事人,确保名单上没有真正陷入经济困境的父亲 。 舆论的阳光,终于照进了隐秘的角落。11月,一名菲律宾母亲突然收到失联7年的孩子父亲的消息,对方语气慌张地询问孩子近况。具本昌陆续接到类似反馈:那些多年杳无音信的“坏爸爸”们,在照片可能曝光的压力下,开始主动现身 。可这份迟来的联系,终究难掩过往的亏欠。阿明的邻居、17岁的玛丽安,看着母亲手机里陌生男人的问候信息,轻声问:“现在才来问,当初为什么要走?” 具本昌的行动始终伴随着争议,私信里的质疑从未停歇:“这不是侵犯隐私和诽谤吗?”他并非没有顾虑,毕竟2024年1月,他就因公开拖欠抚养费者信息被判缓刑并处罚金100万韩元。但咨询律师后,他选择坚持:“当孩子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时,逃避责任的人没资格谈隐私” 。这份坚持背后,是五万孩子的生存困境——他们大多生活在贫困线边缘,无法接受良好教育,在身份认同的迷茫中挣扎,成为跨国责任缺失的牺牲品 。 如今,马尼拉的街头仍能看见单亲妈妈们抱着孩子,翻看手机里具本昌发布的寻亲动态。那些被公开的照片里,有的父亲笑容灿烂,有的眼神闪躲,而照片旁的混血儿们,眼神里满是对“爸爸”二字的懵懂渴望。这场用照片铺就的寻亲路,或许能追回部分抚养费,却难以填补孩子成长中父爱的空白。 南海的风年复一年吹过菲律宾的海岸,带走了“跑路爸爸”的踪迹,却带不走五万孩子的牵挂。当具本昌的手指再次按下发布键,屏幕上的照片不仅是寻亲的凭证,更是对每一个缺位父亲的追问:跨越国界的距离,真的能隔断血脉里的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