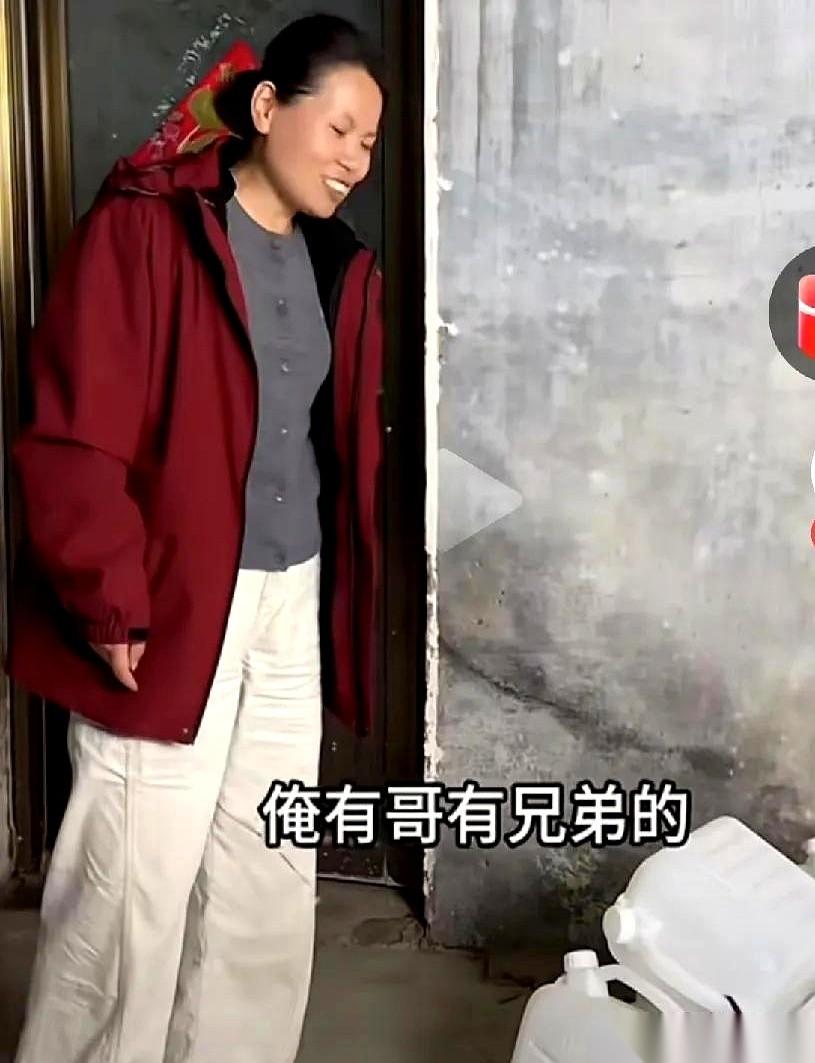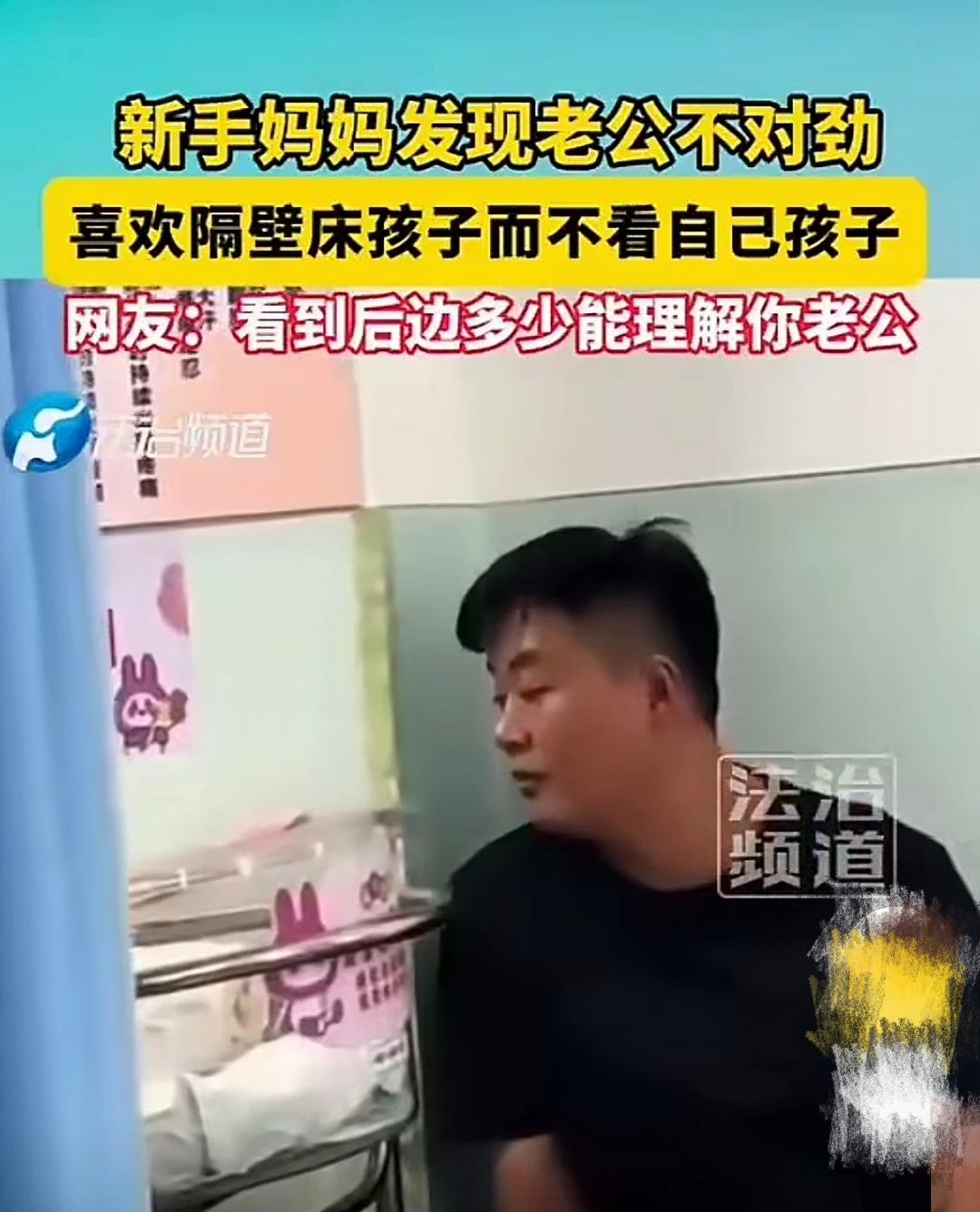家的盛宴 城市里,黄昏的灯光次第亮起,我踏着暮色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一股混杂着油烟与炖肉香气的暖流扑面而来,瞬间裹住了周身。厨房里,母亲系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围裙,正弯腰查看砂锅里的汤汁;父亲在一旁笨拙地剥着蒜,眼镜滑到了鼻尖。这画面二十年如一日,却又每次都能让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之一颤。 我常想,中国家宴的炊烟,是从《诗经》时代便袅袅升起的。“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古人储备美味以度寒冬,亦以御生活的荒芜。而今我们围坐分食,何尝不是以一种温热的方式,抵抗着世间的寒凉与疏离?那炖锅中翻滚的,何止是肉块与香料,更是千年以来未曾断绝的人间烟火气。 幼时只知馋那口吃食,眼睛盯着糖醋排骨滴溜溜转。长大后,才渐渐品出宴席之外的滋味。姑姑总会带来她亲手腌的咸菜,装在老旧的玻璃罐里,口上封着红布。她嘴上说着“不值钱的东西”,眼神里却藏着怕被嫌弃的忐忑。而无论大家尝过后的一句“还是那个味”,便能让她眉宇舒展,仿佛一年辛劳皆得了报偿。一罐咸菜,竟比许多贵重礼物更见情意,因它里面腌着的是时间、是手艺、更是一份“把你放在心上”的郑重。 杯盘狼藉时,话题便开始真正活色生香。不再拘泥于学业工作,转而复活家族的记忆。叔叔三杯下肚,又会讲起祖父当年如何用一辆破自行车驮着全家过年货的故事,那路上的冰辙与喘息,已被岁月镀上了金色的光辉。小辈们托腮听着,仿佛在接收一种无形的族谱密码。这些絮叨,平日里散落在电话两端,唯有借着饭桌的热气才能重新聚拢、拼接,让一代代人的面目在言谈中渐渐清晰。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临别时,母亲照例要塞满每个人的手提袋——冻好的饺子、新熬的酱、洗净的水果。我们总推说太重,她却执意要给,仿佛这些食物能代替她,继续滋养她牵挂的儿女。于是我们带着沉甸甸的包裹离去,也带着一身油烟味融入地铁人潮。这气味久久不散,竟成了乡愁最具体的气味标签。 原来,中国人家庭聚餐的真味,从来不在菜式的丰俭,而在于那顿饭是一个锚点,稳稳定住了漂泊的人心。它让我们确信,无论世间风雨如何,总有一盏灯、一桌饭、一群人,在等待你的归来。那由食物蒸腾起的,是一个民族最深处的温暖与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