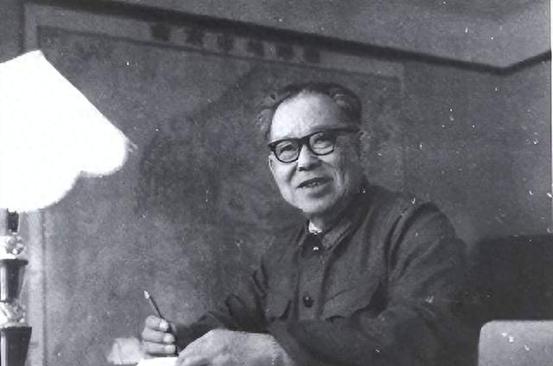上级派他负责上海地方工作,大军区政委陪同,警卫荷枪实弹护送 “1976年10月9日清晨,专机刚拉起机头,苏振华低声对身旁的廖汉生说:‘老廖,咱们这趟,可不能出半点岔子。’”一句话,把机舱里的气氛瞬间收紧。彼时距离“粉碎四人帮”不过数日,上海这座繁忙的城市暗流翻滚,中央决定临时抽调苏振华坐镇。苏是海军政委,资历深厚;廖是南京军区政委,熟悉华东局势。两人加起来,足够压住场面,却也清楚,任何闪失都将牵动全国目光。 飞机下降时,虹桥机场外围警卫线一层又一层,海军警卫营全副武装。跑道尽头,装甲车静置,发动机未熄。防备如此严密,只因前车之鉴太多。几天前,上海民兵指挥部还执行一级戒备,随时听命于马天水、徐景贤等原市领导。中央决心先稳军心再稳民心,才会让苏振华以“临时负责人”身份秘密抵沪,待机而动。 抵达当晚,苏振华并未直奔市委,而是拐进海军上海基地司令部。这里戒备森严,更重要的是通讯安全。凌晨两点,基地地下会议室灯火通明,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中央工作组首批骨干汇聚。地图铺满整张桌子,红蓝标记密密麻麻:要害桥梁、电台、中型工厂、重要仓库,统统标了三遍。廖汉生把手指敲在“第二武装”可能聚集区,“万一有变,先切断他们的交通和电讯。”苏振华点头,只留一句:“行动要快,声音要小。” 10日拂晓,60军和第一军两个师以“野营拉练”名义逼近沪闵结合部,兵不血刃占据外围高地。市区里,军代表悄悄进驻二十多家重点工厂和码头。老工人私下嘀咕:“怎么又来了?”却没人敢造次。紧接着,中央第二批工作组一百八十余人分散进场,倪志福拄着拐杖坚持坐镇机床一厂,他的哮喘在潮湿空气里喘个不停。有人劝他回宾馆休息,他摆摆手:“要干就干到底。” 与此同时,彭冲在南京指挥后方协调。江苏省委原本离不开他,此刻也只能全力配合。丁盛、周纯麟负责盯牢警备区,防止前市委旧部调动仓库枪械。几条线同时推进——军队包外围,民兵受控,中央干部接管行政系统,上海这部复杂机器逐步停转再重启。 有意思的是,基层并非人人抵抗。造船厂老技师盯着生产线对工人喊:“趁外面乱,咱可别把船期给耽误。”外贸口岸急需交船,不敢出纰漏。苏振华抓住这一点,强调“恢复生产”是硬指标。三天后,全市主要国营企业开工率已回升到七成,外电报道“不寻常的平静”,算是给中央吃了颗定心丸。 城市局势稳住后,政治工作才轮到台前。揭批、整组、清查档案……流程严格却不拖泥带水。苏振华对干部说,“先把框架立住,再谈思想问题。”这句干脆的话赢得不少共识,也减少了无谓口号。遗憾的是,倪志福病情恶化,不得不回京治疗,但手里的技术细节仍通过加密电报每天报来。 十月中旬,中央批准成立上海市委新的核心班子。苏振华任第一书记,彭冲、倪志福分列其后。知情者都明白,这是维稳时期的过渡架构,任务完成即撤。上海方面没有公开庆祝,却通过工会系统向全市发出一纸通告:交通、粮油、电力一切正常,市民可照常生产生活。街头巷尾议论不断,但秩序稳稳当当,再无风浪。 19日夜,廖汉生接到返宁命令。奔波半月,他确实疲惫。回程途中,专车驶过嘉定,锣鼓声忽远忽近。车厢里没人说话,只有心照不宣的松口气。军区司令部随后撤回额外警卫力量,民兵指挥部降为二级戒备,上海恢复常态指日可待。 11月初,中央对全国局势作最后梳理,苏振华完成阶段任务,返回海军。离开时,他只带走自己那只褪色行李箱。机场送行人员不多,场面低调得像普通公务出差。有人问他感想,他摆手道:“上海的事,算解决了,但全国还得接着干。”随后转身登机,没有回头。 此后数年,上海工业数据逐季回升。“一破一立”留下的裂缝,靠制度和生产慢慢填补。那场荷枪实弹护送的行动,被归入绝密档案,直到多年后才零星公开。外界看见的,只是一座城市在风口浪尖的短暂停顿和随即复苏,而幕后那一连串周密调度、硬碰硬的对峙与谈判,却很少有人能完整讲述。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军政系统积累的“应急方案”在这座城市得到最大限度的验证。军事力量、政治权威、工人阶层的生产积极性三条线合流,构成稳局的铁三角。倘若缺一角,上海很可能走向另一种结果。试想一下,若非苏振华与廖汉生及时到位、一环扣一环部署,谁能保证港口、金融、粮仓不会成为谈判筹码?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可被忽视的细节依旧值得记住:机场巡逻兵的弹匣是真实装满的,60军步兵真的野营在松江稻田边,工厂大喇叭里循环播放的“抓革命、促生产”广播带也的确断了磁带。正是这些细节,拼凑出1976年十月的上海全景。 临危受命者已经离场,街市烟火又起。行动代号、警卫方案、空中航线都被锁进档案柜。文件字迹仍旧鲜亮,只提醒后来者——当年那趟专机的引擎声,意味着中央意志,也意味着一旦失灵,将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