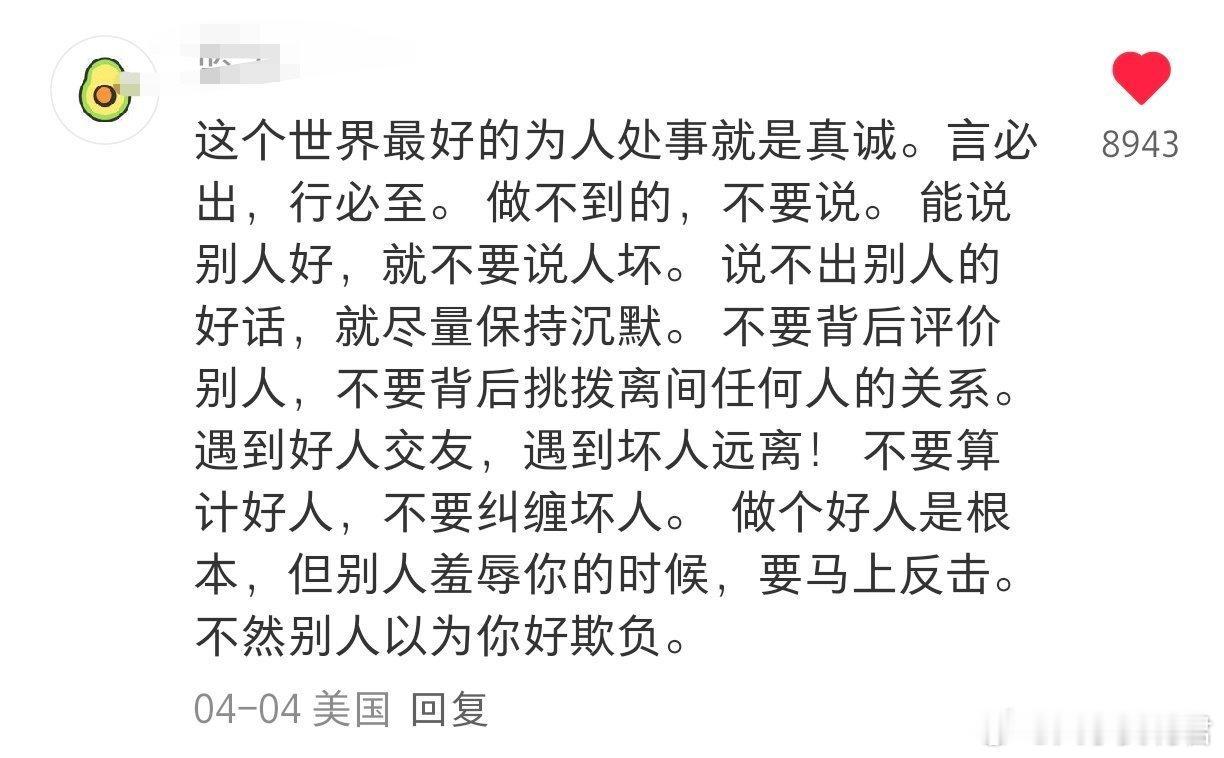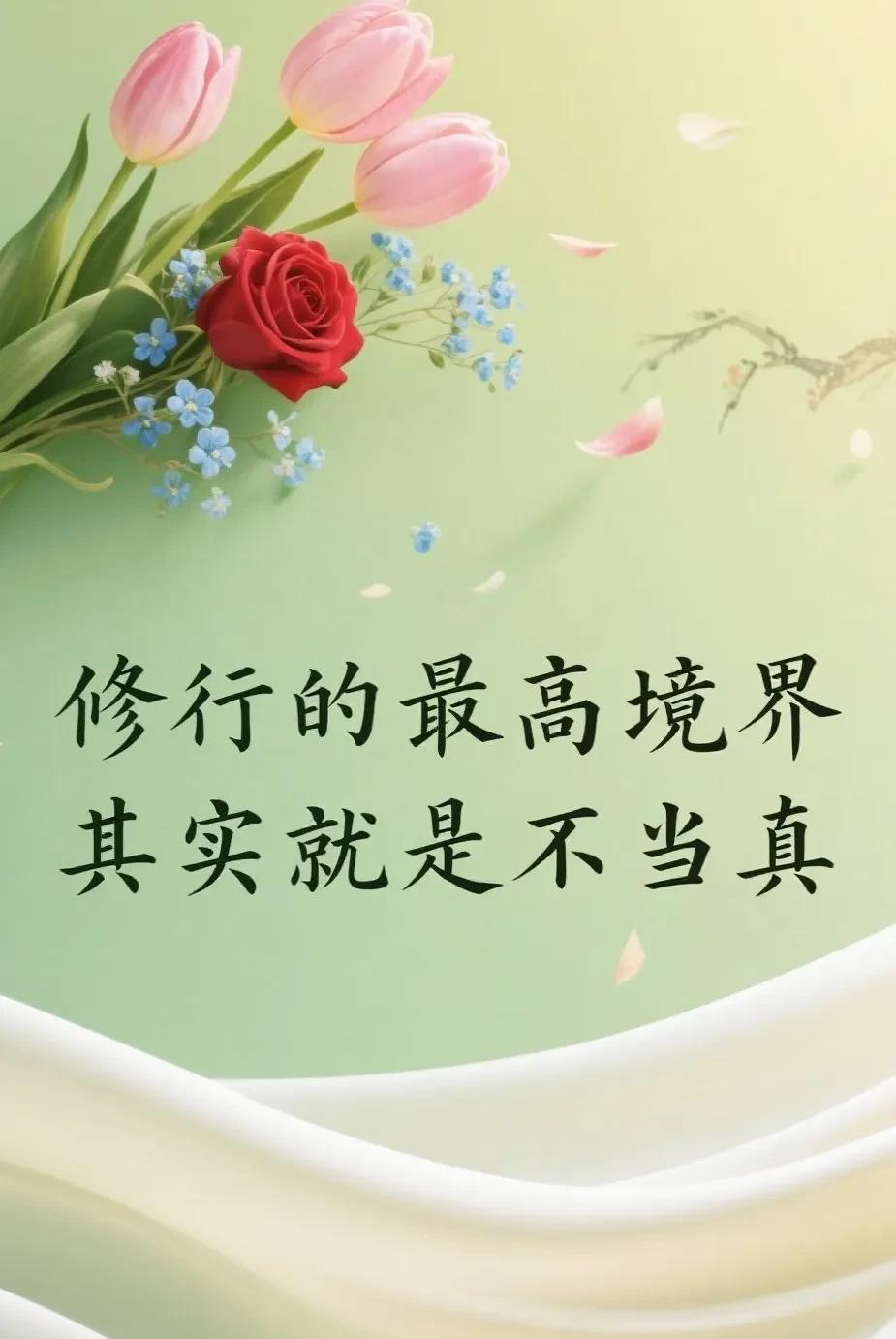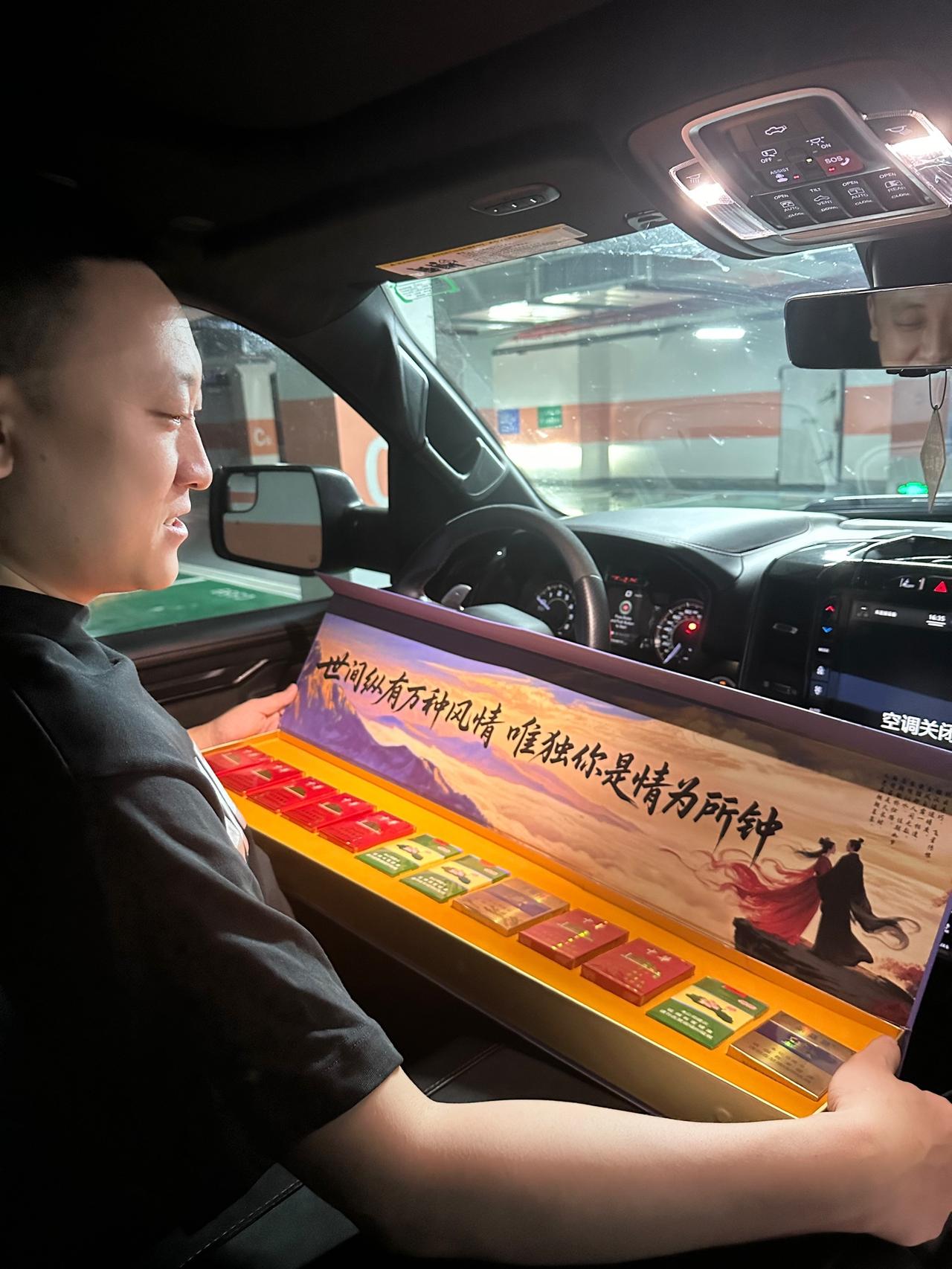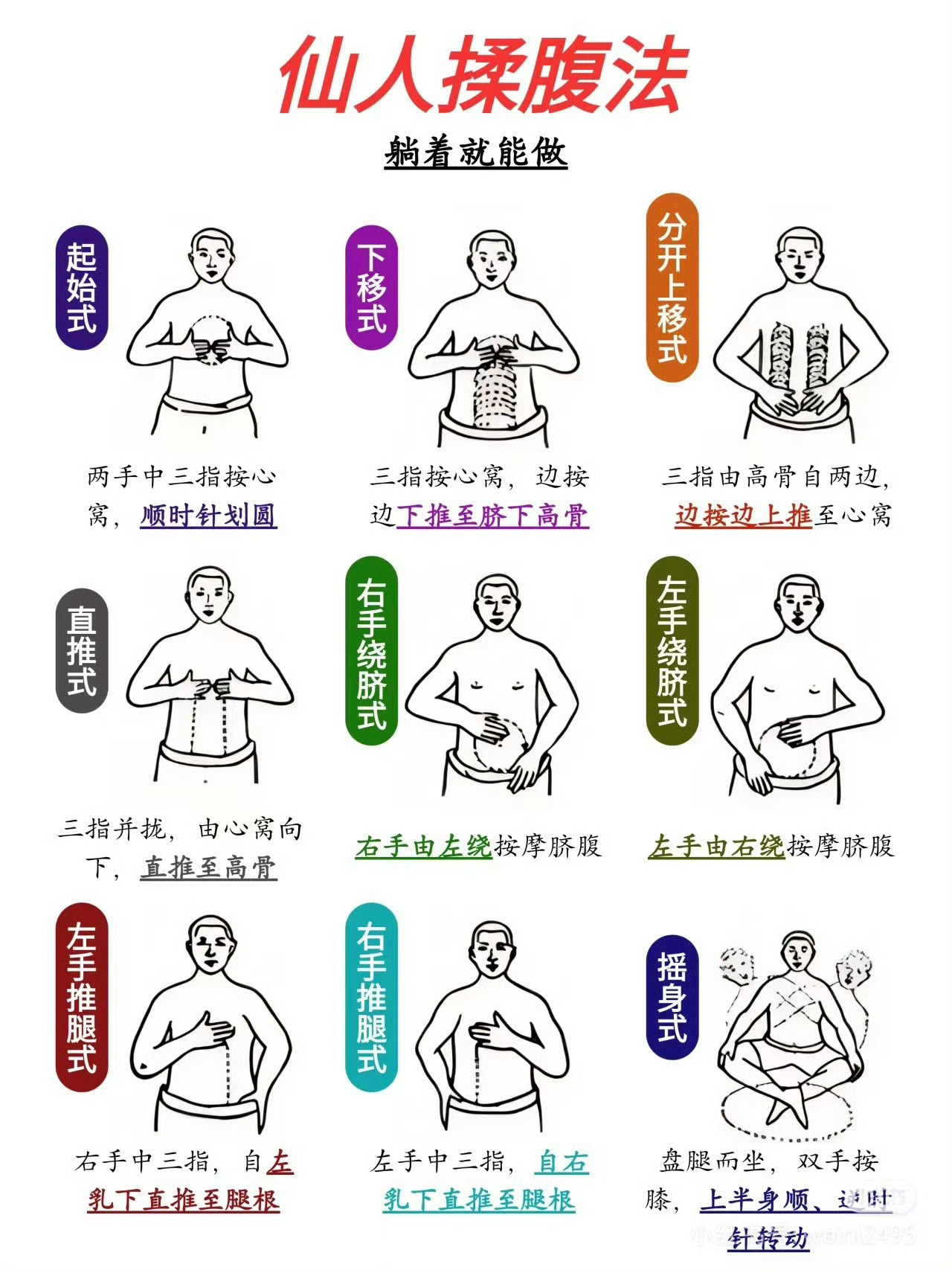当我们在诗词里读到“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雅致,在戏文里看惯“秦淮八艳”的风华,或许很容易被那些朦胧的诗意包裹——仿佛烟柳画桥边的女子,生来就该是风月场里的点缀,用笑语盈盈承接文人墨客的笔墨。
可掀开这层温柔的面纱,底下藏着的,是无数少女被碾碎的人生。她们中,有的本是书香门第的女儿,只因家道中落被辗转贩卖;有的是农家女娃,一场天灾人祸后,便被亲人“换”了几担米粮;更有甚者,自小被拐卖,连自己的名字、故乡都记不清,只知道进了这朱门高墙,就再也不是“闺中少女”,而是任人挑选的“商品”。
白日里,她们要学琴棋书画、唱曲儿跳舞,不是为了怡情,而是为了让自己“值个好价钱”;夜幕降临,醉醺醺的客人推门而入,不管愿不愿意,都得强撑着笑意斟酒、陪聊,稍有不慎便是呵斥与打骂。她们的身体不是自己的——染上风寒要接客,月事来了要接客,甚至被醉酒的人推搡受伤,第二天依旧要描上浓妆,装作无事发生。
有人说“她们能赚银钱,比农家妇好过”,可那些银钱,大多进了老鸨的腰包,她们能留的,或许只够买些劣质的胭脂,或是偷偷攒下几文钱,盼着有朝一日能“赎身”。可这盼望,往往是镜花水月:要么攒够了钱,却被老鸨耍赖扣下;要么遇上“有情郎”许了承诺,最后却被当成玩物抛弃。更多的人,在日复一日的消磨里,二十出头的年纪,就已被掏空了精气神——双手粗糙,眼角爬满细纹,咳嗽时带着血丝,看上去比田间劳作的老妇还要憔悴。
她们也曾有过少女的憧憬吧?或许在某个清晨,偷偷对着镜子梳发时,也想过若能像寻常女子那样,嫁个庄稼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许在听客人说起家乡的桃花时,也会想起自己模糊记忆里,院墙边那棵开得热闹的树。可这憧憬,终究被淹没在夜夜的笙歌与醉语里,直到生命被榨干,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残叶,悄无声息地埋在乱葬岗,连块刻着名字的墓碑都没有。
我们读历史,不该只记得“红袖添香”的浪漫。那些被遗忘在风月场里的女子,她们的眼泪、挣扎与不甘,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她们不是诗词里的符号,不是戏文里的背景,是曾真实活过、痛过的人。记住她们的命运,或许也是在提醒:每一份“雅致”的背后,都不该有被牺牲的个体;每一种“风情”的描绘,都该多一份对生命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