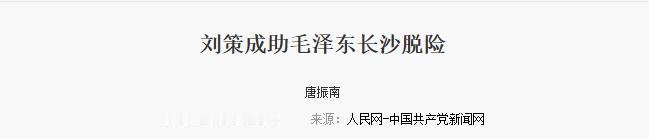一个国民党的老警察厅长,到了68岁,还给伟人写信求工作。信里没拐弯抹角,直接说“我实在找不到门路了,只好来找你”。伟人原本最不喜欢这种事,尤其是打着“老关系”的旗号来办私事的。但这一次,他看完信后,沉默了几秒,最后却说了一句话:“把这事办妥,满足他一切要求。” 1951年,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内,一封来自湖南的信放在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信封朴素,寄信人一栏写着“刘策成”。 警卫员瞥见,认为又是哪位“老乡”来请托安排工作。 然而,当毛泽东看到那熟悉的名字上时,却立马拆开信封。 内容十分直白:“我工作的事还没着落,只能来北京找您帮忙!” 这近乎“讨官”的信,若出自他人,定会引来不悦。 但毛泽东看完,竟写下了“同意”。 警卫员难以置信的看着这位最忌讳“老关系”请托的主席,竟为了一封如此直白的信破了例? 那么,主席究竟与他又有着怎样的经历? 1923年,长沙城笼罩在军阀赵恒惕的白色恐怖之下。 时任湖南省长的赵恒惕,对积极推动“湖南自治”、撰文揭露其独裁野心的毛泽东恨之入骨,密令抓捕。 这份密令,很快落在了省会警察厅长刘策成的案头。 刘策成,是赵恒惕的姻亲,此刻却如坐针毡。 他并非寻常官僚,早年留学日本时便追随孙中山、黄兴加入同盟会。 在邵阳驻省中学当校长时,曾因密谋反袁而入死牢,幸得蔡锷搭救。 后执教湖南第一师范,与青年毛泽东结下深厚师生情谊。 他欣赏毛泽东的卓绝见识,常私下赞叹他有“治世之能”。 此刻,要他亲手抓捕自己寄予厚望的学生,这怎么能下得了手? 但是,军令他却不得不执行。 散会后,他密召亲信王建屏:“务必抢在军警大规模行动前,连夜通知毛泽东火速撤离长沙!” 王建屏领命,趁夜色潜入毛泽东栖身的清水塘小院。 一张写着“三更天出城,走南门!”的纸条,塞入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警觉,当即收拾行装,匆匆撤离。 几乎同时,刘策成亲命王建屏带队包围了清水塘,上演了一出“追捕未果”的戏码。 第二天,赵恒惕得知没抓到人,生气得很,斥骂手下无能,却不知正是他最信任的警察厅长放走了“要犯”。 风声鹤唳中,刘策成自身亦险象环生。 一次,赵恒惕亲信在他书房发现藏匿的《新青年》杂志,开始怀疑她通共。 危急关头,刘夫人急中生智,将杂志投入灶膛焚毁,谎称佣人所藏,方得险险过关。 此事在长沙官场悄然流传,刘策成“家藏革命火种”的名声不胫而走。 刘策成对毛泽东的襄助,远不止于一次救命之恩。 早在1920年他任衡山县长时,便已与毛泽东结下书缘。 彼时毛泽东筹划创办文化书社,传播新思想,却资金不够。 刘策成闻讯,毫不犹豫地变卖了祖传玉佩和妻子的嫁妆首饰,凑足三百块大洋,送至毛泽东手中。 这笔巨款,相当于他当时两年多的薪俸。 书社开张之日,刘策成微服前往,见书架上赫然陈列着《共产党宣言》等禁书,非但未以警察厅长身份查禁,反而自掏腰包购下十本。 此举自然招致赵恒惕的震怒,大骂其“警察厅长带头看禁书”。 书社盈利后,毛泽东想还钱,刘策成却拒绝:“我若图利,当初何须变卖传家之物?” 这份基于共同理想的书香情谊,早已超越了寻常师生。 时光荏苒,1949年新中国诞生。 远在湖南乡间的刘策成,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 得知毛泽东当选国家主席,他激动难抑:“我早知润之有治世之才!” 欣喜之余,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这位埋首书斋、潜心研究《庄子》多年的老书生,想到自己能否为毕生所学觅一用武之地? 而他并非贪图权位,而是渴望一个能查阅典籍、安心著述的环境。 几经踌躇,他终于向中南海发出了那封直白的信。 毛泽东“同意”后迅速落实,湖南省政府安排刘策成担任省参事室参事。 然而,参事室的频繁会议,与刘策成的夙愿相去甚远。 一次会议间隙,他竟忍不住在记录本上抄录起《庄子》笔记。 老人深感时日无多,于是再次提笔致信毛泽东。 “我不要当官,只求一安静书桌!” 这近乎“拒官”的二次请求,再次考验着中南海的耐心。 毛泽东闻讯,想起了当年书社旧事,对老师一生痴迷学问的性情了然于心。 他再次批示:“特批入中央文史研究馆!” 并特别嘱咐:“从我稿费中拨款,为老先生租赁一处安静院落,便于研究。” 此等破格礼遇,实属罕见。 1951年6月,一纸盖有国徽印章的红色聘书送达刘策成手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老人双手捧着聘书,老泪纵横。 他即刻整理毕生心血,二十箱书稿,举家迁往北京。 在毛泽东稿费支持的院落中,刘策成心无旁骛,继续《庄子》研究。 数年后,凝聚其毕生心血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付梓出版。 更令人惊叹的是,毛泽东亲笔为恩师著作题词。 这部引证浩繁、考据精详的学术专著,一经问世便震动学界!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刘策成助毛泽东长沙脱险;新湖南——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刘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