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张铁生从兴城县初中毕业后,响应号召到枣山大队插队,因表现出色,他被选为生产队小队长,1973年,他获得了宝贵的大学招生考试机会,也由此走上了人生的新轨迹。
1973年夏天,张铁生坐在辽宁兴城的一间考场里,望着眼前的理化试卷发了愣,那一年,他已经23岁,裤腿上还残留着田间干活时溅上的泥点,考试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是一道通往未来的门槛,对他而言,却像一堵墙,他不是不想考好,而是实在没时间复习,作为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的生产队长,这个春天他刚和社员们熬过一场抗旱保苗的苦战,白天带人干活,晚上还要照看牲口,书本离他的生活实在太远。 那一天,他在试卷上写下的不是答案,而是一封信,他在试卷背面写给“尊敬的领导”,讲述自己身处农村的真实生活,说明自己缺乏学习条件,也表达了对当时招生方式的一些疑虑,他没有求情,也没有抱怨,而是把心里的想法写了出来,试卷交上去之后,他照常回到田里干活,没想到,这封信很快被媒体报道,引发强烈反响。 那一年,张铁生被录取进入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很多人记住了他是因为那张“白卷”,但他进入大学后并没有因此自满,在学院里,他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也积极参与各类实践活动,他加入了党组织,组织学习小组,还下乡为农民治病培训赤脚兽医,短短两年时间,他从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成长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委,并在学院担任领导职务。 张铁生的上升速度令人咋舌,1975年,他才24岁,就已经坐到了全国人大常委的位置,一年之后,他还作为代表在各地做教育工作的汇报,彼时的他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似乎未来一片光明,然而,风向很快变了,1976年10月以后,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他的命运也发生了急转直下,不久,他被撤除所有职务,开除党籍,后来因被定罪入狱服刑。 这一关就是15年,从人大常委到阶下囚,这样的转变不仅是身份的跌落,更是精神的冲击,1991年10月,张铁生走出高墙时,已经41岁,他错过了整个八十年代,那是中国社会最剧烈变化的时期,他不知道BP机为何物,也不明白“大哥大”是干什么的,时代没为他停下脚步,他却要重新找回节奏。 出狱后,他面临的不只是身份的标签,还有找工作时的重重障碍,那个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阵痛期,下岗潮波及千万人,一个与社会脱节多年、又带着犯罪记录的人,想重新开始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并没有放弃。 在大学时的老同学董礼平的帮助下,张铁生重新站了起来,董礼平不仅在他出狱时亲自接他回家,还与他结为夫妻,两人结婚那年,是张铁生最艰难也是最温暖的一年,这段感情没有轰轰烈烈,却是他人生中最坚实的依靠。 他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在辽河饲料公司沈阳办事处负责采购和联络,后来,在朋友金卫东的支持下,他和几位合伙人共同投资创办了天地饲料厂,起步阶段并不轻松,但他凭借对农村和畜牧行业的了解,在市场中一步步站稳了脚跟,到1995年,天地饲料厂已经在沈阳市场打出了名气。 1998年初,天地饲料并入了新成立的禾丰牧业,张铁生持股成为企业股东,负责企业的商务及外联事务,他不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市场经济中的一员,企业逐步壮大,业务扩展到饲料、肉禽一体化以及国际贸易,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默默做好份内的事情。 2003年,禾丰牧业完成股份制改革,企业发展迈入新阶段,张铁生作为创始股东之一,继续在公司担任监事会主席,2014年,公司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他持有的股份价值达到数亿元,成为拥有财富和实力的企业家。 张铁生的故事,不只是“白卷英雄”或“政治起落”的标签所能概括,他的前半生仿佛一场过山车,从普通农民到国家领导机构,再到铁窗之中,跌宕起伏,令人唏嘘,但他的后半生,却是一段重建自我、拥抱现实的旅程,他用实际行动证明,即使曾经跌倒,也可以在另一个领域重新站起来。 他没有在失败中沉沦,也没有躲避曾经的过往,他选择从头再来,哪怕步履维艰,他没有什么华丽的语言,也不善于表达情绪,但他用每一次选择,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答卷,这份答卷没有评分标准,也没有主考官,但它比任何一次考试都更真实、更厚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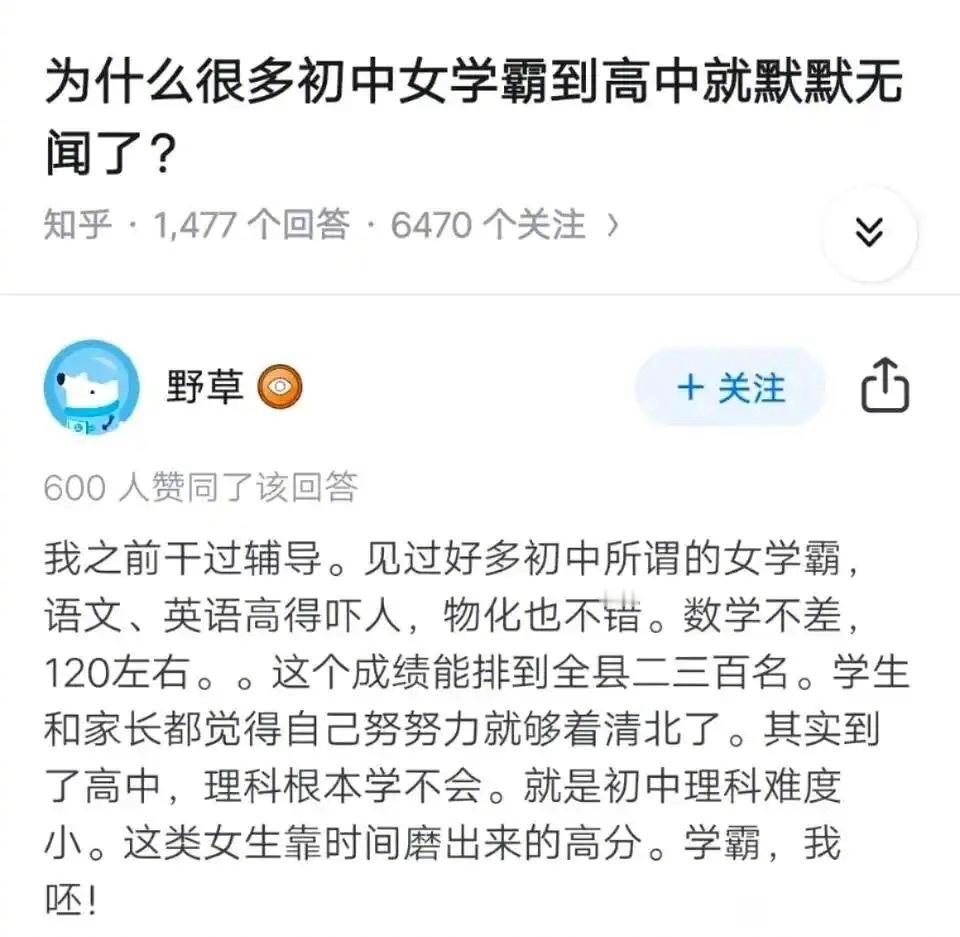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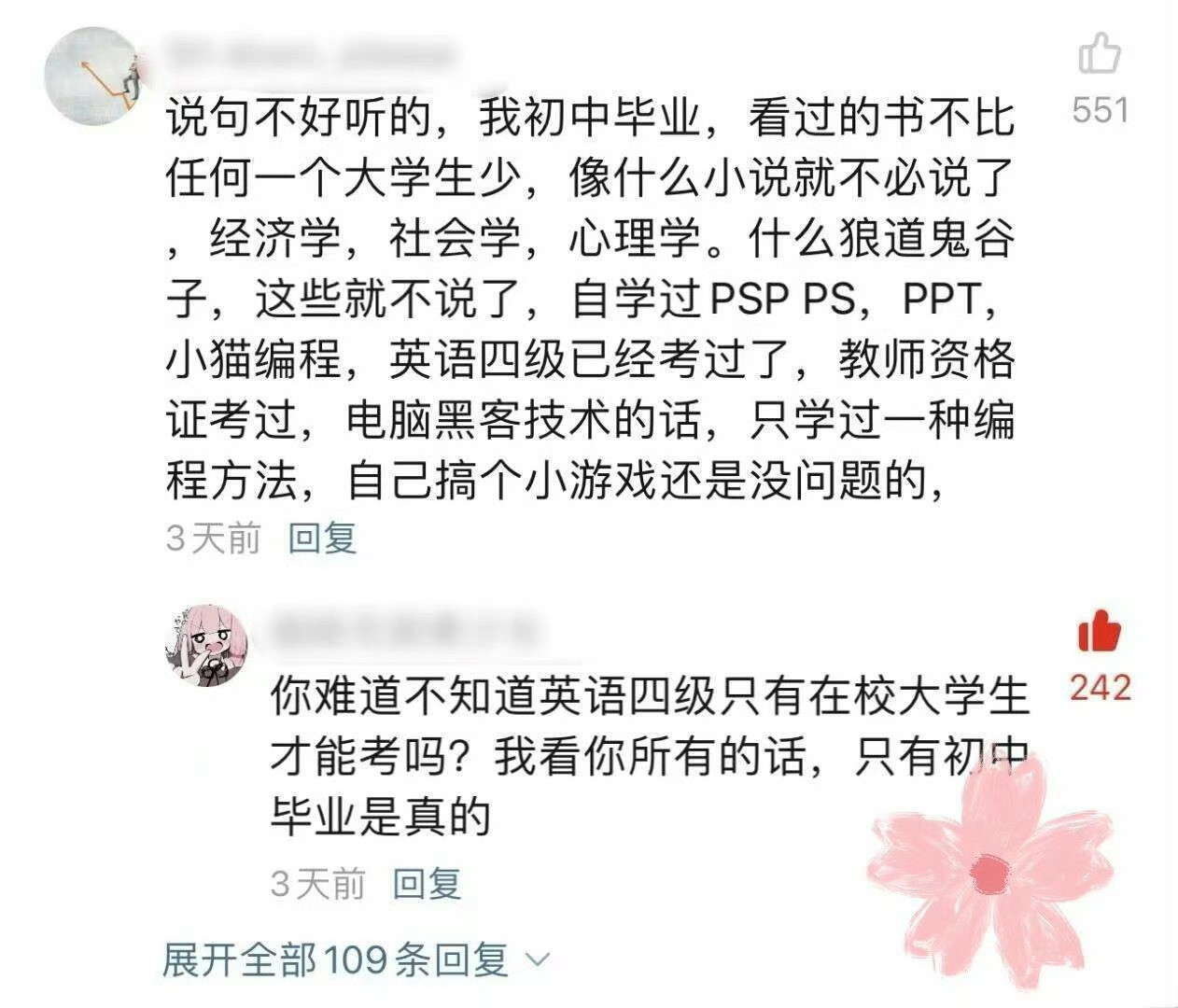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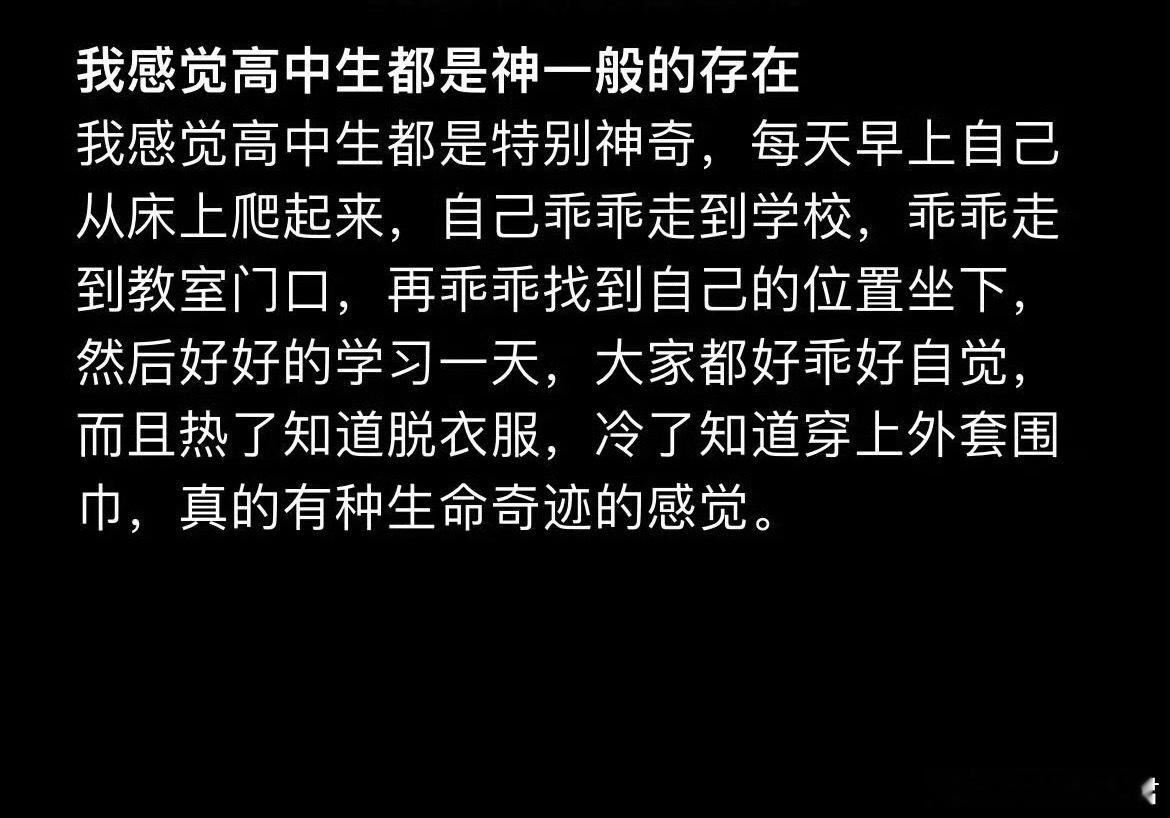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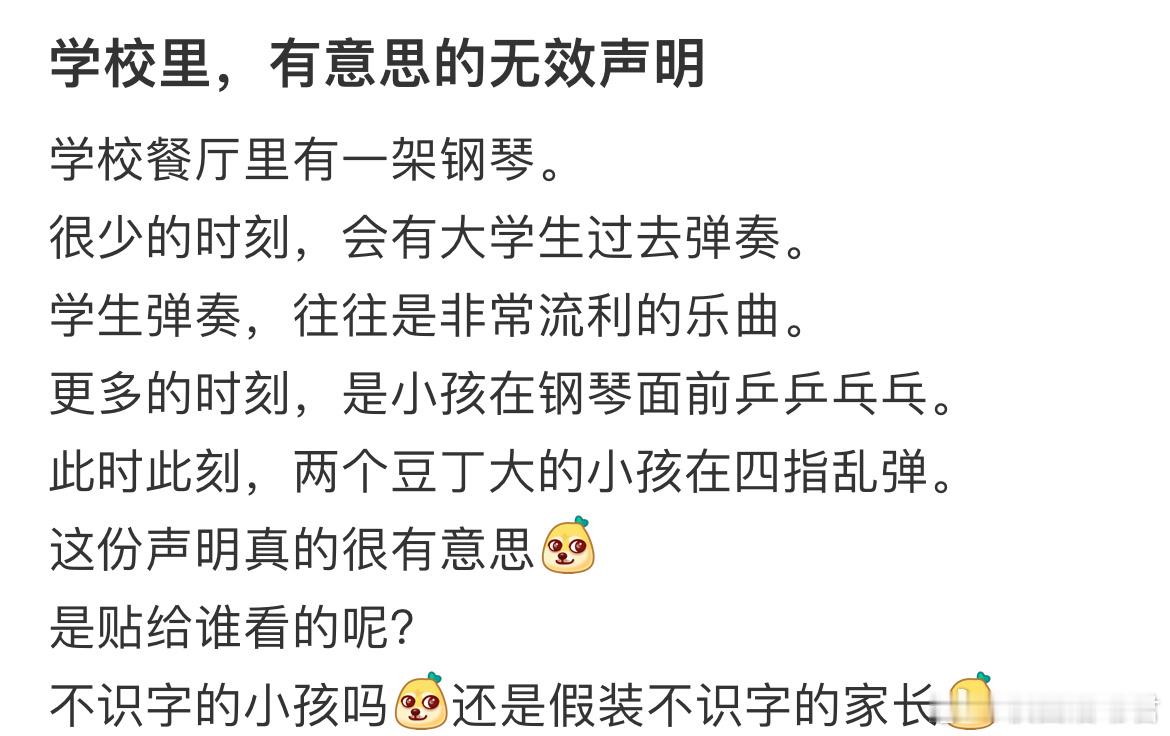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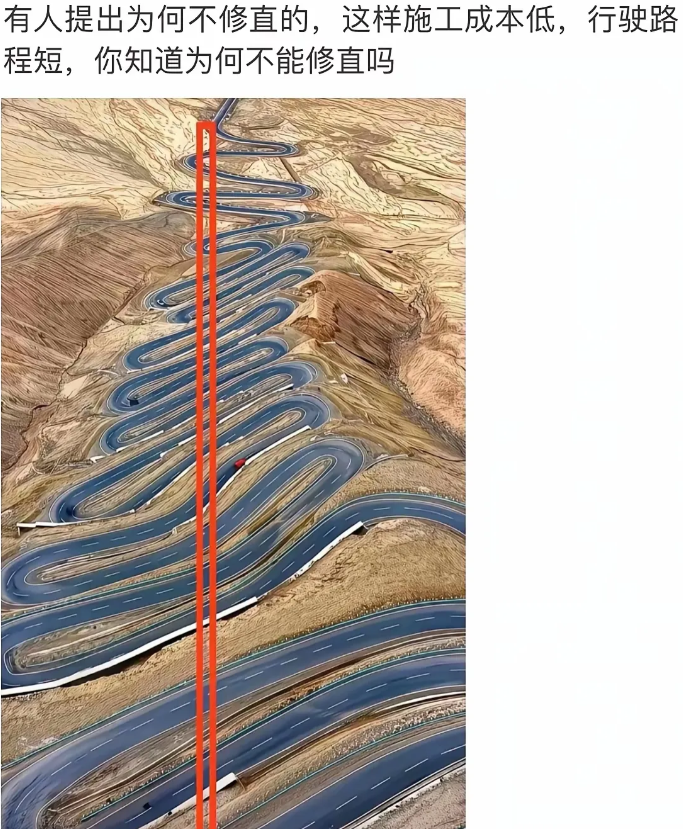

lyl_1963
罪犯就是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