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95年秋,吴王杨行密路过开元寺, 见一小和尚相貌贵不可言,便收为养子。不过,小和尚并没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自己名叫彭奴,父母双亡后流浪到开元寺寄居。杨行密没有多想,只觉得这个孩子“方颡丰颐,隆上短下”,非同凡人,于是带在了身边。
谁也没有想到到,这蓬头垢面的孤儿,日后会搅动整个江南的风云。
那时初入吴王府的彭奴活得如履薄冰,生怕哪里做的不好,干的不对,被驱逐或是挨打。
那杨行密的亲儿子们视他为入侵者,不仅在饭桌上抢他的碗,之后在校场上故意撞他射箭的胳膊,寒冬里把他的被褥扔进雪堆。
而这些彭奴从不争辩,默默啃着冷饼充饥,深夜蜷在草席中取暖。
只有油灯下的兵书是他的庇护所,烛泪烫红手背也浑然不觉。
杨行密曾把锦袍赏他,他却捧着绸缎不敢穿,师父说人要知分量,这料子太好,我撑不起。
正是这话更让杨行密确信此子不凡。
当杨行密长子杨渥为折辱他,竟在练箭时把靶子挪到他面前。
箭矢贴耳飞过时,彭奴面不改色拾起断箭,反夸杨渥箭术高超,又指着远处老槐树上的麻雀激他显真本事。
杨渥被捧得飘飘然,追射麻雀半日无功而返,反被彭奴递帕奉承,公子敢试就是胆气!杨渥一高兴竟褪下玉扳指赏他。
廊下观战的杨行密对谋士徐温感叹,这孩子会化敌为火,把渥儿的戾气都化了。
这就是语言的魅力,论会说话是多么重要。
当杨行密议事时,彭奴总蹲在沙盘旁划地图。
有次众将为攻城争执不休。
只见他指着盘中山涧细痕,若在上游筑坝,趁守军聚东门时放水,土墙必塌。
满座将领嗤笑童子妄言,唯独老将拍腿称妙。
之后按此计果然破城后,杨行密正式将他托付给徐温,此子不凡,你善加教导。
自那时候彭奴从此改名徐知诰,头上多了“徐”姓庇护,但是心里仍揣着那半块刻“李”字的玉佩。
然而徐温的严苛比风雪更刺骨。
有次徐温迁怒挥棍打他,又将他赶出府门。
徐知诰却跪在府前石阶上,冻得唇色发紫也不离去。
待到徐温归来惊问缘由,他俯首答,做儿子的,岂能舍弃父母?
然而就是这话戳中枭雄软肋。
从此徐温倾囊相授,教他骑马射箭、理政安民,连自己最珍爱的箭痕软甲也赐予他。
之后的升州是徐知诰的试验田。
赴任时他特意换上粗麻衣,骑马绕城三日看民生。
见农户面黄肌瘦,他开官仓借粮种。
见税吏克扣钱粮,他设“明账箱”许百姓投书揭发。
有年大旱,他当街架锅熬野菜粥,自己先喝三大碗,百姓吃糠,官家岂能咽肉?
而粮商趁机囤粮抬价,他派兵抄没奸商库房,白米流进千家万户灶台。
等到徐温来视察时惊呆了。
城门处跪满高呼“徐公”的百姓,田埂边老农捧出新麦,刺史教我们轮作法,收成翻倍哩!
徐温表面嘉许,转头却把儿子徐知询安插到升州夺权。
谋士宋齐丘点醒徐知诰,润州与扬州一江之隔,若京中生变,您可朝发夕至。
这话让他心头雪亮,徐温忌他甚于重他。
毕竟太过于耀眼出众的他已经威胁到了徐温的地位。
之后在杨行密死后,杨渥继位,可这小子荒淫无道,没多久就被徐温废了。
徐温立了杨行密的另一个儿子杨隆演,自己把持了朝政。
然而徐知诰在这期间没少帮衬徐温,可也悄悄培养着自己的势力。
徐温一死,徐家儿子想夺权,徐知诰没费多大劲就把他们压了下去。
这时候的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吴王府受气的小和尚了。
他穿着紫袍站在朝堂上,底下文武百官没人敢抬头看他。
有人劝他干脆称帝,他却摇摇头,先把杨行密的后人扶上王位,自己当个大丞相,慢慢收拢人心。
在禅位大典前夜,徐知诰独坐灯下。
他摩挲着当年不敢穿的锦袍,忽然操剪“刺啦”裁下一截袖口。
侍从惊呼可惜,他却将布条系在腕上,穿龙袍的皇帝多,敢裁龙袍的少,这破处正好警醒我莫忘本。
登基后他改姓李名昪,复国号唐,史称南唐。
朝臣献上镶金《帝王训》,他摆手拒收,去开元寺请部《地藏经》,我背得熟。
他治国如当年煮赈灾粥。
吴越国遭火灾,群臣怂恿趁虚攻打,他却运去三十船粮棉,趁灾劫掠,与贼何异?
江南在他的治理下成乱世桃源,减赋税、兴太学、修书局,连汴京书生都南下投奔。
临终前他咬破儿子李璟手掌,记住!中原必有一统日,若见北方生乱,立刻挥师北上。
可惜李璟耽于词曲,终将父亲咬血挣来的基业,断送在“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悲叹中。
杨行密初见彭奴时,以为“贵不可言”是帝王相。
四十年后,金陵皇宫的晨钟撞碎薄雾,宦官看见李昪抚摸着钦陵石砖,那是他命人从开元寺后院拓来的旧石。
他一生未忘,所谓贵气,不是锦袍加身的显赫,而是雪夜草席上苦读的韧劲。
不是龙椅的镶金嵌玉,而是升州田埂里沾泥的粗布袖口。
当他在弥留之际摸到腕上旧布条时,恍惚又变回沙盘前画策的小和尚,而历史的笔锋已为他写下判词,从尘埃里长出的树,才撑得起王朝的冠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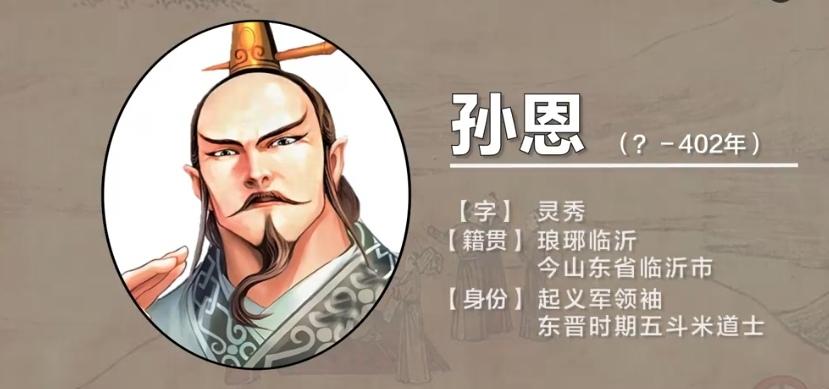






猛兽大哥
其实比小说精彩
斩不断理还乱
人都死几千年了,你还在这吹。这个就是个阴险小人,夺人家业。
新 回复 08-15 16:03
是复国,恢复家业
Amani
杨行密后代没一个有好下场的
AB成 回复 08-16 18:24
杨行密儿子们不争气啊!一个像样的有能力的儿子都没有,在乱世时代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啊!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办法啊!要知道杨行密没有一个好儿子,他徐温不是一样的吗!就是李昇不也是一样的吗!都是这样的情况(没有什么有能力的儿子都被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