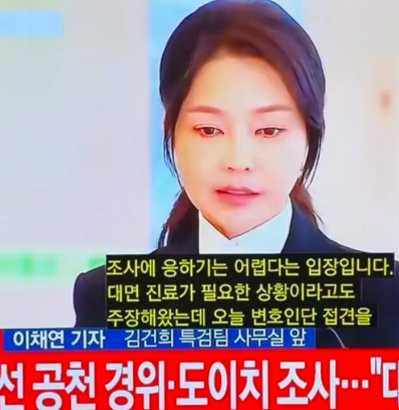1941年,一名15岁的男孩在上厕所时,发现墙缝里似乎藏着什么东西,他用手把泥巴刮开,竟然发现了一个油布包,当他打开包裹时,里面的东西让他既害怕又愤怒。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37年,在南京城估衣廊的华东照相馆里,15岁的学徒罗瑾每天埋头在暗房冲洗照片,几天后,这份平静被几个日本兵打破,他们把胶卷往柜台上一扔,命令他尽快冲洗。 而罗瑾像往常一样走进暗房,可当影像在药水中慢慢浮现时,他的手开始发抖,这些照片,全都是日军在南京城里犯下的罪证:被洗劫的店铺、搂着姑娘狂笑的日本兵、紫金山下堆积的尸体。 然而,罗瑾清楚,私藏这些东西就是死路一条,但他更怕这些罪行被彻底掩盖,他心一横,冒死多冲洗了一套。 并且他挑出最清晰的16张,订成一本相册,封面是他亲手画的,一把滴血的刀刺穿一颗心脏,旁边是两个字:血债,这本相册,成了他床板下的秘密,也成了压在心头的千斤重担。 时间来到1941年初,汪伪政府的警卫旅进驻毗卢寺,城里到处都在搜查,罗瑾觉得床板下不再安全,他把相册用油布包好,塞进了毗卢寺后院厕所的墙缝里,又用新泥封好,可三天后他去查看,墙缝空了,相册不翼而飞,罗瑾当时只感到一阵绝望。 谁知,这本相册并没有消失,而是开启了另一段守护,就在罗瑾藏好相册不久,19岁的吴璇也来到这个厕所,他是来毗卢寺参加电讯培训的学员,无意间注意到墙上那块新抹的泥巴。 可出于好奇,吴璇抠开泥巴,发现了那个油布包,照片里的内容让他瞬间明白了这东西的分量——那个被活埋的老人,他三天前还见过;那个被剖开肚子的孕妇,让他想起了自己饿死的妹妹,他没多想,立刻把相册藏进棉袄带回了家。 当晚,吴璇在自家厨房的灶台下挖了个洞,用铁盒把相册装好埋了进去,他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觉得儿子会给全家招来杀身之祸,吴璇却对父亲说:“如果这些证据消失了,死去的人就真的白死了!”这句话最终让父亲沉默了。 但吴璇依然觉得不保险,后来,他趁换岗溜进毗卢寺大殿,把相册塞进了弥勒佛像脸部金漆剥落处的一个暗格里。 此后的四年,无论外面炮火如何,吴璇每天雷打不动地去摸三次,确认相册还在,他还曾在相册扉页上,用刀尖刻下一个“耻”字,因为手抖,最后一竖拖出了一道半寸长的血痕。 终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吴璇第一时间从佛像里取出相册,送往南京军事法庭。 并且在1947年2月6日,这本被命名为“京字第一号”的相册,成了审判战犯谷寿夫的关键证据。 当法官展示其中一张照片时,谷寿夫在中华门外指挥机枪扫射平民的场面清晰可见,连他军服上的三颗金星都看得一清二楚,谷寿夫在庭上嘶吼“这是伪造!”,但法庭出示的胶卷编号,与罗瑾当年冲洗的批次完全吻合,让他无从抵赖。 在审判结束后,罗瑾和吴璇在法庭走廊里第一次见面,两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因为一本相册,命运交织在了一起,他们紧紧握手,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而70岁的吴璇则在展厅的角落里,指着相册扉页上的“耻”字,轻声对讲解员说:“这个字歪了,当年刻的时候手抖。” 在1995年,两位老人在纪念馆再次相聚,罗瑾的右耳在当年已被日本兵打聋,吴璇的背也驼得厉害,他们站在遇难者名单墙前,把相册的复印件一页页烧给逝去的同胞。 有记者问他们当年怕不怕,罗瑾坦言当然怕,吴璇也说恐惧是人之常情,但有些事,怕,也得做。 直到2014年,在首个国家公祭日,两家人将相册原件正式捐赠给纪念馆,它从此成了镇馆之宝,相册最后一页,是罗瑾当年用铅笔写下的一行字:“若有人问起,就说是一个中国人留下的。” 这份血色相册,后来作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核心部分,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如今,在纪念馆的展柜里,这本封面画着血刀的相册静静躺着,旁边的说明牌只有一句话:“由普通市民罗瑾、吴璇冒死保存。”没有过多的修饰,但每个字都有千钧之重。 当年,一个少年冒死记录下真相,另一个少年则拼命守护了它,他们只是两个普通人,在那个连活着都奢侈的年代,却用近乎本能的勇气,完成了一场跨越八年的生命接力。 这段历史的沉重,不只在于日军的暴行,更在于像罗瑾和吴璇这样的普通中国人,是如何用血肉之躯,为民族的伤痕刻下了一份不容篡改的备忘。 【信源】抗日战争纪念网2020.5.20一本滴血的相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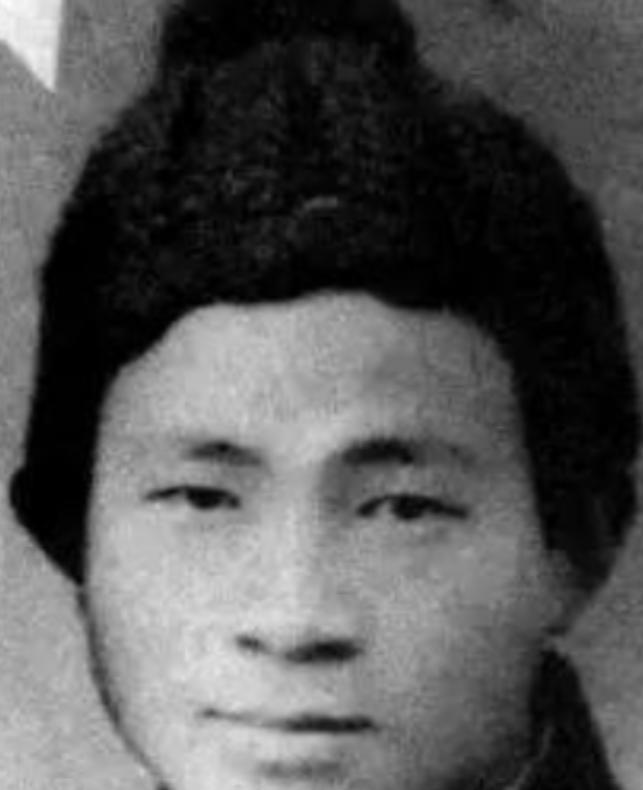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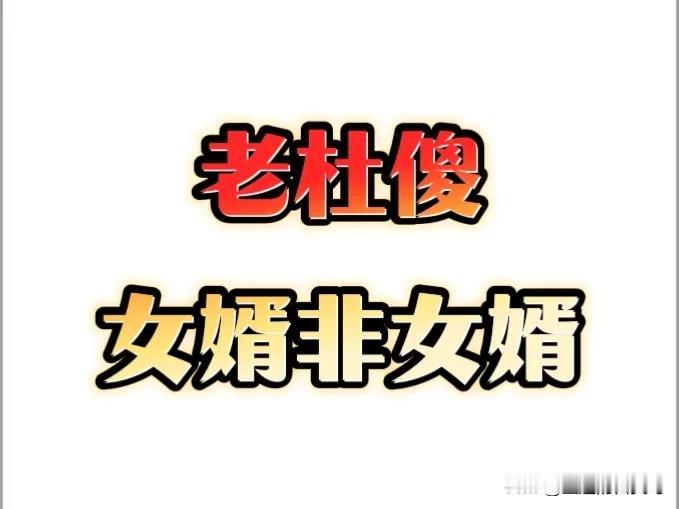
![像这种免费送房的例子,会在很多小城市上演……[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13792628978584617183.jpg?id=0)